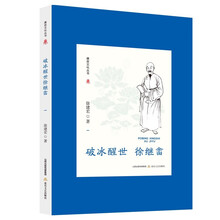孙成嘻的一笑:“来点油腥味大的。你跟洋人成天在一起,听说他们男女一见面就要抱着亲嘴儿,那还不亲煞啦!”孔祥熙正不知该咋回答,程四蛮救了驾:“你这灰鬼,快闭了你的嘴。孔少爷还没成亲,你别来不正经的。”“童男子呀,”孙成又嘻的一笑,“那咱就说正经的。我听说你都是大学生了,在洋学堂里住了五年多,该没有不知道的吧。这二年到处传说洋人在教堂净千坏事,挖出咱们孩儿的心肝配药吃。我老不大信。你说真有这事儿吗?”程四蛮还是怕为难了孔祥熙:“孙大哥,你就不会问个别的?”“这怕球甚?”孙成不以为然,“你我都不是练拳的,又不是在教的,本分老百姓,总想求个明白讨个公道还不成?你赶你的车,别搅和我们的事,人家小伙儿还没说不愿意呢,是不是?”孔祥熙看看不说话是不行的:“孙叔,我也不知这称呼对不对。听四蛮哥说,您是走南闯北吃药行饭的。这自古以来童心能人药吗?治的什么病?您应该最知底呀。”孙成说:“可洋人跟咱们不一样,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总有些怪法术吧?我真亲眼见过他们吃牛肉,血糊淋淋的不熟就吃,那还有什么不敢吃?”
孔祥熙耐心地解释:“这倒是事实,西人与我们人种不同,自然长相不同,饮食习惯也就不一样。不过他们总也是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会干出不像人的事。”
孙成说:“照你的话,他们都是好人?干过的坏事都是假的?那些在教的人千过的坏事也是假的?”
孔祥熙说:“孙叔,他们都干过甚的坏事,我真还不大清楚,您能给我讲讲吗?”
孙成说:“想听?”
程四蛮插嘴:“你别听他瞎喳喳,你问他真正见过几个洋人?”
孙成认真起来:“不是吹,我这些年哪里没去过?传教士、二毛子害人的事我能给你们讲三黑夜。小伙儿,我提‘二毛子’三个字你不嫌吧?”
孔祥熙大度地说:“没事。您就讲吧。”
下面就是从孙成话匣子里倒出来的东西:“六年前在泽州府,有个传教士强奸了十七岁的一个民女,族人告到官府。这个官儿还行,把传教士逮了去过堂,打了狗日的一百大板,撵出山西。这没错吧?可倒好,人家教会不干了,太原城天主堂的艾主教亲自出马,跑到巡抚大堂闹事,硬让把泽州府那位清官儿给撸了。再说绛州的事。绛州有个东雍书院知道吗?不是你进的洋书院,是咱老祖宗办的那种。教堂非说这书院是他们的教产,就要霸占。咱们的人说,那是学生作文识字的雅净地方,不能给,给你们另辟地方还不行?人家就说不行,非得要。这不是明欺负人吗?官司越打越热闹,越打越叫人憋气,你猜怎么着,人家法国在咱们国最大的官儿,那叫什么公死(使)的,亲自到咱省里闹腾。末了,硬把那四十三亩地的书院夺走,还另外搭赔了一块地。气人不气人?这号事多了,这是两个例子。下面我再给你讲二毛子,这些家伙更坏,也是只说两个例子。那一年我在丰镇,有个二毛子名叫韩大成,看中本村孟士仁一块村边近地,生下霸占的坏心。先说跟人家换,人家不换;后来就栽赃陷害,说人家偷了他的庄稼,告到官府。这个官是个胆小怕事的软蛋官,一听二毛子告状,只怕惹出洋人闹事,一顿板子打下去,屈打成招,叫孟家把一块好地赔给了韩大成。这还算好,没出人命。潞城县马厂有个财主阎贵生,先就为富不仁,横行乡里,入了教越发强梁。他有个女儿长得好,一早许配给刘家。刘家后来败落。这阎财主就生了嫌贫爱富之心.想悔婚。刘家自觉寒酸,说退婚可以,但要把彩礼也退了。不想这阎财主是出了名的铁公鸡,只知道进,不知道出,要钱比要他闺女还肉疼。两家为此翻了脸,动起千戈来。阎贵生仗着教会势力,叫人把上门讨彩礼的刘家父子活活打死。人命关天,官府不能不过问。可是阎财主躲进教堂,传教士挡在门口,公差连人影儿都逮不着。拖了一天又一天,我离开那地方时还没逮着,只怕也就那么拖下去了,阎家再使些钱,还不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光逼死人命这号事,我就亲身碰到过四回哩……”程四蛮听到这里,说:“我就不信,这些事都叫你碰上了?”
孙成说:“你不信?我这可是有名有姓有根有据。”
程四蛮说:“谁不知道你会编派?要不咋叫孙嘴皮呢。”
孙成急了:“我他妈要是瞎编,我就是裤裆里那玩意儿。”
孔祥熙没再听二人斗嘴,他陷入了沉思。下午父亲那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加上现在孙成嘴里这一堆事儿,心里有一种新的感触,仿佛另外给他打开一扇窗户,叫他看到一片从没见过的风景儿,不过不是好风景儿,是叫人看了不舒服的风景儿,就像看到一片乱坟岗子。“走到这一步,要我看是官府逼的,是饥荒逼的,是列强逼的,是那些不法教民逼的……”他不由得又想起父亲的话,心里嘀咕:看来这义和团的事还真不简单呀……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