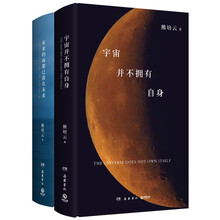她住在玉米地边的山畔,靠近那股嬉笑着流经古树的庄严的阴影的清泉。女人们提罐到这里来装水,过客们在这里谈话休息。她每天随着潺潺的泉韵工作幻想。
有一天,一个陌生人从云中的山上下来;他的头发像醉蛇一样地纷乱。我们惊奇地问,“你是谁?”他不回答,只坐在喧闹的水边沉默地望着她的茅屋。我们吓得心跳,到了夜里我们都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晨,女人们到杉树下的泉边取水,她们发现她茅屋的门开着,但是,她的声音没有了,她的微笑的脸哪里去了呢?空罐立在地上,她屋角的灯,油尽火灭了。没有人晓得在黎明以前,她跑到哪里去了——那个陌生人也不见了。
到了五月,阳光渐强,冰雪化尽,我们坐在泉边哭泣。我们心里想,“她去的地方有泉水么,在这炎热焦渴的天气中,她能到哪里去取水呢?”我们惶恐地对问,“在我们住的山外还有地方么?”
夏天的夜里,微风从南方吹来;我坐在她的空屋里,没有点上的灯仍在那里立着。忽然间那座山峰,像帘幕拉开一样从我眼前消失了。“呵,那是她未了。你好么,我的孩子?你快乐么?在无遮的天空下,你有个荫凉的地方么?可怜呵,我们的泉水不在这里供你解渴。”
“那边还是那个天空,”她说,“只是不受屏山的遮隔,——也还是那股流泉长成江河,——也还是那片土地伸广变成平原。”“一切都有了,”我叹息说,“只有我们不在。”她含愁地笑着说,“你们是在我的心里。”我醒起听见泉流潺潺,杉树的叶子在夜中沙沙地响着。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