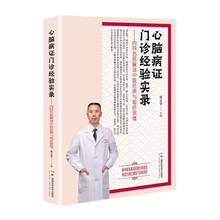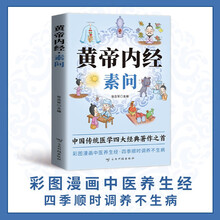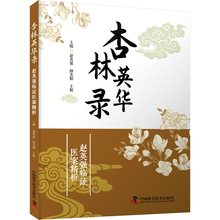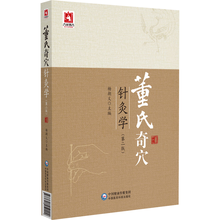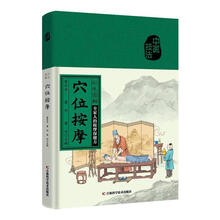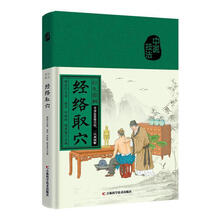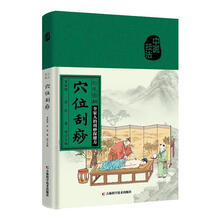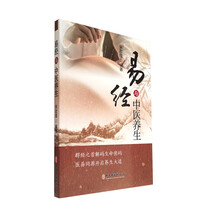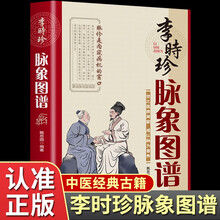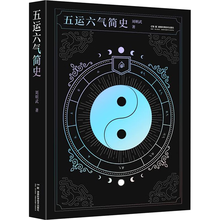医论篇
一、谈临证治疗中的五个相结合
在医学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作为中医专业人员,我们不但要勤奋不懈地深研承古,还要孜孜不倦地开拓创新,才能不断进取。在临床诊治疾病的过程中,我们面对诸多疾病,其中不乏疑难病、危重病。有易治者,也有难疗者;有可治者,亦有不可医者;还有看似不可治而经过悉心医治,使之由重转轻、由危转安者。基于此,郭淑云教授依其临证体会,总结出五个相结合,并将其指导运用于临床,可使患者得到更为快速、正确、有效的治疗。这五个相结合分别是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辨证论治与专方专药相结合、整体用药与局部用药相结合、中药内服与外治疗法相结合。
(一)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
郭淑云认为,疾病的治疗既需辨病,更当辨证。她通过实践发现,仅凭辨证论治难以对疾病做出正确诊断,如胃癌和胃炎患者均表现为胃痛,如果均按胃痛进行辨证施治,其效果及预后必然不同。借助胃镜等检查,若确诊为胃癌早期,则可帮助我们制定更为科学的治疗方案为患者尽快手术,进行适宜的放化疗,同时配合中医的辨证论治,如此,既不会贻误病情,又使治疗更加完善。因此,郭淑云在临床上先通过辨病对疾病的病因、病机演变及转归预后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再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确定*佳的治法。在辨病的基础上进一步辨证,能够提高治疗的准确性和用药的针对性。在中、西医诊断清晰的情况下采用中医治疗时,郭淑云在临床中采取辨证论治的方法进行治疗,因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髓,不单纯依据西医的诊断结果与诊疗模式拘囿中医的辨证选方与用药,用中药治疗有很好疗效的则不应用西药。如胃痛一病,中医常将之分为外邪犯胃、饮食停滞、肝气犯胃、脾胃湿热、瘀血停滞、脾胃虚寒、胃阴亏虚七型进行辨证施治,前五型属实证,后两型属虚证。但以临床所见,特别是慢性胃病者,常几种证型相互兼夹,出现既有脾胃阳虚,又兼有气滞血瘀或饮食积滞等证,并常出现寒热错杂、虚实并见等种种复杂证候,因此,更当遵从中医辨证论治的指导原则依证施药。
如上消化道溃疡之胃痛多为虚实夹杂之证,因于实者多为气滞、血瘀、痰湿互结,因于虚者则以脾胃气虚为主,其中十二指肠球部溃疡以脾胃虚寒证为多见。西医治疗主要以H2受体拮抗剂或质子泵抑制剂为主,抑制胃酸保护胃黏膜;中医在辨证施治时则注意溃疡面的修复、保护以促使其愈合,对于反酸、烧心者,郭淑云常选用乌贝散(乌贼骨、浙贝母)、瓦甘散(煅瓦楞子、炙甘草)等药。
慢性萎缩性胃炎,多属中医之“胃痞,罹病多因脾胃气虚,运化失职,气血不畅,使胃络瘀阻,胃失所养而致。该病多为本虚标实之证,其基本治法为健脾补中,活血化瘀,以促进萎缩性腺体的逆转和恢复,常用黄芪、党参、茯苓、山药、莪术、三棱、丹参、延胡索等药。
胆汁反流性胃炎之胃痛常为肝气郁滞,疏泄失常,肝气挟胆汁横逆犯胃,使胃失和降所致。故常以疏肝利胆、和胃降逆为法,使肝郁得疏自不横逆犯胃,胃气得以和降则平逆胆汁的反流。常用金钱草、延胡索、川楝子、旋覆花、半夏、竹茹、枳壳、陈皮、降香、左金丸(黄连、吴茱萸)等药。
(二)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
郭淑云认为中西医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理论体系的医学,在临床诊治疾病方面各有其长。中医学注重宏观辩证思维,而西医学注重微观本质的研究,能够在微观的层次上认识机体的结构、功能和代谢特点。临证时,郭淑云时常将患者脉证与内镜下表现相结合,进行综合辨证施治。即以中医整体观为指导的“宏观辨证与借助现代先进检测手段的“微观辨证相结合,中西合参,既遵循中医整体辨证原则,又充分运用现代医学理论及检测手段,师古而不泥古,承新并于开拓,使传统辨证更趋准确、完整、客观。借助胃镜的更深入观察,使中医望诊范围得到进一步延伸和扩大。在宏观辨证的基础上,通过胃镜的“微观辨证,将胃黏膜相作为中医“望诊范時应用于临床,可帮助医生对局部的病变进行更直接、更深层次的观察与分析。郭淑云善于在中医“宏观辨证的基础上,结合胃镜下胃黏膜相的“微观辨证确定胃痛的瘀血指征,认为胃镜下浅表性胃炎的点、片状红班,或充血、水肿、糜烂;消化性溃疡及其周缘的充血、水肿、糜烂等;萎缩性胃炎黏膜的暗红色树枝状血管网和蓝色血管网:以及不典型增生、结节、息肉等,都是血瘀的证候。郭淑云认为胃黏膜色泽鲜红、充血、水肿、糜烂,与“疮疡类似。在治疗该证时,连翘、蒲公英、败酱草为常用药。连翘被称为“疮家圣药,蒲公英、败酱草亦有解毒消痈疗疮之效,若在中医辨证为“热甚或属“湿热证者选用之,药物能够直接作用于病变局部的表面,取效甚佳。
综上所述,郭淑云倡导中西医结合下的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有机结合,强调中医为体,西医为用。临证不能以理化检查的结果作为中医辨证用药的依据,治疗时当以辨证论治理论指导而施方用药。
(三)辨证论治与专方专药相结合
郭淑云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华,是在辨明病因病机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相应的论治:专方专药是根据中医千余年来的临床经验总结出的对某种病证具有特殊疗效的方剂或药物,进一步完善了辨证论治。临证中若忽视辨证施治,只强调专方专药。由于缺失了中医学在诊治中的精髓,常致法不对症,治不中病;而对于某些疾病,若只辨证论治,忽略专方专药有时亦难取效。所以,辨证用药可发挥中医所长,着重调整机体功能以应对病情之变化:而针对特定病证运用专方专药,则对提高疗效大有裨益。清代徐大椿曰:“药不过一一二味,治不过一二症,而其效则甚捷“凡人所患之症,止一二端,则以一药治之,药专则力厚,自有奇效。若病兼数症,则必合数药而成方。岳美中亦指出:“研究探讨更多更有效之专方专药,是不断丰富与发展辨证论治具体内容之重要途径之一, 专方专药与辨证论治貌似对立,但实际上是统一的, 较妥当之论治当是专方专药与辨证论治相结合“专病专证专方专药与辨证论治相结合,才是较有成效与可靠的措施,指出了辨证论治与专方专药在临床诊治疾病相结合中的重要作用。
郭淑云根据多年来从事脾胃肝胆系统疾病的诊治经验,认为辨证论治与专方专药两者在临证中各司其用、各行其能,各有其长而具有了互补性,临证中不可偏废,若能正确配合应用,常常取效快捷,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如在治疗呕吐、呃逆、嗳气及某些特有的病证方面,常取此法获效甚佳。她认为古典医籍所载之专方专药俯拾皆是,应用由来已久,其选药精当、疗效卓著已在大量临床实践中得到了认可。如在专方的应用方面,治挛急疼痛之芍药甘草汤,治痰饮呕吐之小半夏汤,治泛酸烧心之瓦甘散、乌贝散等;在专药上,张仲景对于黄疸热重于湿证之茵陈蒿汤,湿重于热证之茵陈五苓散,阴黄证之茵陈术附汤,证虽不同,但三方均以茵陈为君药专用于黄疸的治疗:其他如治疗呃逆、嗳气的柿蒂、刀豆子、旋覆花,治疗阿米巴痢疾的鸦胆子,具有催吐作用的瓜蒂散等皆是专药专用。但必须指出的是,在临床上,应用专方治疗与之相应的病证时,由于药物组成、剂量大小及各药之间的配伍比例相当精巧严谨,在符合原证的情况下,不必独出心裁予以更改,若原方主治不能完全涵盖证候时,则应辨证施治予以加减。此外,对于一些疑难杂症,临证时无对应之古典专方专药,而以常用方药治疗少效或无效时,也需根据病证,自拟经临床多次验证的治疗该病而效著之方药,此亦可视为自身经验的专方专药。
案1.呃逆
刘某,男,59岁,2017年12月20日来诊。因感寒、情绪焦虑引起呃逆频作8天,经服西药解痉剂及中药、针灸、穴位封闭等诸法效差。现患者呃逆频作,晨起醒来时大呃,夜间寐时小呃,由于频繁呃逆颠顿,以致胸胁肌肉掣痛,常欲以双臂及手掌紧抱胸胁,以求呃逆时肌肉抽掣减轻而缓解疼痛,望之舌质淡红,苔薄白,脉略弦。方药:炒白芍30g,炙甘草10g,丁香10g,柿蒂20g,刀豆子30g,白僵蚕10g。3剂,每天1剂,水煎服。患者服1剂后呃逆即止,3剂药尽出院,未再复发。
【按语】本案患者因外感寒邪,内侵于胃,复因情绪焦虑,使肝失疏泄,横逆犯胃,致胃失和降,气逆动膈而呃逆。治宜温中散寒,缓急解痉。方用医圣张仲景缓解挛急之名方芍药甘草汤调和脾胃,敛肝柔肝,缓急止痉;丁香、柿蒂、刀豆子为止呃之专药,与芍药甘草汤联用更具辛散温通、温中和胃、降逆止呃之功;辅以白僵蚕以助止痉之力,诸药相合,寒散郁解痉止而呃除。
案2.上腹疼痛
王某,男,31岁,2017年4月25日来诊。每于凌晨3~4时上腹紧缩样疼痛,因疼痛难忍而翻身滚动,数人难以按捺,当地医院曾多次以哌替啶、氯丙嗪、异丙嗪同用亦未能控制,细问患者为剧烈的紧缩挛急之痛,即以行气化瘀、解痉止痛法为主治之。方药:芍药甘草汤合金铃子散、丹参饮加减。炒白芍60g,炙甘草15g,延胡索15g,川楝子10g,丹参30g,檀香5g,砂仁5g (另包后下),生山药30g。3剂,每天1剂,水煎服。第1剂服后当夜及次日凌晨均未发生疼痛,3剂尽服而疼痛一直未再发作。
【按语】本案以紧缩挛急样疼痛为特点,考虑为胃痉挛所致,方用芍药甘草汤以酸甘化阴,调和肝牌,缓急止痛;川楝子、延胡索合用为金铃子散,其中延胡索既行血中之气,又行气中之血,专于活血散瘀,行气止痛,合川楝子疏肝泄热,解郁止痛;丹参饮为治疗气滞血瘀互结于脘腹之专方,方中重用丹参活血祛瘀,然血瘀气亦滞,故辅以檀香、砂仁温中理气止痛,三药合用气血并治,使气行血畅,挛解而痛自除;方.中加生山药乃养护胃气之意。三方合用,祛瘀通络,疏理气滞,刚柔相济,缓急解痉之功卓著,故效若桴鼓。诚如清代医家徐大椿所云:“世又有极重极久之病,诸药罔效,忽股极清淡之方面愈。此乃其病本有专治之方,从前皆系误治,忽遇对症之药,自然应手面痊也。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