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台湾没败
时间一到1840年,每种中国历史都变得悲情,国仇家恨就此开始。像台湾这样的中国领土,也面临命运前所未有的敲门。
作为带来改变的西方列强,他们忘不了《一千零一夜》中阿里巴巴叫开宝库大门的口诀—“芝麻,开门吧”,面对台湾,谁都想当那个阿里巴巴。几百年来在西方列强眼里,台湾比一个装满金银宝藏的山洞值钱一万倍。当初荷兰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过了三十八年“台湾瘾”,在郑成功的驱逐下,离开时还恋恋不舍。明郑时期,有郑氏集团的允准,英国等西方国家有机会跟台湾做了十来年生意。到了清朝管辖后,西方国家再想一睹宝岛的真面目,就难了。
台湾,开门吧,这是西方列强在十九世纪的企盼。他们知道,要靠一句口诀达成愿望只是神话,而最有效的,是武力。
第一个对台湾提出要求的,还是如日中天的英国。
早在1824年,英国船只就在台湾沿海游弋,进行测绘,不能不说是一种觊觎的先兆。1840年鸦片战争开打,英国在武力为后盾的一系列企图心中,没有漏掉台湾。
但台湾本身没在这场战争中被打败过,还有惊艳的表现。战争爆发后,台湾的战略地位马上得到道光皇帝和闽浙总督邓廷桢的重视,布防就此开始。1841年9月底,已经在厦门、虎门各处得手的英军终于向台湾伸手,一艘运输舰向鸡笼(今基隆)港发起进攻,把守港口的守军奋起反击,结果是英舰中炮逃窜,触礁击碎。这一仗英军死三十二人,被俘一百多人,是清朝对英作战的首次胜利。
10月,英军又派舰船到达鸡笼,声言主要目的是索还被俘的英国大兵,每名愿意用银洋百元交换。两国正在交战,台湾军民不可能单方面收下这笔“赎身费”。结果英舰再度发炮,遭到更猛烈的还击,英军撤走。
11月,英国派出多艘兵船,打算到台湾相机行事。已经指挥两场胜仗的台湾兵备道姚莹和总兵达洪阿制定了战术,宗旨是“不与海上争锋”,“以计诱其搁浅,设计歼擒”,一艘英舰在这种安排下真搁浅了。据记载,这场胜利中的战利品包括英军从其他战场上缴获的清军兵器,又被台湾军民反抢了回来。俘虏里还有为英军效力的汉奸。
整个鸦片战争期间,清军屡战屡败,沿海各地丧师失地,唯独台湾连战连捷,没让英国人占到便宜。除了英军派往台湾的不是主力外,还在于岛上军民团结一心,地方官指挥得当。这样的经验没办法避免清军在整个战争中失败,清政府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缔约过程中,英方硬说在台湾被杀的兵丁是商人,是“妄杀冒功”,要求将台湾的地方官治罪。打了败仗的清政府无奈,只得把立下战功的姚莹、达洪阿革职流放,差点儿在台湾激起兵变。
姚莹、达洪阿在战争期间将大多数英军俘虏处决,是英国人嫉恨和不愿放过他们的原因。这两人后来又被朝廷重新启用,表明皇帝并不昏愦,只是无奈。
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清朝后,通过《南京条约》强迫中国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通商口岸,不包括台湾。但英国人不垂涎不惦记是不可能的:台湾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门户,战略地位绝佳,还有两种谁都眼馋的物产,一是樟脑,二是煤炭。如果舰船在海上航行时,能在台湾中途加煤,那可是个绝妙的主意。英国的涉华官员一直认为五个港口中的福州不大理想,亏损多,想另在台湾开港。清朝的态度是“断不可行”,台湾兵备道徐宗乾还订下了“全台绅民公约”,明订“不设通商口岸”、“不准夷人登岸”等。
一时不能开港,但英国人还是有特权,就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考察了台湾北部的煤炭,优良的煤质让他们惊叹。1850年,英国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文翰想花钱购买台湾鸡笼山的煤矿,遭到中方拒绝。
年轻的美国也对台湾兴趣浓郁,好几位美国商人、军人都向政府建议:占领台湾吧,用钱买用枪炮打下来都行。从1856年到1857年,美国驻华代办彼得·巴驾为台湾忙个不停,几次致函美国国务卿,强调应抓住时机占领台湾。巴驾还将美国驻香港舰队司令邀请到澳门,一起筹划如何打宝岛的主意。
英、美觊觎台湾,要得逞还得靠又一次武力。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又吃了大亏的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俄签订了《天津条约》,规定在台湾增辟新的通商口岸。落实这规定数美国最积极,从1859年就催着开口通商。清廷觉得拖也拖不过去,另外,走私贸易已经进行了两三年,不开放反而收不到税,更吃亏,于是就在淡水准备停当,只待美国派个驻台领事来。不料美国自家内乱,爆发南北战争,领事派不出来,开港的事情只得暂搁。
美国派不出领事,英国却不放手,1860年,英国领事到达台湾,又过了两年,淡水正式开关。本来《天津条约》中规定:台湾开放的口岸是台南、淡水两处,但列强并不满足。结果一位法国驻福州的税务官梅里登口吐莲花,说港口可以分为“正口”和“子口”,在南部,台南为正口,打狗(高雄)是台湾的子口;北部,淡水为正口,基隆为淡水的子口……一通鬼扯,让台湾开放了台南、高雄、淡水、基隆四个口岸。
宝岛终于重新向西方开门。从此,樟脑、煤炭等台湾商品源源出口,鸦片、纺织品和日用杂货涌入岛内。涌入岛内的还有一种西方的“特产”,叫传教士。
《赛德克·巴莱》讲的是什么
电影《赛德克·巴莱》的导演是以《海角七号》一举成名的魏德圣,题材是日据时代的“雾社事件”。
“赛德克·巴莱”的意译是“赛德克,成为真正的人”,赛德克是族名。读过这本书前面的内容,会了解台湾少数民族的族群细分比较复杂。在一般史书里,“雾社事件”被记述为少数民族泰雅族人对日本殖民者的反抗,赛德克族被视为泰雅族的一支。但赛德克族一直强调自己的独特属性,在历史上,赛德克族也跟其他泰雅族人有不少纠葛恩怨。
1915之后,在日本殖民当局的铁腕弹压下,台湾岛内不再有大规模的武装反抗了,1930年的“雾社事件”成为平静中突然出现的大地震。少数民族当主角,跟1915年前以汉人为主体的反抗相比,色彩独特。雾社是中台湾一带的泰雅族(含赛德克族)少数民族部落,莫那·鲁道是其中一支马赫坡社的头领。
尽管少数民族的生活和思维跟汉人不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道理同一。此前,日本殖民者多年推行针对少数民族的“理蕃政策”,山里的资源要,少数民族的劳动力也不放过。雾社民众的劳役重,工资低,还总被日本警察赖账。为了深入统治台湾,当局鼓励日本警察与少数民族部落头领或有地位的家族通婚,有的警察在日本有妻室,到台湾后又娶少数民族女子为妻,一旦返回日本就将其遗弃,造成一幕幕人伦悲剧。莫那·鲁道的妹妹就这样嫁给了日本巡查,又被抛弃,地位尊贵的女子遭遇如此命运,族人愤恨难言。
导火索是一场婚宴,在莫那·鲁道家中举行。日本警察吉村恰巧经过,莫那·鲁道的儿子塔达欧请他入内敬酒,傲慢的吉村嫌塔达欧手脏,不愿受酒,并用手杖敲打他的手,双方发生口角。次日,塔达欧携酒前往警所赔罪,吉村不予理睬。族人的不满情绪达到极点,又害怕日本人会报复,终于由莫那·鲁道决策先发制人,起事反抗。莫那·鲁道除率领马赫坡社外,还说服了雾社中的斯克社、塔罗湾社等一道参加。
1930年10月27日,日本人正在雾社公学校举行升旗典礼,少数民族青年突然闯入,首先砍落日本“理蕃”顾问管野政卫的头颅,随后一拥而入,将在场日本人砍杀一尽。莫那·鲁道本人率众分袭日本警察宿舍、邮政局、商店,并切断电话线。日本殖民当局迅即从台北、新竹等地调动大批军警进攻雾社,反抗者退入山中岩窟。日本军警用炮轰,用飞机轰炸,甚至违反国际公约投掷毒瓦斯,还挑唆分化,组织与莫那·鲁道等人有恩怨的其他少数民族部落进攻反抗。在电影《赛德克·巴莱》里,少数民族彼此间生死缠斗情节没有被回避,成了日后对这段历史产生分歧的重点。
眼看大势已去,莫那·鲁道和追随者一道先杀死家眷,后自杀。许多少数民族妇女、小孩集体自缢身死。一种说法是,他们的自杀是为了激励夫婿父兄的意志,使战斗者没有后顾之忧。
殖民当局强调有一百多名日本人被杀死,为此毫不动留情地挥动屠刀。在随后的五十多天里,参加反抗的几个少数民族社群人口由原来的一千四百多人减少到五百多人。1931年,日警又挑唆亲日的少数民族突袭,制造“第二次雾社事件”,又有两百多人遇害。剩余两百多人被强迫移居,离开故土,历经的苦难不仅是普通的家破人亡。
日本人也要追究管理失当的问题,检讨“理蕃政策”,时任总督石塚英藏于1931年引咎辞职。在日本人的检讨里,“人心”肯定是个重点。
厘清事件的轮廓不难,难以言喻的是人心。莫那·鲁道并非闭塞山中的老头领,他到过日本,深知以少数民族的力量无法对抗近代化殖民体制。日本人也曾在当地努力推行“文明教化”,还培养出两个起了日本名字的少数民族“楷模青年”花岗一郎、花岗二郎,但两个从外表到生活已经高度日本化的年轻人在事件发生后自杀了,还留下遗书,表明与部族共进退的心迹。从头到尾,莫那·鲁道和“雾社事件”反抗者们是求死而非求胜,以死来“成为真正的人”,体现着电影《赛德克·巴莱》力推的一句主题:“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叫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
日本人确实在富国强兵的近代化进程上先走一步,但在中国人记忆里,没有比日本侵略者的行径更野蛮的,可见文明和野蛮是相对的。莫那·鲁道们的反抗跟蒋渭水、林献堂们的反抗动机也许不尽相同,但既然在同一片土地上面对同样的压迫者,少数民族和汉人有着命运的交集。
开启蒋经国时代
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一个时代,除了此人当时的影响力外,更在于后来者的记忆。
蒋经国无疑拥有自己的时代,无论从哪个角度,将台湾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段岁月命名为“蒋经国时代”,没人会有异议。
蒋经国时代何时正式开始?明显的划定是1978年就任,名正言顺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不过多数人认为比这更早,从1972年他当上“行政院长”起,台湾就悄然更换了时代。
1972年5月,蒋介石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这已是他第五次连任,表面的选举制度早就是橡皮图章,一切早在股掌。经由一道就任的副手严家淦推荐,蒋介石提名长子、原“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为“行政院长”,5月26日,“立法院”以未曾有过的最高得票率——93.38%同意了这提名,也都是走走程序,没人能阻挡蒋氏父子间的权力授受。这一年,老蒋八十五岁,小蒋六十三岁,垂垂老矣的蒋介石总算安心。
蒋经国时代何时开始酝酿?其实是从国民党还没失掉大陆时。蒋介石的栽培、蒋经国的努力,国民党内外了然。逃到台湾后,围绕蒋经国的布局更具体,从情报、治安系统起,横跨党、政、军各方面。蒋经国于1949年初到台湾的第一个职务是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此后,历任的要职包括“国防部总政治部作战部主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国民党中常委、“国防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经委员会主委”。
终于官拜“行政院长”,有了“组阁”大权,蒋经国面临的,却是内外交困。“外交”全线溃败、台湾当局代表刚刚被驱逐出联合国,许多国家(包括日本)相继与台湾“断交”。国际环境的挫败反过来影响内部,经济不稳,社会矛盾上升。在蒋经国上台的1972年,申请移民的人数较往年增加八倍,资金外流严重。1973年碰到第一次石油危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震撼了靠外贸起家的台湾。1974年的经济成长率1.1%,比预期的9.5%差得太远;工业成长率竟为–4.5%,不进反退;当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47.8%,经济市场呈现空前的混乱。
蒋经国如何开始他的时代?后人的总结是:应变求存,实行“新人新政”,推动“革新保台”,施政核心是“本土化”,但仍然延续着“威权政治”。
就任“行政院长”之际,蒋经国致词说:“个人突出的时代已过,只有集体的思考、计划、努力、创造,才能完成时代的任务。”实际上,“个人突出的时代”并没有过去,这“突出”的“个人”由乃父变为他本人,党、政、军、特的各脉络各环节,完全在他个人的主导之下。
但蒋经国时代太不同于蒋介石时代了,他得在变局中想办法,延续国民党偏安海岛的局面。在用人方面,他吸引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技术人才,破格提拔国民党第二代,取代一身暮气的老官僚。他开启了所谓的“本土化”,起用台籍政治人物。以前,台籍人士能进入“内阁”的,只有蔡培火、连震东两人。蒋经国一上任,便大量启用台籍人士“入阁”。“行政院副院长”首度由台籍人士徐庆钟担任。十六名“阁员”当中,有六名台籍人士,包括连震东、李登辉等,台北市长张丰绪,台湾省主席谢东闵也都是台湾籍。过去,台湾省主席清一色都由外省人担任,且多为军人,从蒋经国时代起,屡屡起用台籍人士。
蒋经国明显不同于父亲的另一点,是不再执迷于“反攻大陆”,把力气和资源投向建设台湾。蒋介石将太多财力、物力、精力用在“反攻大陆”的政治神话上,社会民生建设都要“等‘反攻大陆’之后再说”。显然,蒋经国知道非留在台湾不可了。1973年12月16日,他提出五年内完成“十大建设”的计划,包括南北高速公路、桃园国际机场、台中港、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苏澳港、炼钢厂、造船厂、石油化学工业和核能发电厂,他喊出口号:“这些建设,今天不做,明天会后悔。”十大建设果然在台湾的“经济奇迹”上发挥重要作用。台湾渡过石油危机,经济成长率到1975年升至4.2%,1976年达13.5%,创空前的记录,通货膨胀率重新降回10%以内。
蒋经国更在意的,是政治,除了最后时刻的彻底蜕变外,前期也有一项重要政治变革,是开放“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台湾五六十年代的选举,因受到所谓“动员戡乱”体制的限制,最高层次只能选到省议员和县市长,不能改选“中央民意代表”。但是经过二十年的不改选,台湾的“国会”(“立法院”“监察院”和“国民大会”)已经成为全世界老人密度最高的地方了,“国会”老化不解决不行。蒋经国透过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从1972年底起,有了“增额”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虽然只占“国会”总额的小部分,不能发挥什么大作用,却也留下了台湾日后政治转型的伏笔。
1975年4月5日,八十八岁的蒋介石病逝,副手严家淦继任,蒋经国则在当月当选国民党党主席,也就握有了政治实权。197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之前,懂得进退的严家淦,表示放弃竞选连任,向国民党中常会建议提名蒋经国为候选人。蒋经国“当仁不让”,于3月21日经“国民大会”选举当选。以前的老蒋就被台湾官方称为“蒋公”。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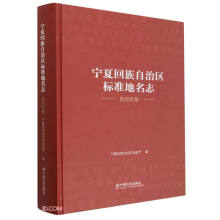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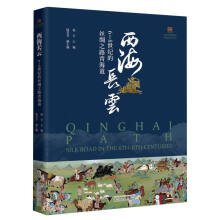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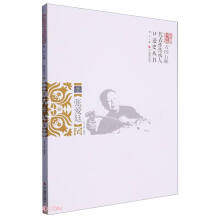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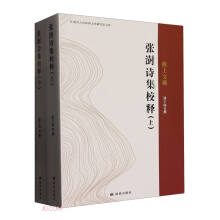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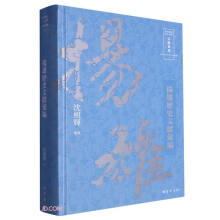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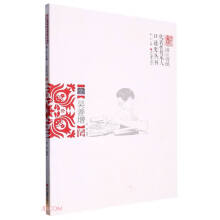
——作家、《南方都市报》资深编辑侯虹斌
一部用散文笔触写就的“台湾情史”,这部触摸台湾前世今生的温情读物,像一把带有体温的钥匙,打开了我对当今台湾诸多的陌生空间和困惑地带,让我对台湾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又理性的体悟。在此之前,我没有读过任何一部有关台湾的书,能像这部书一样,一边告诉我台湾的来龙去脉,一边又传递着一种非常有分寸的情感——不煽情却让人动情,不冰冷却让人冷静。
——出版人、读蜜传媒总编辑金马洛
在这个“人人皆媒体”的时代,带来远方真相的还是记者,勾勒史实的写作者,不仅缘于他们的专业,更因为他们带着问题去,才能发现匆匆而过中被忽视的答案,而且,他们不仅揭示现状,也连接过去与未来。很高兴遇到一位适合的记者兼作者——亢霖,惊喜是,他另一重诗人的身份,又为历史记述加上了温情的笔触。
——媒体人、《中国经营报》记者马连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