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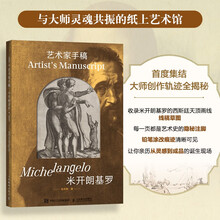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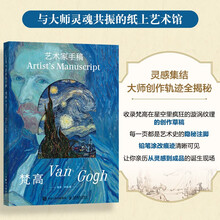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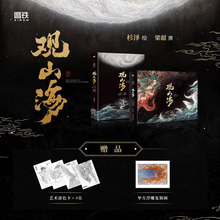

一笔一画、这个字那个字、颜真卿、柳公权、黑黑白白,陪我度过了无数晴窗松影和静夜昏灯的时光,摩挲着宣纸棉纸毛边纸不平滑的表面,就像抚摸老友的手掌。这其中,有多少眷惜、多少温情!濡墨使笔,在纸上画来画去,墨痕映带出来的,不只是一个字一个字,更是一种心境、一幅画、一种感觉,裹着我深入悠远的记忆!我写字只是抒情,从不苦练,遂也不再有什么进境。“少习若天性”,那些点画使转,于我殆如本能,便如用筷子挟菜吃饭,随手搦管,如亲故人。写字写得玩,不必矜肃以对,也即因此而得孔子所说:“游于艺”之趣,而少了点俗气匠气。玩须有玩兴,且须有与生活搅和的热情。搅和不会成为艺术,但能使生活艺术化,不再刻板、不再紧张、不再装腔作势。
写字,是我幼年学得的技艺,是跟玩家家酒、跳房子、打纸牌同一时期学会的。但学会之后,越练越熟,便渐渐荒疏了打纸牌之类的其他技能;且也在此技艺中获得了其他技能无法提供的快乐,以致玩耍至今。
写字当然需要练写。我学写字,是在面摊子上练的。其实也无所谓练不练。每天家父卖面,我就拉一条板凳,坐在面担子旁边学写字。爸爸通常总是用旧报纸写好一些字,供我在他卖面时照着摹写。这原是为了让我多识些字,兼防我趁机偷溜了去玩。可是我在摹写的过程中,对那些线条点画越来越感兴趣,觉得它们变化无穷。所以写得很起劲,墨渖淋漓,看在大人眼中不免误以为孺子可教。
待我上了学以后,老师见我能写字,又不免时时命我去写些海报、告示之类。而其实此刻写字仅是涂鸦,什么笔法都不懂。但人的毛病,就是受不得鼓励。「杀君马者道旁儿」,一获嘉许,便矜然自以为我是能写字的了。幸而小学一年级跳读三年级,导师黄灿如怜我寡学,才又教我正式学写了些字帖。
早先我亦曾临写过陆润庠等清末人的一些帖子,甚至还写过一两册何绍基。一个小娃儿,初入门,写这些,不是笑死人吗?但父亲卖面极忙,根本无暇指导我。他随便我写什么都好,只规定每天写好了几张报纸,就钉在木板墙上。夜里我睡了,他打烊回来看过,用红墨水毛笔批改圈点一番,依旧钉回墙去,让我起来自己看。我见他圈得多就高兴,批得多了就丧气,如此而已。
从前俞曲园《曲园自述诗》中载有「娇小曾孙爱似珍,怜他涂抹未停匀,晨窗日日磨丹矸,描纸亲书上大人」的诗,描写他教孙子俞平伯(僧宝)写字的情况。自注说:「小儿初学字,以朱字令其以墨笔描写,谓之描纸。『上大人孔乙己』等二十五字,宋时已有此语,不知所自始。僧宝虽未能书,性喜涂抹,每日为书一纸,令其描写」。我父虽然不是俞曲园那样的大学者,但对孩子怜爱之情,想无二致。我之涂抹,大概也与宋代以来直到俞平伯时代那些小孩子们接受到的写字教育相似。
不过黄老师觉得我这样乱学乱写颇不正宗,便命我仍以柳公权〈玄秘塔〉为主。但我其实并不甚懂得择帖,什么钱南园、黄自元也都曾胡乱学写过一阵。用笔也没个准,狼毫、羊毫、七紫三羊,抓着就用。而墨,是市面上最通行的古梅园墨汁。当时流行的墨条,较廉价,为我们小孩子能用得起的是烟墨,号称「五百斤油」。但小孩子惮于烦劳,除非去比赛,大抵都用墨汁,谁也懒得磨墨。墨汁与磨的墨究竟有什么分别,亦甚为茫然。
由于当时常参加一些国语文竞赛,学校觉得我是可以培养出去「为校增光」的,所以许多课或升降旗、打扫劳务之类都可以不必参与,只要去办公室练练字就好。后来更在医务室里为我放了一张桌子,我遇着不想上的课,便名正言顺地躲去那儿写字。整个医务室里根本没人,我独自在其间看小说、睡觉、闲闲练练书法。后来另有一位同学徐永昌亦来,我们又多了些聊天玩耍的乐趣,生活真是好不惬意。
这样写字,当然挣得了许多奖励,还得到机会代表台中市远赴台北去比赛。第一次坐光华号特快火车,赴台北游历,真是宛若驶往天堂,快慰欢畅极了。但「祸兮福所伏,福兮祸所倚」,成天玩耍不上课的结果,是数学一落千丈,差点儿考不上初中。
所以,初中以后,我对写字便再也热衷不起来了。虽然也仍去比赛,却几乎不再练字。心理上觉得已经练得够多了,何必再练?对于是否可由此成为一名书法家,亦完全没有概念,因此也无甚期许。初中时我仅见过的一名「书法家」是李世杰。他来学校表演拳指书法,我们都觉得很好玩;但知道他那些作品是要卖钱的以后,心理上总是觉得怪怪的。
也就是说,除了练过几年字以外,对于书学、书史、书坛状况,我一概不知,练字也难说有什么法度。举凡执管、用笔、结体、章法、行气、落款、使转,主要是靠自己从字帖子上去揣摩,包括写于右老的标准草书。故所得既浅,又可能不甚正宗。篆、隶更是根本没有碰过。
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入大学。由于未再练字,因此也毫无进步。唯一有点长进的,是高中认识了同学孙武曾,一同打拳作字,他喜欢写隶书,我才接触到这种书体。
如此学书经历,可说是极稚拙极浅陋的了。但幼年扎的一点童子功,也不能说是毫无作用。写字一道,对我而言,真如古人所说,叫做「童而习之,习与性成」「少习若天性」。那些点画使转,于我殆如本能。所以几乎从来不必复习,不用再去锻鍊,随手搦管,如亲故人。有时我看某些书法家写字,要先试笔、调息、敛气老半天,便暗惜其工夫毕竟不到。而书家作字,又往往太过矜慎,以此为「艺术创作」。我则因为太熟了,执笔写字,便如用筷子挟菜吃饭,常事也,本不必矜肃以对,所以也少了点艺术工作者的庄重气,同时也就可以比较不做作。
更重要的是,是对点画线条的亲切感。此乃少年玩伴,一笔一画、这个字那个字、颜真卿、柳公权、黑黑白白,陪我度过了无数晴窗松影和静夜昏灯的时光;摩挲着宣纸棉纸毛边纸不平滑的表面,就像抚摸老友的手掌。这其中,有多少眷惜、多少温情!濡墨使笔,在纸上画来画去,墨痕映带出来的,不只是一个字一个字,更是一种心境、一幅画、一种感觉。每一搦管,总不像手拈着笔杆,而彷彿手上面还有另一只手;黄老师胖胖的手正握住我的手在教我运笔。她手上的温度与力量,裹着我的手,也裹着我沈入悠远的记忆中!
因此我写字只是抒情,从不苦练,遂也不再有什么进境。大学读中文系,课程中虽有书法一门,我也率意对之。王久烈老师对我这般胡闹,大概觉得很可惜,开示了许多笔法,令我眼界豁然,才又开始写一写。
不过大学毕竟不同于小学。大学里人文荟萃,能使人对人文之美兴起具体的向往。书法与书家不再是纸上的东西,或遥远的、冷冰冰的历史生平记载,它们活生生地在周遭。正我如在《四十自述》中说的:「当时每位老师几乎都写得一手好字。申庆壁先生书如孙逸仙,浑朴厚实。丁龙垲、白惇仁两先生学颜鲁公,矜重古雅;白师的章程行稿,更是妙绝天下。王仁钧先生流丽婀娜,用笔至巧。戴培之先生,通和硬媚,亦不可多得。……其他如汪中、刘太希诸先生,诗书也都是久着盛名的。这些老师们授课,常用自写的毛笔手稿付印,文采烂然,墨渖淋漓。他们着长衫、啣烟斗,谈诗论艺,横案作字,我辈小子,望之皆觉其飘飘若云中仙人。上课时捧读其彩笺墨宝,翫其笔势,实在钦羡不已。偶于其黑板板书中,窥见其用笔之法,更觉欣欣然,若有所会。……如汪中(雨盦)先生讲诗,讲了什么,我全忘了。但我永远能感受到、能在脑海中浮荡起一个个诗的情境。檐前细雨灯花落,夜深只恐花睡去,宫灯教室里,黄暗的灯光,诗人曼声长哦,墨笺娟美,夜雾低迷。那一句句的诗语,都不是古人古书上的意象,而就是我们读诗时亲身体验的情境。灵魂于此,彷彿正彳亍于魏晋唐宋诗人之园林书案间,应目触心,理解即在当下。」
这是一个诗、文、书法以及具体人格风姿气象共同形塑的人文美感情境。在这个情境中,我们才能懂得古代文人写字抄经、飞笺斗韵、函札往返、题壁、墨戏、识跋等境况与感觉。跟书法相关的一些知识,例如评碑、论帖、选笔、择砚、用墨,乃至镌印、拓搨、装裱、鉴定等等,也都附着在或生存在这样一种情境中,令我们有了具体的了解。
所谓具体的了解,就是说它不同于抽象的、概念的、知识的、客观的了解。例如执笔法,读唐太宗〈笔法诀〉、韩方明〈授笔要说〉、林蕴〈拨镫序〉、卢携〈临池诀〉、李后主〈书述〉、陈绎曾《翰林要诀》等等,获得的理解是抽象知识概念的,我们具体见一师友用笔执管,便是具体的了解。一种执笔运笔法好不好,此刻便非知识理性问题,而是由看那个写字的人写得好不好来判断,或依你对那个人的观感与关系来判断。而一些书家之技艺,如落款、行气、附笔、题记、选纸、配色,亦非知识问题或常识问题,乃书法一道,在文人生活世界中逐渐形成的惯例以及雅俗择别之标准。从知识上讲,未必讲得清楚,需要由「见多识广」中养成此类识见。
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大增长了不少见识。纯由书艺上说,大学里卧虎藏龙,我是排不上名的。但我本来也就不准备以艺名家,故得此情境,反而更能恣情,亦更能增长我对书法的理解与涵养。后来我常写东坡语云:「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自通神」,基本上即得自这段时间的体会。
然而,读书万卷,谈何容易?一日一卷,须百年乃得三万六千卷,赵之谦曾为潘祖荫题书斋曰:「未读五千卷书者不得入此室」,标准虽已降低,却也得有二十年苦功才能达到这个指标。可见以读书万卷来增益书艺,原非懒惰人所能借口,工夫不比退笔如山者更为轻松。只不过,如此学书,其道迂而广。迂曲些,但也广阔些。比只是握一管笔苦苦杀纸耗墨汁,好像更圆通些,或更适合我这样的人的脾胃罢了。
虽然如此,我也并非全不练字。因此时眼界已开,故我喜欢去看别人写的字,每逢佳处,辄默忆于心,或移写于所带的簿本纸片上,尤其注意结体间架的问题。因为行气神韵难以摹习,字形体势则易于研拟。当时不但看近时名家,也看市招告示,什么都感到新奇,学得了不少窍门。
……
书法艺术的品鉴
唐初书法史初探
孙过庭的书论
张怀瓘书论研究
袁小修论书画
傅青主的书学
刘熙载的书概
康有为的书论
佛道经典书帖考
书法与道教
书学与武学
女书
僧书
醉书
无名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