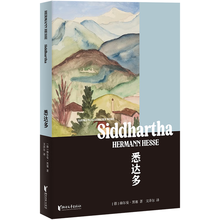“很抱歉,我得承认我开始去打扰他们了。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开端。我一向不是这样办事的,我总是用我自己的腿走自己的路,往我想去的地方去。我本来自己也不会相信我会这么做的,但是一你们看——不知怎么我觉得自己必须不择手段地达到目的。于是我便去打扰他们。那些男人说‘亲爱的朋友’,可是什么也不帮我做。于是——你们相信吗?——我就试着找女人帮忙。我一查理·马洛,让女人去干——去找个职业。老天爷!噢,你们瞧,这个念头就这样驱使着我。我有一个姨妈,一个亲爱的热心人儿。她写信说:‘这很令人高兴。我准备为你做一切,一切。这个主意非常妙。我认识那个机构里一位很高层人物的妻子,还认识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等等,等等。她下决心去大大忙乎一阵,让人家任命我当一条内河汽船的船长,如果我这么盼望的话。
“我得到了任命——当然,并且很快就得到了它。似乎公司接到消息说,他们有位船长在一场和土人的混战中被打死了,这是我的运气,这下子我更急于想去了。好些个月以后,我才试图找到他的尸体,这时我才听说,这次争吵最初是由一场关于几只母鸡的误会引起的。是的,两只黑母鸡。弗雷斯勒文一一这家伙的名字,他是个丹麦人——认为在这笔交易里人家耍花招让他吃了亏,于是他上岸去拿一条棍子揍那个村长。啊,昕人说起这个,同时又听他们告诉我说,弗雷斯勒文是一个两条腿走路的生物当中最文雅、最娴静的一个,我一点也不吃惊。他无疑是的;但是你知道,他在那边从事这场崇高的事业已经几年工夫了,很可能他到最后觉得有必要维护一下他的自尊心吧。因此他毫不留情地抽打着那个老黑人,同时有一大群这黑人的同胞在一旁看着他,吓得目瞪口呆。后来有一个人一据说是村长的儿子——听见老家伙的喊叫声,逼急了,用一支长矛冲这位白人犹豫不定地一戳一它当然便轻而易举地戳进了两块肩胛骨中间。马上全村的人都逃进了森林,他们以为会有各种各样的灾难临头。而另一方面弗雷斯勒文的汽船也惊慌失措地开跑了,是由轮机手在掌管的,我相信。此后一直到我出场并且接替了他的职务以前,似乎没有人为弗雷斯勒文的尸体多操过心。可是我不好丢开这件事不管;不过当我最后有机会和我的这位前任相会的时候,他肋骨间长出的青草已经高得足够盖住他的遗骸了。全副骨头架子都在。自从他扑倒在地之后,这堆超自然的存在物不曾被人动过。村子被抛弃了,茅屋都黑洞洞地空敞着,在日渐腐朽,歪歪斜斜地围在坍塌的泥墙里。果真是大难临头了。居民们已无影无踪,男人、女人、孩子们,全都怕得要命,钻进丛林,四处逃散了,再也没有归来。我也不知道那几只母鸡命运如何,我想不管怎样了吧,总归是献身于这场进步的事业了。反正是靠了这一光荣的业绩,我才获得任命的,本来我还得好好儿盼望一阵子呢。
“我像发了疯似的四处奔跑,去做准备,不到四十八小时,我已经在横渡海峡,去见我的雇主,并且签了合同了。短短几小时以后,我便到达一座城市。这地方总是给我一种白色坟墓的印象。这无疑是偏见。找到公司办事处并不费力。它是这城里最大的事物,我遇见的每个人满肚子里都装的是它。他们正打算经营一个海外的帝国,通过贸易去赚取非常多的钱。
“深深的阴影当中一条狭窄又荒凉的街道,高大的房屋,数不清的挂着软百叶帘的窗户,死一般寂静,石板缝里冒出青草来,左左右右都是神气十足的能走四轮马车的拱道,巨大的双扇门沉甸甸地张开一条缝。我从一个这样的门缝中溜进去,踏上一条打扫干净、不加修饰的楼梯。像荒野一般死气沉沉。我推开我遇见的第一扇门,两个女人,一个胖,一个瘦,坐在草垫椅子上结着黑绒线。瘦的一个站起身冲我走来——依然低着头在结绒线——只是在我刚想给她让路的时候——就像你碰上一个梦游病患者一样——她才站住,抬起了头看我。她的衣服平整朴素得像个伞面子,她一言不发地转过身去,把我领进一间候见室。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