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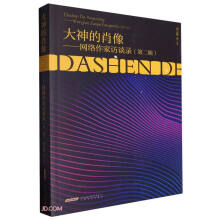


那是1972年的秋天,我和安妮·阿尔贝斯(Anni Albers)驾车沿着威尔伯高速公路,从我家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Hartford, Connecticut)的印刷公司返回她和约瑟夫·阿尔贝斯(Josef Albers)在奥兰治市(Orange)纽黑文(New Haven)郊区的家。阿尔贝斯夫妇——安妮74岁, 约瑟夫85岁——是包豪斯成员中仍然在世的最后两位。我在两年前经人介绍与他们两位结识,这会儿我正在为一个限量版的印刷作品同安妮一起工作,在这个作品上,她创造性地运用了通常用在平版印刷而非抽象艺术上的照相版印刷技术。
安妮和我乘着我的二座两厢车,这是一款名爵B-GT,阿尔贝斯夫妇称赞它是包豪斯的功能完善理念及无冗余空间理念的范例。“比起坏的艺术,我们更喜欢好的机器”,约瑟夫曾这样说过。然而,那天下午的倾盆大雨滂沱不止,安妮变得焦躁起来。“请把车开到桥底下,靠边停下来,等这场大雨消停些。”她用她那夹杂着德语口音的英语请求道,那克制的礼貌难掩她内心的绝望,“在三十年代我们乘朋友的福特A型车去墨西哥,我们也经常不得不因为暴风雨而靠边停车,”她补充说,表明她并不是在批评我的车技。
当我停下车来,雨帘在挡风玻璃上愈加密集,前方什么也看不见了。在这个当年由工作改进组织(WPA ,即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修建的美丽石雕道路桥下,安妮如释重负,随即闭上眼睛。她是位冒险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她引诱阿尔贝斯坐了五个星期的香蕉船从德绍(Dessau)的包豪斯到特内里费岛(Tenerife);在五十年代他们前往马丘比丘(Machu Picchu)——然而她也长期焦虑,她将它归因于1939年的那段时间,那时她不得不设法把她的一大家子人弄出纳粹德国;她父母的那艘船停靠在墨西哥的委拉克鲁兹(Veracruz), 在安妮越来越绝望的双亲终于设法上岸之前,她和约瑟夫不得不急匆匆地一个接一个地贿赂那些官员。当时我24岁,正吮吸雨露琼浆般地体会着安妮的生活经历,仿佛那就是我的亲身经历。同时,我还着迷于她和阿尔贝斯对艺术所做的巨大奉献,以及使他们能够抵御住任何诱惑的工作方式。现在,在桥下的跑车里,这个曾经是包豪斯纺织作坊主任的女人,由于她在指导自己新近作品的印刷工作方面尽心竭力,也由于她亲自在那里仔细检查和调试设备从而加强了灰色油墨的阶调,让我确信我们旅程的挑战是值得的。
我关掉了发动机。安妮转向我,微笑着说:“你应该得到奖励! 我知道你一直都想听到关于保罗·克利(Paul Klee)的事。” 自从我们第一次见面,我的问题就总是围绕着克利、康定斯基(Kandinsky)或者他们的其他同事,不论她和约瑟夫提及与否。然而,夫妇俩是那么专注于手头上的工作而无暇怀旧于往事,我只能得到一些匆匆忙忙的回答。终于,安妮说:“我要告诉你一些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的事,关于克利的五十大寿的。”
那是1929年。安妮告诉我,克利“在那个时候”是她的“上帝”;他也是她的离德绍包豪斯不远的林中住宅的隔壁邻居,那一排住宅由五栋华丽的新教师住宅构成。虽然在她眼中,这位瑞士画家是孤僻而不易接近的——“就像肩负世界之重的圣克里斯托弗(Saint Christopher)”——但她对他极度崇拜。她甚至在为克利的一次作品展深感震撼之余买了他的一幅水彩画作,在那次展览中,克利几乎倾其近期的画作,将它们展示在魏玛(Weimar)包豪斯的走廊上。她对家族的财富通常是避而不谈,那次购买是少有的一次对她家底的大公开。她告诉我,当她的两位舅舅开着希斯巴诺-苏莎(Hispano-Suiza)出现时,她尴尬极了,以至央求他们立即离开。然而,虽然在经济萧条时期她购买作品的能力显然会把她与其他学生区别开来,但她还是忍不住要得到克利那满是箭头和各种抽象符号的作品。眼下,她的上帝寿诞在即,安妮听说纺织作坊的其他三名学生正从附近的容克斯飞行器厂(Junkers aircraft plant)雇用一架小型飞机,他们将让这个神秘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男人的生日礼物从天上落在他的面前。他们主意已定:他不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接受礼物的方式当然也得与众不同。
克利的礼物计划装在一个形如天使的巨大包裹里,从天而降。安妮用微小闪烁的黄铜屑装点天使卷曲的头发。其他的包豪斯们忙着制作将由天使带来的礼物:一幅莱昂内尔·费宁格(Lyonel Feininger)的印刷作品,一盏玛丽安妮·勃兰特设计的台灯(Marianne Brandt)和一些来自木工作坊的小物件。
安妮原本不在将让天使降落下来的那架容克四座飞机的乘客名单上,不过,当她和她的三个伙伴抵达机场的时候,飞行员见她很纤瘦,于是便邀请她一同登机。对他们四个来说,这都是第一次飞行。当十二月的寒风穿透安妮的外套,当飞行员以360度回旋捉弄年轻的纺织设计师使他们在开敞的座舱里挤作一团时,安妮突然间意识到了新的视觉维度。她告诉我她一直生活在她的纺织和抽象水粉作品的视觉平面中,现在她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这种视角加入了时间因素。她如此着迷以至忘却了恐惧。
她引导飞行员确认出坐落于自家隔壁的克利家与康定斯基家共享的那幢房子。随即飞行员猛然下降,他们将礼物丢了下去。然而,天使的降落伞并没有完全打开,它跌跌撞撞地着了地。尽管如此,克利还是非常高兴。后来,他以他的绘画来纪念这些不寻常的礼物以及它们的传递过程,画中描绘了一个装满礼物的羊角,搁在地上,完好无损,尽管天使因磨损看上去有点糟糕(见彩图1)。这幅布面油画的收藏者詹姆士·索拉尔·索比(James Thrall Soby)告诉我的妻子和我,他认为该作品描绘了“一个在鸡尾酒会上酩酊大醉的女人”,克利将自己的金色风格用于安妮的黄铜屑,那表现了社会名流的金发。而安妮的说明彰显了事实。
约瑟夫·阿尔贝斯并不像克利那样对此事印象深刻。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问安妮是否看见“一帮白痴在头顶上飞来飞去。”安妮每每想到此事都会淘气地莞尔一笑,“我告诉他我也是其中一员,”她以她平常的语气说道,话中带有一种她常有的挑衅式的自豪感。
终于,雨停了,我们继续向前行驶。这正是美国为波普艺术欢呼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报纸上天天都要报道前一晚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和简·霍尔泽宝贝(Baby Jane Holzer)去了什么晚会。我对这些时下流行的道听途说没有兴趣,而对每一点关于包豪斯生活的信息都如获至宝。在回家的路上,听着安妮重新豪爽地绘声绘色,我开始看到包豪斯天才们生活在创造力之中,看到他们作品的耀眼光芒。
这些画家、建筑师、设计师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引领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有着与大多数人一样的需要,恐惧,以及渴望。随着我与约瑟夫的接触日渐增多,他也说出他同事们的欢乐与奋斗,这样,我对他们的现实生活以及他们改造可见世界的异乎寻常的活力都可谓略见一斑。他们对宇宙的尊重、为宇宙之美锦上添花,是持之以恒的,不过,经济、家庭和健康之类不可逃避的现实问题也是一直存在的。
安妮·阿尔贝斯是一个不轻信他人的人,可能甚至是对约瑟夫,她都不轻易相信,显然她有许多事想一吐为快。虽然她似乎总是充满确信,但还是有很多事使她不自在。当我们之间的友情有助于缓解她力有不足的感受后,她讲述了一件侮辱之事, 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前曾经刺痛她。此前,她从未跟别人提起。
阿尔贝斯夫妇搬进由格罗皮乌斯(Gropius)设计的极好的德绍包豪斯平屋顶教师住宅不久,约瑟夫(其时他在教员中已是身居高位)告诉妻子,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和他的女伴莉莉·赖希(Lilly Reich)会到家里来共进晚餐。比丈夫小十一岁、仍然是纺织作坊学生、对自己在社交方面并不充分自信的安妮,想要把一切都做到尽善尽美。在那时她和约瑟夫已经结婚三年,仍然感觉自己像一个想在丈夫的同事面前留下好印象的新媳妇。再说,密斯当时已是德国名声大噪的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阿尔贝斯夫妇俩对他的作品都十分钦佩。
安妮的母亲给过她一个黄油夹。 她从小生活在柏林(Berlin)的一个奢华家庭里,家庭成员视厨房为禁地,只准下人出入,但是当在布满装饰的餐厅里、在厚重的雕刻精美的毕德麦耶尔式餐桌上排开杯盏时,黄油球是一道必不可少的风景,安妮熟知那是怎么做的。在德绍的那个晚上,她准备着晚餐,小心地用那精巧的金属制黄油夹刮出薄如纸页的黄油薄片,并将它们做成如同鲜花盛开的精美造型。那是一种程序,也是对材料的操控,她都引以为豪,她在阐述她的织物与版画艺术时也经常提及。同纺织一样,制作黄油球也需要用正确的工具对简单的物质进行仔细地牵引拉伸,从而实现成功的变形。把黄油设计成形似花朵的样式与她通常的非再现性设计的理念格格不入,但这是少有的让她觉得身心愉悦的一次。
密斯和他傲慢的女伴来了。他们还没有脱去外套,还没有道一声问候,赖希却一眼扫过桌子,惊呼道,“黄油球!就在包豪斯!在包豪斯我原本认为你们应该会摆出一块上好的黄油块!
那是一个嘲讽,安妮·阿尔贝斯在半个世纪之后仍然一字不拉地记着。莉莉·赖希的评论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她的出言不逊。这次围绕着餐桌上黄油的形状的事件例证了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我们每一次审美的选择都影响着人类日常生活体验的品质。我开始理解,这个想法以及个人品性的重要性,正是包豪斯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