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
这会儿,一个柳丝儿纹风不动的夏日的午后,我坐回拱宸桥边自己的咖啡馆,打开胜利女神雕像的照片和录影,正视、旁观、远看、近察,试图重现一周前在卢浮宫亲身领受的那旋绕在女神周身的风暴,然而,我的追述将何其苍白??
试想一下,如果你刚刚才见过蒙娜丽莎经典的微笑,又刚刚才度量过断臂维纳斯合乎黄金律的美,那么还有什么可以震撼你,冲击你,让你尚在五十米外,还没有步近中庭,就被一股扑面而来的风所裹挟?
因为突然,所以窒息。我相信人世间有一见钟情,却没有遭逢过一眼勾魂摄魄、当场气绝身亡的奇遇。毕竟女性与男性相比,看待异性的角度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我做不到第一眼即从外表断定自己能否全然接纳一个男性的一切。那就让我想象真爱吧,带有一定的侵略性的,类似风入穷巷与陋室,吹死灰,骇溷浊,扬腐余,席卷起枯枝败叶,于是通体敞亮,心头一阵阵寒噤。里尔克在《哀歌》第一首中写道:美,是一种你恰好能接受的恐怖!
就是这样,我被胜利女神吓到了——
她正面迎你,立于舟首微翘的船头。右腿在前,臀部随殿后的左腿而略倚向左,从腿部肌肉饱满的线条,以及胸部凹凸有致的轮廓,你能清晰地感到她身体的重量如何均匀的囤蓄于此,囤蓄于这一副强有力但又不失女性柔美的下肢中,也正是这一完美的站姿,令女神巍然傲立了千年。
最令我心折的是女神的衣裳被海浪浸湿又被海风吹动的细节。双乳撑起了观者坚挺的性别意识,而衣裳S型的褶皱,以及顺致而下的沉坠线条,在不断地呼应有形物质与无形要素之间的绝对统一。那水与风与肌肤之间薄薄的透明感,甚至能让你感到女神潮湿的腹部透过冰凉的大理石,尚在呼吸。
从侧面看,女神张开的双翅羽翼分明,甚至能清晰地看出羽毛被海风剧烈吹拂后那略显凌乱的痕迹,听说运动品牌耐克的商标灵感就取自胜利女神翅膀的弧线,优美又不失雄健,意味着永恒的胜利与凯旋。据说她是为一次海战打败统治着埃及的托勒密而建,十八世纪被后人发现前一直耸立在萨莫德拉克勒边的悬崖上。
风从哪里来?我环顾四周。卢浮宫建筑样式古典,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规模宏大,内部装饰华丽。光线从穹顶圆形天窗中投射下来,柔和地打在这尊高3。28米的雕像上。胜利女神所在的这间中庭正好处于另外几间展厅之间,一条宏伟宽敞的阶梯高处,我不断地抬头昂视,仿佛她随时都可能凌风而去。
没有其它可能,这尊女神雕像的头部如果存在,那么她一定是正视前方,毫无畏惧。也许是出于大理石材质的原因,以及雕塑这一艺术手法本身对于平面物质处理的难度,我们发现所有的希腊雕像眼神所呈现的都是无物的圆形。空洞,所以包含一切。一种圆,一种自在的逼视,满足着观者内心的一切视觉要求。在游赏之际,卢浮宫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向我们讲解绘画创作中透视法的要妙,以及这一技法对整个西方绘画艺术的重要性,这一点在《蒙娜丽莎》中得到佐证。眼神对位,即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看画中人的眼睛,它都如同星辰一般跟着你,转。也可作唯心理解:你在看,所以她在看。
当然,我现在关于雕像眼睛的谈论都是空谈,因为这尊胜利女神,除了与维纳斯一样没有手臂以外,连头也没有。但是假如它存在,是不是又会生出更多遗憾?据说有很多后来者从艺术的残缺法则中深得了遗憾之妙。罗丹发现他的巴尔扎克雕像那只手过于出众以至于影响了躯干主体的凸显,便挥刀割爱。我反躬自问,为了一首诗的整体效果,我舍得将那些最得意的句子轻轻删去吗?这一抱负何其悲壮。可又为什么不反过来,只留下一只手,让它格言般存在?
胜利女神的手果然都遗落乌有乡了吗?并非如此。就在女神雕像的右侧,展示着一只向上微拢的手掌,据介绍,经过鉴定,可以确认这只手掌的石质与雕塑本尊出自同一个岛屿(1863年从萨姆特拉斯岛的神庙废墟中发掘出来)。馆中更有一张平面图,推断还原出了女神雕像完整时的样子:右手拿着一只长长的号角,与雕像的嘴部连接在一起,左手则握着一根无头的长矛,耷拉着垂下。就像男人最怕的就是女人对他没有要求吧,女神无手,因而把握了一切。老子说,执者失之;反过来,失者执之?我不赞成刻意破坏,也不认同拼凑历史。高鹗被人指摘了多年,而狗尾续貂的野心却一再上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不成样子。
此时的运河已夜色旖旎,月亮似一枚自身的倒影,笼着水衣。七月十三夜的月亮,有一点不圆满,有一点缺憾,但是,很美。
螺蛳青
一个女子爱惜自己的形象,谢绝在大庭广众之下啃肉骨头以大快朵颐,我认为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对于一盘小小的螺蛳,因羞于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而投箸不食,那就显得有点拘礼或矫情了。
吃螺蛳是一项技术活儿,掌握者不仅能一饱口福,而且完全可以做到指顾之间庄矜有致。
人们一想到螺蛳,不是酱爆的,就是水煮的,加点葱蒜,加点辣椒。的确,烹饪之道不在于如何变着法子折腾,而在于因材制宜。有那一等大厨为拔高螺蛳的品位,把它们与本鸡、甲鱼同炖,或把它们掏空,再将一撮撮肉末塞进壳内,颇具盛德之饰。然而,虽上得台面了,汤的口味也不错,我却唏嘘不已,只认是生生糟蹋了这水中仙子。
要知道螺蛳的最佳产地,并非肥沃的池塘湖泊,而是水质清淳的江河。它早已习惯了在清水中开阖吐纳。更何况,螺蛳之美,不仅在其紧、韧、鲜的肉质,更在筷子起落间悠游闲适的那一种意趣。
吃螺蛳,就像嗑瓜子,壳多肉少,所得不偿劳,因此,吃的实在是一份心情,一种境界。最好,吃螺蛳是靸一双悬而不落的拖鞋,翘着二郎腿,支在一条长板凳上,在酣醉摇曳的路灯下,叮当碰撞的酒瓶间。这不仅适合那些摇摇而不坠的惬意闲汉,也适合一干窈窕淑女。
作为淑女之一,与那些更为热爱生活、拥抱生活的人相比,我在夜色下出没于酒肆的机会不多,但我毕竟在富春江的深水浅滩边长大,隔三岔五就能在餐桌上遭遇到螺蛳,熟能生巧,因此,无庸讳言,——唉,这话太文气了,我就直说了吧:本人吃螺蛳的段位相当高,以至于一顿下来,别人食肉而饱,我能将螺蛳当饭吃,以至于落下一个雅号,唤作“螺蛳青”,即一种专吃螺蛳的、生长于清水中的鱼。
毫不夸张地说,一盘螺蛳上桌,我只要看一眼便知道,它是神品,还是逸品。
如果螺蛳壳上附有绒毛,就说明产自富营养化的湖泊或池塘中,即为次品,已不足道。
如果螺蛳壳色泽深绿,外形大过拇指甲,且表面光滑,就一定来自水草丰沛的江湾河曲里,若能遇上一盘这样的螺蛳,算你走运了。它们可以酱爆,更适合汤煮。按照我家乡的做法,除却放入姜蒜,汤汁中还要加几片咸肉,搁汤搁肉的烧在一起,然后用朝天椒增辣,用青椒调香。只要厨师料理得当,大有可能成为一盘螺蛳的神品。但是,假如其个头超过拇指甲那么大,情况就不妙了,好比今人学八大山人的写意,过犹不及。换言之,大的螺蛳口感嫌硬,而且不易入味,吮吸起来难免摇唇鼓舌的,伤及元气,只好跟田螺一样拿去灌肉了。
那么什么是螺蛳中的逸品呢?当是个小而色浅的。个头应控制在无名指甲大小以内,螺壳略显透明,呈浅绿色,细细的一盘上来,甚至有一种小户人家的寡淡和清寒。这些个小肉嫩的螺蛳,最适合酱爆,而掌握汤汁的浓稠稀薄尤为重要,太稀则味不逮,过稠则口感粘腻,而且吮吸起来力屈势沮。火力应该是越旺越好,只须在铁红的热锅中轻轻翻几个身便可装盘。很多人对它望而生畏,原因很简单,总觉得个小就加大了食客的劳作,增添了麻烦。其实不然。
真正的吃螺蛳高手,已经到了人螺合一的境地:伸出筷子,夹起螺蛳,放在唇尖,再一撮口,然后是珠落玉盘,以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完成一个个流畅的循环,端的是气定神闲。整套动作迅捷而精准,如蜂啜蜜,吮其精而弃其杂。又好比高速公路上的驾车能手,不争一时之快,让马达转速保持在一个固定值内,除此之外,快慢由人,荣辱不惊,最终他会发现,无论如何赶超,你总是绝望地在他前头。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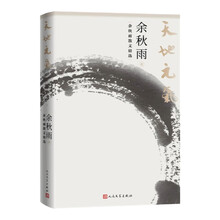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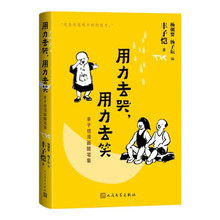



——余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