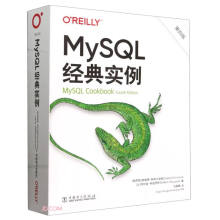我之所以敬仰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Robbe-Grillet),缘于他的多才多艺:农艺师、小说家、电影工作者和业余画家。当然,在我看来,他还是一位小说理论家。他那些论战性的文章──比如《为了一种新小说》──具有哲学性的深刻。罗伯-格里耶一贯反对把小说搬上银幕,因此,他给作为导演的自己及其助手还有技术人员制作了一份类似说明书或者操作手册一样的文本,比如法国午夜出版社出版的电影小说《去年在马里安巴》(L’Annéedernière àMarienbad,1961)、《不朽的女人》(L’Immortelle,1963)和《格拉迪瓦在叫你》(C’est Gradivaqui vousappelle,2002)等,这些文本里有关于音轨的说明,有关于摄影机如何运用的说明,等等。他为这种文本发明了一个词:电影小说(ciné-roman)。在《不朽的女人》一书的导言中,阿兰·罗伯-格里耶给了电影小说一个这样的定义:
人们即将读到的这本书,并不自诩为一部自成一体的作品。作品,是电影,如人们在电影院里看到和听到的那个样子。而在这里,人们只能找到对它的一种描绘:举个例子吧,这就好比对一部歌剧而言,它是剧本,配有音乐总谱,还有布景提示,表演说明……对没能去观看放映的人来说,电影小说还能够像一本乐谱那样被人阅读……
结合我编剧并导演第一部电影的经验,我愿意把对小说和电影的研究结合在同一个文本里。我愿意尝试一种新的文体写作,混杂着虚构、纪实、传说、寓言、梦境和自传性的回忆,既现实又超现实。也就是说,我想要写出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小说,也即电影与小说这两种艺术形式相互渗透和彼此映照的新的小说。就我的理解(可能是浅薄的,甚至是谬误的)来说,电影小说(如果说真有这样一种小说的话),以打破小说和电影剧本在文体学上的差异,进而打破现实与非现实的铁幕。其实,早在1970年代我尚未出生之前,伟大的阿兰·罗伯-格里耶就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实验了。我只是在阿兰·罗伯-格里耶所定义的电影小说的基础上,增加了叙事的成分,并且吸收了他那混合着自传与虚构故事的《重现的镜子》(或是《昂热丽克或迷醉》,或是《科兰特最后的日子》)的写作技巧,从而使电影小说在挖掘叙事之可能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但是,每每想及自己受到阿兰·罗伯-格里耶如此深刻的影响,,我就痛感于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所谓的“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Influence)之折磨,竟至于手指痉挛到有些不能敲打键盘以便写下自己贫弱的记忆和肤浅的思考以及畏葸的实验。在阿兰·罗伯-格里耶和我之间,间隔着两个遥远大陆的两个文明体系那至今不可跨越的智力的鸿沟(而且这智力的鸿沟日益扩大)。
智力的鸿沟可能源自便于抽象思维的拼音文字与适合事物表象之感官描述的象形文字的发明。也就是说,象形文字是感官的产物,而拼音文字是思维的产物。当我们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超绝万物的唯一而又绝对的“TheGod”和“All·h”译为“上帝”、“天主”或“真主”的时候,我们显然是降低了“TheGod”和“All·h”的神之属性,使其具有拟人的物化倾向从而不再超绝万物,不再绝对唯一。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