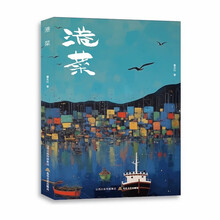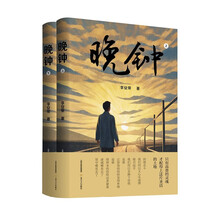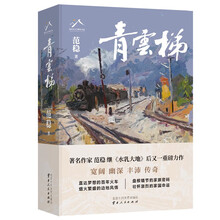冷飕飕的寒风,昏暗暗的路灯,黑魆魆的鼓楼,空荡荡的地安门大街。虽然快到新年了,可没有一点儿过年的气氛。天刚擦黑,后门大街的许多店铺
就上了板,黑了灯。年关贱价牺牲、大甩卖的招牌,孤单单地摆在几家还盼着最后几个顾客光临的商店门口。快散了架的有轨电车,响着有气没力、
刺耳的“铛铛”声,慢腾腾地开过。车上连个人影都看不到,就连地安门门洞里的乞丐也都不见了。寒冬腊月,昏天黑地,一街萧条,一片凄凉。
大街路西的一家古玩店还亮着灯。门脸儿不大,黑地金字的牌匾十分考究,上有陈怀臻教授署名题写的三个大字:“品古斋”。自从陈怀臻买下“品
古斋”后,为了继承原来店铺的古风古韵,店里装潢陈设都没动,只是把门前的旧牌匾摘下来,换上了现在这块新牌匾。有陈家带来的新运气,足够
了。
屋里昏暗的灯光下,围着一张硬木圆桌坐着几位学者风度的客人。
“陈教授,宝贝是件真宝贝。可是,本主儿的管家死活不让价。还说,要是带到国外,可就发大财了。”头发花白的齐先生说。
“您找专家问过?”陈怀臻有些不放心。
“问过好几位。其中有您认识的几位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可都不大清楚,更从没见过。这我才请常三爷亲自出马。这不,今天我把常三爷和刘五爷都
请来了。”
常三爷先开了腔:“本主儿姓金,爱新觉罗宗室近亲之后。他爷爷是‘载’字辈的,比末代皇帝宣统还长一辈。我向多位老资格的朋友请教过,这位
金先生的身世绝无问题。”
“您见过这件宝物?”
“齐先生和他的管家说起你在慈慧殿重修了贝勒府,这位金先生才答应我们看看这件宝物。我又专门请了故宫博物院的单先生一起去的。”
“难得请单先生给把把眼,让您费心了。”
“此事非同小可,不敢不仔细。”
“本主儿让我们事先告知都有谁去,最多三位。由本主儿确定日期。”齐先生说。
“前天,齐先生陪着我和单先生按时去金宅。金先生没露面,管家接待了我们。”
刘五爷急着问:“结果如何?”
“真品,绝对是真品,我算是开了眼。单先生跟我说,这宗宝贝,连故宫博物院都没有,的的确确是件无价之宝。”
微弱的灯光下,一片寂静。齐先生提起暖壶,给茶壶续上水,给每位斟上茶。
刘五爷一个劲儿嘬牙花子:“平时置产,乱世藏金。就算是件无价之宝,三十条金子,那可是不少钱哪。”
常三爷频频点头,“谁说不是。四百八十两金子!就算是现在物价飞涨的局面,少说也能买一千万斤大米!乱世年头,花这么多钱,实在让人心疼。
”
齐先生压低声音:“可有人不心疼。我们答应了金先生管家一定对此事严格保密。昨天他急着忙着来这儿问我,是不是走漏了消息。”
“怎么?”陈怀臻问。
“他突然接到一位先生的电话,声称对金先生的家藏宝物有兴趣,肯出高价。”
“这么快?”陈怀臻皱起眉头。
“管家说,此事要是传开了,可就闹大了。一再叮嘱,要是咱们确实有意,回音要快。金先生已然决定提前离开北平,取道天津南下了。”
刘五爷咳嗽了一声,“怀臻,可否容我说说不同想法?”
“五哥,您说。”
“三十条金子不是小数,也有其他用法。”刘五爷有些犹豫。
“五哥,您尽管说。”
“比如,可以在香港买房子置地,当下正是好时候,价位已经到了谷底。当然,我只是随便说说。”
“多谢您的提醒。说实话,现在我已是万念俱灰。这俩糟钱儿能留住国宝,也算是对得起祖宗。”
大家默默点头。
常三爷发话:“怀臻,不管怎么说,总得会会这位金先生,亲眼见识见识这件宝贝,再做商议。”
“三爷言之有理。”刘五爷频频点头。
“齐先生,那就麻烦您再跑一趟。要是能见,今天晚上咱们就去见金先生。我们在家里等您的电话。”怀臻果断决定。
“好,各位坐着,我马上去。”齐先生穿上大衣,疾步走出门外。
怀臻转过身来,“五爷,三爷,您二位要是没要紧事,先到舍下吃顿便饭,等候齐先生的消息。如何?”
“这就是要紧事。五爷,咱们走。”常三爷搀着五爷一起走出“品古斋”。
小吴一直警惕地坐在道济轿车里。他不仅是司机,还是陈怀臻和家人的贴身护卫。见陈怀臻等人走出“品古斋”,他打着火,拉开车门,请各位上车
,又返回店铺门口,查实门锁已然锁好,这才慢慢地启动轿车,顺着后门大街,不一会儿就来到了慈慧殿三号大门前。小吴扶着常三爷、刘五爷、陈
怀臻下了车,走进大门。几位顺着青砖甬道,绕过影壁,穿过垂花门,走过两边是海棠树的过厅,再进一道门,绕道雕梁画栋的回廊,这才来到了陈
家豪宅正院的北屋大客厅。
“欢迎,欢迎!二位可是稀客,”佑君早已等候在客厅门前,“请进,快请进。”
“陈太太,不是不愿意常来,就是来您府上忒费劲。”刘五爷拄着手杖走在最后面。
“怎么?”
“从大门口到您的客厅,少说得一里多地。”刘五爷半开着玩笑。
“看您说的,我来搀您。”佑君赶忙迎上前去。
刘五爷和常三爷先在法元老人画像前鞠了三个躬,宾主在西客厅落座。十件套的真皮沙发周围摆着五个大小洋式玻璃茶几,旁边还有一个镀金的轮车
。轮车上是一套纯银的咖啡壶碗。现代设计的大花盆里,郁郁葱葱的石榴树、桂花树、橡皮树,给大客厅送来活活生气,阵阵清香。
陈家老三陈恩豫走过来,给各位敬茶。
看着这个浓眉大眼的英俊年轻人,常三爷笑着招呼:“这不是恩豫吗?好久没见了。”
“常伯父、刘伯父,好久没去看望你们了。我刚从上海回来。”
佑君解释:“他考上了交通大学,过完寒假还得回上海。”
“名牌大学,什么系?”刘五爷问。
“航空系。”
“好!造飞机,打日本。”
说着话,佑君站起身来,“各位都饿了吧?咱们到餐厅吃点儿便饭。闺女们和小崧苼都在那儿等着哪。”
大家走进东餐厅,思惟、悟荃和小崧苼紧忙站起来,招呼客人们入座。老朋友聚会,又热闹,又随意,闺女们也都不回避。每次见到已经长成漂亮大
闺女的思惟和悟荃,常三爷和刘五爷总得夸上半天。两位姑娘秀眼长眉,都是女中学生打扮,短发,棉旗袍,又秀气,又文雅。大家团团围坐在大圆
桌周围,一边品尝着热气腾腾的炉肉火锅,一边喝着花雕黄酒,一边聊着各家的近况。炉肉火锅是北平地道的特产。用新鲜的五花肉,加上特制的调
料,用松木加火熏到八成熟,再稍经烹炸,“炉”好了待用。再用新鲜猪肉馅儿,加上特制的调料,用松木加火熏到八成熟,再稍经烹炸,做成炉肉
丸子待用。用炭火烧开铜火锅,把事先准备好的虾米、豆腐、白菜、粉丝一层层地垫在锅底,再铺上一层炉肉丸子,上面再铺上一层炉肉,盖上火锅
盖。待开了锅,掀开锅盖,炉肉火锅就算大功告成了。只可惜,现如今炉肉火锅已经失传了。
恩豫举起酒杯,“我敬常伯父、刘伯父一杯。”
“我也敬常伯父、刘伯父一杯,”坐在母亲旁边的小崧苼虽不满九岁,可又高又胖,像个小大人。
“小孩子家不许喝酒。”佑君拿过崧苼的酒杯。
“妈,不是黄酒,这是茶。”小崧苼又把酒杯夺了过去。
“这孩子,什么都少不了你。”佑君笑道。
“躲在家里,和老朋友、孩子们一起吃顿饭,喝上几杯,咱们也就剩下这个乐儿了。”常三爷无限感慨。
“今朝有酒今朝醉吧。”刘五爷又干了一杯。
“这就算是万幸,知足吧。”佑君说。
“盼着吧,世道要变了。”恩豫说。
“有什么新闻?”常三爷问。
“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不但剿不了匪,反倒失去了自己的十余万部队。天津、塘沽海上通道被切断,北平已成瓮中之鳖。起义和谈是唯一出路
。”
“你都是听谁说的?”佑君问。
“济生大哥说的,还有错?”
正说着,电话铃声响起。
“齐先生的电话,”佑君放下话筒,“请各位马上就去金先生那里。”
“我也去。”小崧苼嚷嚷着。
“小孩子家,你凑什么热闹。”佑君对小崧苼板起了脸。
“让他去见识见识也好。”怀臻管教子女虽很严,可总愿意他们能多见见世面。去“品古斋”,会老朋友,怀臻就经常带着小崧苼。不坐车,爷儿俩
骑自行车。怀臻在前面骑他那辆德国蓝牌,小崧苼在后面骑他的小自行车。崧苼特别爱听大人们说古论今,尤其爱听老北平的人情世故。听到父亲要
带他去,小崧苼高兴得一溜烟跑了出去。怀臻和常三爷、刘五爷也跟着走出餐厅。
道济轿车出了慈慧殿,过了景山东街,一辆车也没有,一个行人也看不到。灯火管制,路灯全灭了。小吴连大灯也不敢开,很快就到了北池子大街。
只见齐先生站在北池子三条胡同口翘首以待。道济车车身太宽,只好停在胡同口。齐先生引路,路北的两扇大红门前,已有人等候在那里。
一位年过花甲,瘦小身材,戴着皮帽,身穿皮袍的老者,把一行人迎进了正房客厅。古色古香的客厅里只剩下些简单的桌椅,空空荡荡。那位老者招
呼大家就坐。下人给大家倒上香喷喷的茉莉花茶。
“这位就是陈先生吧。”老者朝着富态的刘五爷致意。
“不敢,不敢。鄙人姓刘。真正的财主是这位,”刘五爷急忙引荐,“陈怀臻教授。”
“恕我眼拙,恕我眼拙。”老者朝着貌不惊人、身着布面棉袍和棉鞋的陈怀臻表示歉意。
齐先生忙介绍:“真人不露相。金先生,这就是我多次跟您提起过的陈怀臻教授。陈先生用了近两年时间把您叔爷的贝勒府翻盖一新。美国人想以美
元现金高价买这座豪宅,陈先生不卖。多少人开出了天价,陈先生还是不卖。这不,听说您和贝勒府的王爷有亲戚关系,特地登门拜访。”
金先生深怀敬意向怀臻鞠了一躬,“陈先生,真得谢谢您。八旗子弟不争气,要不是您,我叔爷的这座贝勒府可就糟蹋了。”
“金先生,您太客气了。”怀臻抱拳回谢,“这也就是前几年。要是现在,我还真没这个胆量了。”
金先生打量着小崧苼,“这位小少爷是……”
齐先生忙介绍:“这是陈教授的小公子,叫崧苼。”
“金爷爷好。”小崧苼一点儿不怯场。
“好,好。真是将门虎子,一表人才。”金先生很是喜欢小崧苼。
常三爷插话:“金先生,把您那件宝贝请出来,快让大家一饱眼福吧。”
“是,是。已然准备好了。”
身穿长袍马褂的下人们给每位客人送上一副干净的白手套,点起檀香,在客厅中间铺着黄缎子桌布的红木圆桌上,又垫上一个绣花圆垫。一位管事模
样的人,戴着白手套,捧着个镶着祖母绿的紫檀盒,缓步走到桌前。把紫檀盒子轻轻地放在圆桌的绣花垫上,退到一旁。
金先生站起身双手抱拳,“这件宝贝有祖先乾隆爷的御印。按照家里的规矩,我得先施大礼,才能打开这个紫檀盒。”。
金先生低头走到桌前,恭敬地深深一揖,跪在桌前的绣花垫上,抱拳举至额头,磕头。抱拳举至额头,再磕头。抱拳举至额头,再磕头。三叩首后他
站起身来,戴上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抽去紫檀盒顶盖,抽出木销,放倒四面护板,露出了里面的一方砚台盒。长方形的砚台盒不大,木质呈深黄色。
金先生轻轻拿起砚台盒盖,这才露出了一块砚台。看得出来,这块砚台饱经沧桑,年代很久了。
“各位,这就是唐代褚遂良的砚台,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金先生指着四块护板,“这件宝贝之所以称得上是难得的顶级国宝,不只在于这块砚
台,更在于紫檀盒的四方护板。从唐代到祖上乾隆爷,这四方护板上共有唐、宋、明、清四位皇帝的御印和御题。四代王朝、四位皇帝的御印和御笔
齐聚在一件古物上,据我所知仅此一件,世上绝无仅有。来人,把放大镜拿来。给小少爷搬个脚凳,好看得更清楚。”
下人们搬来脚凳,拿来个考究的放大镜,递给陈怀臻。大家戴着白手套,围在圆桌四周,轮流拿着放大镜,仔细瞻仰。
金先生走近小崧苼,“手套太大了,小少爷就用我这块白手绢吧。”小崧苼有礼貌地鞠躬致谢,站在脚凳上,垫着手绢拿着放大镜,也像回事儿似的
细看了一遍。
金先生接着解释:“当年的能工巧匠在砚台盒外面加制了一个极其考究的紫檀外盒。紫檀外盒四周还镶上了四块珍贵的翡翠。打开销子,外盒四壁平
铺开来,在内衬的四块黄罗丝缎上,先有的是唐宪宗的御印。接下来的三块御印是宋神宗赵顼、明成祖朱棣,还有就是祖上乾隆皇帝爷的。每方御印
之下都题有年号和季节。这四块难得凑在一起的御印和御笔,让这方褚遂良砚台金碧生辉,价值连城,成了世上罕见的珍宝。”
一时间,屋里肃静得连喘气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大家又轮流拿着放大镜仔细端详这四方御印和御题,瞻仰那方宝砚和同样珍贵的翡翠玉石,惊叹之
情溢于言表。
陈怀臻抬起头来,不无惋惜地对金先生说:“真是开眼了。冒昧地问您,您真舍得割爱?”
“实不相瞒,这比剜我的心还疼。这次逃难,什么都能丢下,唯独想带着这件宝贝上路。可是,逃难的路不好走啊。这件宝贝要是有个闪失,我怎么
对得起祖上?怎么对得起先人?想来想去,只有把这件宝贝托付给一位有识之士,才是万全之策。”
“恕我多言,”刘五爷插话,“这件宝物一直都在您身边?没有经过外人的手?”
“没有。”金先生语气很肯定,“自从我祖上得到这件宝物之后,就成了我们家世代相传的镇宅之宝。不要说没经过外人之手,就连我们爱新觉罗门
里知道的也不多。”
“金先生,和您一样,陈教授也是万分爱惜这件宝物。一是不愿这件国宝飘落到海外;二是不愿有什么闪失。这样的宝物,开什么价都不多。可是眼
下这战乱时局,您看这价钱是不是还有商量?”齐先生想再还还价。
陈怀臻客气地摆了摆手,“齐先生,依金先生的价,就依金先生的价。金先生,您能把这件宝物托付给我,我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所有人为之一震。
金先生一下动了容,“您别说了,陈教授。遇见您这样仗义之人,是我的福分。照我的管事给齐先生开的价,我只要一半。”
“那可不成,绝对不成。”陈怀臻紧忙拦住。
“这件宝贝跟了您,又进了您的贝勒府,依旧沾着我们爱新觉罗家族的灵气。我放心了,知足了。陈教授,您就别客气了。”金先生坚持。
一直没说话的常三爷出来打圆场:“要不然取个折中,您二位意下如何?”
刘五爷双手一拍,“好主意。”
怀臻又摆了摆手,“不成。还是依金先生的原价。三十条金子,一两也不能少。不然,我于心不安。”
所有人又为之一震。
金先生抬起泪眼,感激地看着陈怀臻,慢慢站起身来,吩咐身边的管事:“把那件象牙白菜翡翠蝈蝈拿来。”
管事从后厅取来一个花梨木盒,交给金先生。
金先生走到陈怀臻面前,“今天和您结识,实乃三生有幸。我从来没有见过您这样的买家。我依了您,就按原价。可是您也得依我一件事。”
“您说,无不从命。”怀臻赶忙站起来。
“您必须收下我这件赠品,”说着,金先生打开那个精致的黄花梨木盒,里面是用整根象牙精雕细刻的一棵白菜,白菜帮子上面还趴着一个用祖母绿
精雕细刻的绿蝈蝈。活灵活现的翡翠蝈蝈头上,伸着两根同样用翡翠玉石磨成的长长、细细的须子。大家都看呆了,又是一件无价之宝啊!
怀臻大吃一惊:“这怎么行!早就听说有一件象牙白菜翡翠蝈蝈,那是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宝贝,我怎么敢收您这么贵重的厚礼。”
“宝物有价心无价。您的好心比任何宝物都贵重多了。”金先生动情地说,“您要是不接受我这番情谊,就是看不起我。”
齐先生赶紧打圆场:“陈先生,您就收下吧,这可是金先生的一片心意啊。”
怀臻真的很为难,“金先生,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您的这番情谊,我永生难忘。”
“就这么办,”金先生知会下人,“你们务必把这两件宝物仔细包好。”
“金先生,还有一事相求,”齐先生说道,“这件事,还望您保密,别和任何人说。”
“明白,明白。”金先生一口承诺,“一定做到。请陈先生放心。”
陈怀臻等人起身告辞:“金先生,三十条金子明天送到。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两件宝物收藏好。改日请移驾寒舍,给您饯行。”
“一定登门拜望,我还真想再去看看翻新的贝勒府。幸会,幸会。走好,走好。”金先生把客人们一直送到门外。
怀臻等人上了轿车,小崧苼突然发现了什么。
“爸,那是咱们家。”小崧苼高叫了一声,指着对面的北池子八十三号。
“不是了,现在不是了。”
没有人解释,不过小崧苼似乎听懂了。道济轿车静悄悄地向北开去,车上的人没话,都在默默地回味着刚刚发生的一幕。
“小吴,先送刘五爷和常三爷。”
“是。”
道济轿车出了北池子北口,左转弯路过故宫东北角楼前的筒子河。曾几何时,红墙后面就是金先生先辈养尊处优、耀武扬威的地方。如今,竟连祖上
传下来的镇宅之宝也保不住了。怀臻凝视角楼,沉思良久。
“齐先生,三十条金子之外,我想再多给金先生十条金子,也算是对那件象牙白菜翡翠蝈蝈的补偿。”
常三爷摇头:“用不着吧?”
刘五爷也说:“不必,大可不必。”
齐先生说:“三爷、五爷说得是。这太伤金先生的面子,金先生绝不会要。”
汽车静悄悄地驶进景山东街,把故宫角楼和筒子河抛在了后面。
“爸,您说那白菜蝈蝈值多少钱?”小崧苼打破寂静,好奇地问。
“还真不好说,”齐先生代替怀臻回答,“太珍贵了。”
得了两件无价之宝,本应是高兴的事,可是车上的人都沉着脸,乐不起来。陈怀臻心里既有一丝安慰,又有了新的压力。买下这件国宝明明白白意味
着自己要和国宝一起留在北平。不言自明,陈家逃离北平出走的路断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