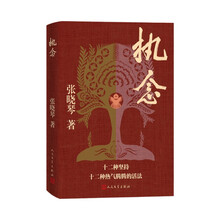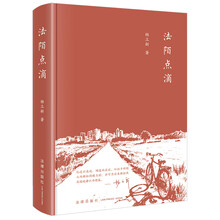洞庭湖畔忆三国
如此,我们可以透过写作,让思绪不住的在多次元的时空之间弹跳,可以引领一个在千百年前就已逝去的战士亡魂,回到他魂牵梦萦的北京城来。
也可以让百花深处的花朵在一组又一组摩登而现代的音韵和弦里在冰封的零度寒夜下绽放。
也因此,你不必再询问作者说,哪个故事是真实的、哪个是虚构的。
翻翻历史书,你就会发现,所谓的历史,说的不就是一部人类的杀戮史么?
我还记得去了岳阳,汨罗江的那一夜,车到了岳阳时已是深夜,我兴奋的拿着导游书跑到旅店的柜台上问人。
“这洞庭湖,是在哪个方向?”
那小姐冷漠的望着旅店漆黑黑的门外说:“你没感觉那风,就从那儿吹过来么?”
我看着黑鸦鸦的门外,实在没能懂她的意思。夜里就自个儿的买了几罐啤酒,在房间里就着窗沿,研究起了洞庭湖畔的三国故事了。我在大乔及小乔浪漫的故事里沉沉的睡去。
几乎是被一阵烈火烙醒那样,我迫不及待的跳到窗口,拉开了窗帘。黄澄澄的湖,喔,说是海么该更贴切些,就在脚下,一望无际的就在湖心点缀了一个金山岛。
我急奔到岳阳楼上,学着孙权在这里操练水师的模样,我在想,我站着的地方,也就是他当年站着的地方。
而昨夜与我这个大王缱绻一夜的大、小乔,现在在哪儿了呢?
那可是一对绝色美女姊妹哪!
先别提孙权大哥可能犯了重婚罪了,我要有两个绝色美女姊妹伴着我,我还干嘛瞎了眼在这洞庭湖上操练兵呢?
搞历史的人挺无聊的,正经八百的,总是记述着谁杀了谁的故事,没什么原创性。我倒认为写作的人多该注意些大人物身边的小人物的浪漫情事,一二国之间杀来杀去的硬梆梆的,就一点都不美了。
而且,政治人物向来乏味,自占皆然,他们常常是五音不全、艺术感极差。我的演艺生涯里最痛苦的记忆莫过于演出时突然有所谓的政要突然冒出来说要合唱一曲的,我跟你保证,如果他们指名要唱某一首歌,而我们乐队奏成另外一首,他们也不会发觉,最厉害的是,他们也可以毫不羞惭的把自己的那一首歌唱完。
所以,你也就别奇怪,为什么他们会穿着短裤、半筒丝袜和黑皮鞋去参加一个晨跑会了。
“我浪费我的时问去提这些人物干嘛呢?”我笑着跟我自己说。
我曾路过这里……
一九九八年,我去了长沙、岳阳和汨罗江。到了汨罗江边上时,已是黄昏,导游先生带我上屈原十三座高冢之中的一座。
五月的风,从远方扬来依然是凉沁袭人的。我坐在三、五层楼那么高的土冢,望着向着西方迤逦而去的汨罗江,夕阳映照在江心上,沿着江边我仰头数着那些说是为欺谩盗墓者而筑的土馒头。
突然在心里涌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动和惊惶。
感动在于,我竟然觉得我曾经路过这些地方。
却也惊惶于除了在历史地理课本上念过之外,我压根就没有来过这个地方。
我请导游让我在土堆上多待些时间,并且笑着跟他说:“你别客气了,我来过这里的。”
我在草上坐了下来,慢慢的整理这些天来的回忆,从长沙、岳阳一路来,一切都显得那么的熟悉。
风中的桂花香、农家的炊烟,昏黄的斜阳就说是在别处儿提时的记忆么。
奇特的是当我望着汨罗江畔一路而去的平原、麦田和土冢,却老实的有种强烈的思乡的感觉。
而教我思念的并不是千里之外的台湾老家,却觉得是沿着江而去的某个地方。
我告诉我自己,就是这个感觉了吧!我的某个祖先,曾经在千百年前沿江而去的,一路迁移到南方去。
而我的潜意识里有这些记忆,而且还可能有更深远的记忆。
于是要如何唤起这些记忆,记述这些记忆,和善用这些记忆,都成有趣的课题。
也许,是太过于感动了,我没能在汨罗江畔写下什么动人的故事与诗歌。
然而,我很欣喜于,由于这些不住的移动,却能引领我进入一个惯有的个人生活里,不常有的领域。如此,我有了更新、更无限的元素,可以在脑子里建构一个更有趣的拼图。
写作就成了一种可以超越时空、象限的游戏了。
北京一夜
在“北京一夜”这样的歌里,就让作者飘移在过去与未来,甚或摩登与古典那样的情境里。
也是缘起于那种假设要飘移才能产生的创作上的心境落差。在九○年冬天,我约了编曲正帆去了北京。我们挑了比较有名、有信誉的“百花录音棚”进行录音的工作。
其实在创作上某些习惯的改变,是没什么道理的,台湾的录音条件与水平,并不输给其他的先进国家。我常常在多年以后被问及为什么要那么痛苦的去北京、去纽约、去伦敦录音,那不是什么虚荣的心理,之于我,也实在说不上来有什么伟大能通的道理。唬烂的说,是北京的涮羊肉好吃吧!
就去了!
也就是去了,北京的录音棚,真的大得像个棚子或体育馆。
于是你就开始虚荣于那种大又便宜些的感觉了。
我说那是自然的,要思考一件事情,当然是越人的空间越好。
我跟正帆,在那个大棚子里工作了七、八天,都有点受不了了。我没告诉他,其实,我的期望更高于手上的进度。我开始感到不耐烦,也自责于没能好好的引领着编曲,却总是将他塞进死胡同里。
夜已深了,录音师没精打采的。我到屋外去抽了根烟,顺便挑了几块砖头发泄似的往那胡同里的公共厕所里摔。
我心里在想,还好有这些砖头,不然,我就要摔我的编曲了,摔完了编曲再摔录音师、摔乐器,然后放把火把自己跟录音棚都给烧了。
不盖你,我偶尔会那样恐吓我的音乐工作伙伴,我会说:“如果,你不逼迫你自己,想出点东西来,我就杀了你,然后,我就自杀。”有点吓人。不过那也就是那么些个“意态”。我常常觉得如果“意态”很充分了,就比杀了别人、杀自己有效多了。
屋外的气温降到了零下,胡同里映着一些残雪的反光,我竖了竖衣领,点了我的第八根烟。
棚里零零落落的传出正帆无助的钢琴声。捻起烟头,准备朝公共厕所里扔去,我认定那里面一定充满了沼气,这烟头一下去肯定会把这死胡同,连同我炸到九霄云外去,那就一了百了了。
突地看见挂在胡同口上的路牌。
“百花深处……”
“百花深处……”操你妈的百花深处,我在心里嘀咕着。
“什么意思啊!”屋外冷得要死,我咒骂着自己,心里只想回我那温暖的南方的家。脑子里不停的用闽南语还嘀咕着:“我哪惦北京?我哪惦北京?”
“我哪惦北京?”念着念着就想笑了。
“对呀!我好好的温暖南方不待,怎么的跑到这共匪的地盘上来干嘛呢?”忘了方才那股气急攻心的感觉,一阵阵的酥麻又涌上了心头。
不由得哼着个莫名其妙的旋律起来,还配上了不闽南、不英的歌词。
“我哪惦北京?我哪惦北京?……one night in Beijing……”
“狗屎!不玩了,弄得我都快疯了,我想跟正帆说不玩了。明天收一收回台北去了。”
现在我们把那些狗尿音乐扔了,到巷子口的涮羊肉店,喝他个烂醉吧!我推开棚子,冰凉的空气弄得大家嚷嚷,我站在棚门口,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发配到塞外去打了一场烂仗的秦俑,不知自己已死去了千年,拖着一身已锈烂的铁衣和结成冰的伤痕血水,回来了。
“给我开城门啊!给我开城门啊!”我心里呐喊着。
屋里的人,看我大概就像是个从零下里冒出来的冰人,瞠目结舌的。
“发什么神经啊!”好像有人笑骂着。
“好了,好了,不玩了,我们去吃消夜了好么?正帆好兄弟!不欺侮你了,我们去喝个烂醉怎么样?”
“反正也赶不上什么狗屎进度了。”我想。
炉子上了桌,酒过三巡,我盯着胡同口的路牌看。玻璃窗外新街口,夜已深了,路上只有些稀稀疏疏的车,没了行人,昏黄的街灯,反射在新落的薄雪上。
“操!大浪漫了吧?”
“这录音棚的地方,早先,是清朝了吧?本来就是个大官邸,住了个什么前清皇族的官邸,总的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花园。从新街口这儿进去,是真要穿过一个很大的,百花齐放的花园的。”
“哇!那我刚刚扔到厕所里的那个砖块,都是前清古董罗?”是真是假,自己也搞不懂了。
“所以哪!我们那棚子才叫百花,这胡同哪!就叫百花深处了。”
“嘿!嘿!”我看我几个朋友,八成是一下冷、一下热的,还或者是故事太迷人了,都像忍住了泪水,干笑着说不出话来了。
“别瞎掰了,哪有那么浪漫。”还好我的编曲还会说话。
“真的,胡同口的路牌边上有介绍的,你去看看。”
“是真的,除非整个北京卯起来骗你,我刚刚去看了那牌子,要不那紫禁城、结了冰的颐和园,怕不都是骗人的。”我自己都觉得是场梦了。
“我哪惦北京?我哪惦北京?……one might in Beijing……”
我跟正帆站定在百花深处的牌子前,二锅头酒的暖意才上心头,两个人似乎都有些了默契,兴奋莫名。
“先别管手上那些电影配乐什么的。就这感觉,我们来弄一个北京的歌。”
“马上?”
“马上!”
“用直觉,就用现在对北京这城市的直觉。冰寒的天、秃了的枝桠、夜月、闭锁不开的天安门,等待着出征的人们归来的老妇。”
不由自主的我又唱了起来,学着小时候胡乱看的京剧调调。
“One night in Beijing,我留下许多情。”
“真过瘾!”
“没错,真过瘾!”
“那是你先给我四或八个和弦,我再走,还是,我先给你主线和画面。”
“一起来,一起来,比较好玩,你刚刚那样唱的就是了,其实我们已经完成一半了对不对?”老战友会知道彼此往下的招式。
“那好,我的下一句是……”
街上行人已稀,又起阵寒风,风中斑斑点点的有些冰晶,非常好看。
而我又彷佛听见遥远的北方,传来了阵阵的狼嗥。
“啊!那儿,果真是狼的故乡啊!”我在想。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