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配件门市部
一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博文,说新疆大盘鸡是我发明的。博主叫“飞行员”,自称是我早年的朋友,二十多年前的一天,他从乌鲁木齐到我家做客。正是秋天,门前菜园的蔬菜都长成了,院子里养的鸡娃子也长大了。我妻子很热情地宰了一只鸡,摘了半盆青辣子,整个鸡剁了跟辣子炒在一起,里面还加了土豆芹菜,盛在一个大盘子里端上来。他从来没见过这种吃法,就问这叫什么菜?我脱口说出“大盘鸡”。
那时这一带的饭馆都有炒鸡的,有叫辣子鸡,有叫爆炒小公鸡,都不叫大盘鸡。他说我把大盘鸡这个名字叫出来后,所有的鸡都跟辣子整个炒了,都装在大盘里,都开始叫大盘鸡。
我在相册中看见一张旧照片上头戴飞行帽的博主,站在一架很老式的小飞机下面,冲着我笑。他是我的朋友旦江。早年我在沙县城郊乡当农机管理员时,他在首府开飞机,是我们县出去的唯一一个飞行员。多年不见的朋友在网上遇见,就像在梦中梦见一样。我和旦江的认识也像一场梦,我那时早就知道每天头顶过往的飞机中,有一架是我们县的旦江开的。但我从来没想过会认识旦江。那个时候,认识一个汽车驾驶员都觉得风光得很。谁会想到认识飞机驾驶员。可是,我妻子金子的同学帕丽跟飞行员旦江结婚了。帕丽在县电影院上班,是金子最好的朋友。有一天,帕丽把飞行员旦江带到我家,我和旦江吃着金子炒的大盘鸡,喝了两瓶金沙大曲,很快成了好酒友。以后旦江只要回沙县,帕丽就带着来我家,金子每次都炒大盘鸡,我和旦江你一杯我一杯喝到半夜。后来我到乌市打工时,旦江已经转业到一个旅游公司当办公室主任。有一阵子旦江家就是我的家,我经常去他家混饭吃。金子来乌市时我们也一起住他家。帕丽和旦江都是好热闹的人,常在家里招待朋友喝酒。旦江家的酒宴,直到有一天帕丽出车祸下身瘫痪。那时金子已经调到乌市工作,我们在城里有了自己的家。金子依旧常去看帕丽,每次都买一只鸡带去,给帕丽炒大盘鸡吃。我却因为忙很少去他们家了。只听金子说帕丽瘫痪后,旦江办公室主任不干了,值夜班给公司看大门,这样白天可以在家照顾帕丽。
我在旦江的博文中没看到有关帕丽瘫痪的事,有几篇文章写他早年的飞行经历,一篇写到他开飞机飞过家乡沙县的情景,他违章把飞机高度降低,几乎贴着县城飞过。他本来想从自己家房顶飞过,但整个县城的房顶看上去都差不多,他从天上没找到自己的家。
旦江的文章一下把我带回到二十多年前那个小县城。我问金子要来旦江家电话,拨号时突然觉得这个号码是多么熟悉,好多年前我曾背熟在脑子里。
我说:旦江你好吗,听出我是谁了吗?
旦江说:你的声音我能忘掉吗?你现在成名人了,把老朋友都忘记了。
我说:我看到你的博客了,你在那里胡说啥,大盘鸡怎么是我发明的?
旦江说:大盘鸡就是你发明的,你干了这么大的事你都忘了吗?
旦江的口气非常坚定。他说每次吃大盘鸡,他都自豪地给朋友介绍大盘鸡是我发明的。他写的博文也早在网上流传开了。
旦江的话让我有点恍惚,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只记得大盘鸡刚兴起那会儿,我在城郊乡农机站当管理员,开了一个农机配件门市部,我是否发明过大盘鸡,真的记不清了。我从十九岁进农机站工作,到三十岁辞职外出打工,这近二十年的时间,我干过多少重要的事情都忘记了,包括是否真的发明过大盘鸡。可是,我开农机配件门市部这件事却一直记得。那是我年轻时干的最隐秘的一件事,到现在没有人知道,我挂着卖农机配件的牌子,开了一家飞机配件门市部。
二
每天有飞机从县城上空飞过,从我的农机配件门市部房顶飞过。我住的县城在一条飞机路下面。我注意到天上有一条飞机路是在开配件门市部以后。门市部开在城东,那里是三条路的交会点,从东边南边北边到县城的路,都会到这里。我看到飞机的好几条路也在头顶交会。由此我断定飞机是顺着地上的路在飞,因为天上并没有路,飞机驾驶员盯着地上的路飞到一个又一个地方。这个发现让我激动不已,我本来想把我的发现告诉单位的老马,老马说他坐过飞机,不知是吹牛还是真的。我和老马骑自行车下乡,头顶一有飞机过,老马就仰头看,然后对我说,他坐过的就是这种飞机,或者不是。老马能认出天上飞机的型号,就像一眼看出拖拉机的型号一样,这让我很是佩服。有几次我都想问老马,他坐在飞机上是否看见下面有一条路。但我没问。我觉得飞机顺着地上的路在飞,这肯定是一个重大的秘密。如果我说出去,大家都知道了飞机沿着地上的路在飞,飞机就飞不成了。因为飞机是有秘密的。没有秘密的东西只能在地上跑,像拖拉机。拖拉机没啥秘密,我是管拖拉机的,知道它能干啥,不能干啥。尽管我时常梦见拖拉机在天上飞,那都是我在驾驶,我的梦给了拖拉机一个秘密,它飞起来。飞机的秘密注定是我们这些人不能知道的,那是天上的东西,即使被我这样的聪明人不小心知道了,我也要装不知道。给它保住密。
我跟飞机的秘密关系就这样开始了,虽然我没坐过飞机,连飞机场都没去过,但我知道了飞机的一个大秘密,它顺着地上的路在飞。我们天天行走的路原来有两层,下面一层人在走车在跑,上面一层飞机在飞。地上的人除我之外都只能看到一层,看不见第二层。有时我往西走,看见一架飞机在头顶,也往西飞。我就想,我要一直走下去,会追上这架飞机。但我不会追它,我不是傻子。我们县上有一个傻子,经常仰着头追飞机,顺着路追。我不清楚他是否也知道飞机沿着路飞的秘密。他后来被车撞死了。
飞机飞来时路上的行人都危险,因为好多开车的司机头探到驾驶室外看飞机,骑自行车的人仰头看飞机,这时地上的路只有飞机驾驶员在看。我知道飞行员在隔着舷窗看路,就故意挺直胸脯,头仰得高高,不看飞机,很傲气地望更高处的云和太阳,我想让飞机上的人看见我的高傲,知道路上走着一个不一样的人。
我确实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在我二十岁前后那些年,我跟这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后来就一模一样了。
三
星期天,金子带着帕丽来到配件门市部,自行车停在门口,两人站在墙根望天。金子说,帕丽的飞机要过来了,旦江给帕丽打电话了,他今天开飞机去伊犁,路过沙县。
我早知道帕丽的男朋友是飞行员。帕丽经常给金子说旦江开飞机的事,晚上金子又把帕丽的话说给我。旦江一年到头回不来,旦江开的飞机却经常从县城上空飞过。全县城的人都知道我们这里出了一个飞行员,他开的飞机经常从县城上空飞过,这是帕丽告诉大家的。帕丽经常带着朋友看飞机,好多人把旦江开的那架飞机记住了,一听见飞机的声音就说,看,帕丽的飞机过来了。帕丽带着朋友在县城许多地方看飞机,到我的农机配件门市部前面来看是第一次。金子说,她让帕丽到这里来看的,她跟着帕丽到好多地方看过飞机,都没有城东这一块飞机多。
金子很少来配件门市部,她不喜欢店里机油黄油柴油还有铁生锈的味道。那就是一台破拖拉机的味道。金子不喜欢拖拉机,不喜欢满身油污的拖拉机驾驶员到家里来。尽管拖拉机驾驶员都不空手上门,不是提一壶清油,就是背半袋葵花籽。那些驾驶员坐在她洗得干干净净的沙发单上,跟我说拖拉机的事。金子不爱听,就到门前的菜园收拾菜地。配件门市部开张后金子只来过有数的几次,她怎么知道这一块天空飞机最多呢?
金子说听见飞机声音了,喊我出去。飞机先是声音过来,天空隆隆响,声音比飞机快,从听到声音到看见飞机,还得一阵子。我把路对面的小赵,路拐角的饭馆姚老板,还有电焊铺的王师傅都叫出来,一起看飞机。隆隆声越来越大,东边的半个天空都在响。飞机的声音只有链轨拖拉机能和它比。飞机就是天上的拖拉机,一趟一趟地犁天空。早年我写过一首叫《挖天空》的诗,在那首诗里,我的父亲母亲,还有一村庄人都忙地里的活,我举着铁锨,站在院子里挖天空。我想象自己在天上有一块地。后来我看见了飞机,知道天上已经没我的事了。
帕丽尖叫起来,说来了来了,我们往帕丽指的天空看,一个小黑点在移动,帕丽使劲朝小黑点招手,金子也跟着招手,还尖着嗓子喊,飞机在她们的招喊声里很快飞到头顶,飞机从头顶过的时候,我感觉它停住了,就像班车停在路上等客一样。帕丽挥着红丝巾跳着喊旦江旦江,金子也跳着喊,好一阵子,飞机一动不动停在头顶。
我说:帕丽,你看旦江把飞机停下让你上去呢?
帕丽顾不上跟我说话,她仰着脸,挥着红头巾,本来就苗条的身体这下更苗条了。她的腿长长的,屁股翘翘,腰闪闪,胸鼓鼓,脖子细细,下巴尖尖,鼻子棱棱,眼睛迷迷,整个身体朝着天上。
飞机开始慢慢移动,要是没有那几朵云,几乎感觉不到飞机在移动。但一会儿,人的脖子就开始偏移。我看见帕丽的脸仰着,整个人都像一个梦幻。我就想:我一个人在梦中飞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人这样痴迷地仰着脸看呢?
帕丽的脸渐渐往西边扭过去的时候,飞机就小得剩下一点点了。帕丽说,她想爬到门市部房顶上看飞机,让我赶快搬梯子来。金子也让我赶快搬梯子。我磨蹭着说梯子在房东的院子里,不好搬。又说梯子坏了。说着说着飞机看不见了。飞机的声音还在,过一会儿声音也没有了。
四
我选择在城东开店是动了些脑子的。我们这里的人分动脑子和动身子两种。我身体不如别人强壮。但脑子多。这是老马说的。老马根据我和他下象棋的路数,知道我的脑子比他拐的弯多,我给他让一个车,他都老输。不过不久后老马又说,可惜你的脑子动偏了。老马嫌我的脑子没用在工作上,私自开一个农机配件门市部,经常不去单位上班。
我开店的城东是一个破烂的小三角地,路上坑坑洼洼,路边很早就有一家汽车修理铺,和一个电焊铺。我的农机配件门市部离它们有一截子路。我不喜欢那个电焊铺切割铁的声音,刺刺剌剌,像割肉一样。我在三岔路口的西面租了间里套外的房子,里面库房兼卧室,外面营业,房租每月六十元。这真是一个卖零配件的绝好地方,门口车流不断。经常有从乡下开来的拖拉机,突突突突开到这里坏掉。也有汽车摩托车开到这里坏掉。那时候从乡下到县城的路都不好走,大坑小坑,那些破破烂烂的拖拉机,好不容易颠簸到县城边,就要进城了一下坏掉。县农机公司在城西。农机修理厂也在城西。要在以前,坏车会被拖到城西修理。现在不用了,城东有我的配件门市部。开车的师傅提摇把子进来,问我有没有前轮轴承。我说有。问我有没有活塞。我说有,啥都有,都在库房里。库房远吗?不远,十分钟就拿来。
我骑摩托一趟子跑到城西县农机公司,花十几块钱买一个轴承,回来二十几块卖给等待修车的师傅。这些精密零配件只有农机公司有,农机公司零配件齐全。我的门市部摆放的大多是常用的粗配件,比农机公司的便宜,就是质量差一点,这个我知道。我进的是内地小厂子的货。正规厂家的配件我进不起,人家要现金。小厂子的货款可以欠。经常有推销农机配件的人,来到门市部,拿着各种农机配件样品,我跟推销员谈好价格,签一个简单的购销合同,不用付定金,过半个月,货就到了。再过一个月,推销员过来收款。前面的款结了,不合格的零配件退了,再进一批新货。有时钱紧张,货款还可以拖欠,越欠越多。两年后我的门市部卖掉时,还欠了一个河北推销员的一千多块钱。在以后的几年中,那个推销员找过我好多次,我的门市部关门了,他问对门理发店的小赵,小赵告诉他我们家住在园艺场,他找到园艺场,我大哥说我搬到县城银行院子了,找到银行院子,我岳父说我到乌鲁木齐打工去了。那几年,只要我回去,就能听到有关河北推销员在找我要货款的事。他们还告诉了我在乌鲁木齐打工的单位。我想着那个推销员也许找到我最早打工的广告公司,又找到后来打工的报社,我换单位的频繁肯定使他失去继续找下去的耐心,也许他还在找。而那些卖剩下的配件,也一直在园艺场的旧房子里堆着。我也一直想找到这个推销员,他发给我的劣质转向杆弯头,因为断裂导致好几起车祸。有一起车祸是转向杆弯头断了,小四轮方向盘失灵,撞进渠沟,坐在车斗上的一个人当场摔死。车主找我麻烦,我说配件是厂家生产的,去找厂家。车主说就不找厂家就找你。我没办法。我也想找到那个推销员。我一直等着他找上门来,等得我都快把他忘记了。就在不久前,我竟然梦见了他,我开着小四轮拖拉机,拉着一车斗锈迹斑斑的劣质农机配件,去河北找这个推销配件的人,我找到生产配件的厂子,门口蹲着一个很老的人,说厂子早倒闭了,我觉得这个老人面熟,又想不起是谁。问合同上的推销员,那老头给我指了一个大山中偏远的村子。我开着小四轮往山里走,走几里坏一个零件,我不断地下来修理。坏的全是我车上拉的那个转向弯头,直到我把车上的弯头全换完,小四轮也没有开到地方。我茫然地坐在坏掉的拖拉机上,前后都是没有尽头的路,坐着坐着我醒来。
醒来我才想起来,那个坐在厂门口给我指路的老头,就是我要找的推销员,他曾多少次到配件门市部,跟我签了好多个购销合同。我在梦里竟然没认出他,反让他又骗了一次。
五
那是我一生中最清闲的几年,我在乡农机站当统计和油料管理员。统计的活是一年报两次报表—半年报表和年度报表。这个活我早就干熟练了,不用动腿也不用动脑子,报表下来坐在办公室一天填完,放一个星期再盖上公章报到县农机局。农机站的公章我管。站长老马对我很放心。管公章是一件麻烦事,每天都有来开证明的驾驶员,那时去外面办个啥事都要开证明。马站长文化不高,字写得也不好,经常把证明开错,让驾驶员白跑一趟县城。后来他就让我写证明,写好递给他盖章。再后来就把公章交给我了。农机站有两个管用的章子,公章和我的私章,都在我手里。私章是在供油本上盖的,挂在我的钥匙链上,我经常不在办公室,我和老马都喜欢下乡,来办事的驾驶员就开着拖拉机四处找我们。大泉乡有十二个村子,西边七个,东边五个。驾驶员先开车到十字路口的小商店门前,打问我们朝哪个方向走了。小商店更像一个不炒菜的小酒店,门前一天到晚坐着喝散白酒的人,浓浓的酒味儿飘到路上。我和老马骑自行车路过,常有人喊马站长过去喝酒,老马知道下去有酒喝,就说不了,忙呢。
只要我们下到村里,拖拉机师傅马上把机器停了,不管是在耕地还是播种,都停了,剁鸡炒菜陪我们喝酒。驾驶员说得好,你们也不是经常来,耽误就耽误半天。酒喝到一半,听到突突的拖拉机声,办供油证的驾驶员找来了,他们在小商店门口打问清楚我们朝东走了,就在东边的几个村子挨个找,很快找到了。
春天播种时我们必须要下村里,检查工作的内容每年都不一样,有时是督促农民在种子中拌肥料,有时是让农民把单行播种改成双行,这就要改造或购买新播种机,过一年又重新改成单行。但有一个内容每年不变,就是让驾驶员必须把路边的庄稼都播直,这样苗长出来好看。路边的庄稼都是长给人看的,那是一个乡的门面,上面检查工作的领导,坐小车扫一眼,就知道这个乡农业种植抓得好不好。所以,路边的庄稼一要播直,有样子。二要把县上要求必须种的庄稼种在路边。三要把肥料上足,长得高高壮壮,把后面长差的庄稼地挡住。
老马干这个工作很卖力,看到有驾驶员播不直,就亲自驾驶拖拉机播一趟。下来大声对驾驶员说,把眼睛往远里看,不要盯近处,盯着天边边上的云,直直开过去,保证能播直。驾驶员都佩服他。
我从来没开链轨车播过种,不知道照老马说的那样眼睛盯住天边的云一直开过去是什么感觉。那些年我的注意力都在天上。我写的一首叫《挖天空》的诗,发表在首府文学杂志上,好几年后我见到杂志编辑,她向同事介绍我说:这就是那个站在院子里,拿一把铁锨挖天空的人。
那是我写的许多天空诗歌中的一首。我天天看天,不理识地上的事情,连老马都埋怨我,嫌我工作不认真,懒。他不知道我这个乡农机站的统计员,在每天统计天上过往飞机的数字。
六
每天都有飞机从县城上空飞过。我把从东边来的飞机叫过去,从西边来的叫过来。我在笔记本上记今天过来一个,过去一个,别人看不懂我记的是什么。有时候过去三个,过来两个,一架过去没过来。我就想,那架飞机在西边的某个地方过夜,明天会多一架飞机过来。可是,第二天,过去三个过来三个,那架过去的飞机还没过来,我想那架飞机可能在西边过两天再过来,第三天那架飞机依旧没过来,第四天还是没过来,我就想那架飞机可能不过来了,一直朝过去飞,这样的话,它就再不过来。有些东西可能只过去不过来。
也可能它在什么地方落下来,就像拖拉机坏在路上。飞机不会坏在天上。它坏了会落下来。或者落在沙漠,或者落在麦田,或者落在街道。飞机太可怜了,它在地上可落的地方不多,除了机场,它哪都不能落。它没过来,肯定是落在哪了。
夜里过飞机,我会醒来,从声音判断飞机是过来还是过去。有时我穿衣出去,站在星空下看。飞机的灯很亮,像一颗移动的大星星,在稠密的星星中穿行,越走越小,最后藏在远处的星星后面看不见。
如果我醒不来,飞机的声音传到梦里,我会做一个飞的梦。我从来没在梦里见过飞机,只做过好多飞的梦。一个梦里我赶牛车走在长满碱蒿的茫茫荒野,不知道自己往哪走,也许是在回家,但家在不在前方也不知道,只是没尽头地走。走着走着荒野上起黑风了,我害怕起来,四周变得阴森森,我听到轰隆隆的声音,像什么东西从后面撵过来,我不敢回头看,使劲赶牛,让它快跑。轰隆声紧跟身后,就要压过头顶了,牛车一下飞起来,我眼看见牛车飞起来,它的两个轮子在车底下空转,牛的四个蹄子悬空,我还看见坐在牛车上的我,脑门的头发被风吹向后面,手臂高高地举着鞭杆。隆隆的声音好像就在车厢底下,变成牛车飞起来的声音。
另一个梦里我开着链轨拖拉机播种,眼睛盯着天边的一朵云,直直往前开。这是老马指导驾驶员播种的动作。在梦里我的视线很弱,周围都迷迷糊糊。或许是梦把不相干的东西省略了,梦是一个很节省的世界。我努力往远处看的时候,那里的天和地打开了,地平平地铺向远处,天边只有一朵云。我紧握拖拉机拉杆,盯着那朵云在开,突然听见头顶隆隆的声音,一回头,发现拖拉机已经在天上,我眼睛盯住的地方是遥远的一颗星星,拖拉机在轰隆的响声里飞起来,后面的播种机在空中拉出直直的播行。
更多时候我自己在飞,我的手臂像飞机翅膀一样展开,额头光亮地迎着风,左腿伸直,右腿从膝关节处竖起来,像飞机的尾鳍。过一会儿又左右腿调换一下姿势。
我飞起来的时候,能明白地看见我在飞。看见带我飞翔的牛车和拖拉机车底的轮子。自己飞起来时我看见我脸朝下,仿佛我在地上的眼睛看见这些。我在天上的眼睛则看见地上。
那时我还没坐过飞机,也没有机会走近一架真飞机,我甚至没有去过飞机场,不知道飞机是咋飞起来的,我看见的飞机都在天上。我的梦也从不会冒险让我开不熟悉的真飞机,它让我驾驶着牛车和拖拉机在天上飞,那是我梦里的飞机。我这样的人,即使在做梦,也从来不会梦见不曾拥有过的东西。
只要做了飞的梦,我就知道夜里听见飞机的轰隆声了。飞机的声音让我梦中的牛车和拖拉机飞起来。飞机声越来越小的时候,我回到地上。有时在半空中梦突然中断,我直接掉落在床上,醒来望望窗外,知道有一架飞机刚刚飞过夜空。
我把跟飞有关的梦记下来。我喜欢记梦。我在农机站那几年,记满了一个日记本的梦。飞的梦最多。我经常梦见自己独自在天上飞,有时一只手臂朝前伸出,一只并在身边,有时像翅膀一样展开。腿有时伸平,有时翘起一只,像飞机的尾鳍。我变换着各种姿势,让飞的样子尽量好看,我不知道谁会看见。我在天上飞时,一直没遇见飞机。那样的夜晚,飞机在远处睡觉,或者从来就没有飞机。或许一架飞机正在飞过,我被它的轰隆声带飞起来。这样的夜晚有两个天空。一个星云密布,飞机轰隆隆地穿行其间,越飞越远。而我做梦的天空飞机还没有出世,整个夜空只有我在飞。
七
帕丽又来配件门市部看飞机。自从金子带她来看过飞机,她就认定城东这一块飞机最多,旦江的飞机不管从哪开来,总要经过这里。帕丽来时先约上金子。有时金子先到,坐在门口等帕丽。有时帕丽先到,站在路边等金子。帕丽和金子一样不喜欢进配件门市部,不喜欢货架上油乎乎的铁东西和里面油污铁锈的味道。但她喜欢跟我说话,说话时眼睛直勾勾看着我。
帕丽每次来我都有点紧张,她当着金子的面也眼睛直勾勾看我。她仰脸看飞机时眼睛却是迷幻的。好多看飞机的人眼睛都不一样。飞机过来时,我的注意力都在看飞机的人身上。我不喜欢跟一群人看飞机。我喜欢一个人站在荒野,仰头看一架飞机在天上。可是那样的时候很少,因为飞机顺着地上的路在飞,它经常飞过的地方,必定是人多处。人多眼睛就多,心思也多。越来越多的人跟着帕丽来城东看飞机,我担心飞机的秘密会保不住。大家都知道了城东这一块飞机最多,他们会不会也想到这里是飞机的交叉路口,进一步想到飞机是顺着地上的路在飞呢。
后来我相信或许没有人这样去想。这样想事情要有这样的脑子,好多人的脑子不会往天上想,大多是凑热闹看看飞机,又低头忙地上的事。哪有我这么闲的人,天天看天。
帕丽很早就知道我是诗人。我和金子谈恋爱那时,金子带我去看帕丽,金子说我是大泉乡农机站的,帕丽看我一眼,对金子撇撇嘴。金子又说我会写诗,是诗人。帕丽眼睛亮了一下。那时帕丽还没跟旦江恋爱,我也不知道每天头顶过往的飞机有一架是我们县的旦江开的。我只是喜欢看飞机。我和飞机的缘分很小就结下了,村子旁种了大片的蓖麻,大人说,蓖麻油是飞机上用的。那时我连天上的飞机都很少见过。但蓖麻油是飞机上用的这句话却影响了我的童年,我经常一个人钻进蓖麻地,隔着头顶大片大片的蓖麻叶子看天空。后来每当我看见飞机,就想起大片的蓖麻地。再后来我开了这家农机配件门市部,开了两年,这期间我为小时候的梦想做了一件事。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我开的是一家飞机配件门市部。
帕丽来看飞机都打扮得很漂亮惹人。我知道好多年轻人是追着看帕丽来的。帕丽不怎么理他们。飞机没来时帕丽就眼睛看着我说话,我不记得她说过些什么,只看见涂得红艳艳的嘴唇在动。她说起话来嘴唇不停,我根本插不进话。她可能只是想让我听她说话,并不打算听我说什么。
那天帕丽翻看我的笔记本,上面有我写的诗。我把写好的诗记在一个硬皮笔记本上,放在门市部柜台里。
帕丽说,你写的诗真好,我一句都读不懂。
帕丽说,我早就给金子说,让你给我也写一首诗。金子经常说你给她写诗,把她写得美极了。金子说,她给你说了,你不写,说你只给她一个人写诗。
我看着帕丽说,写诗要有灵感。
帕丽说:怎样才能让你有灵感?帕丽眼睛直勾勾看着我。她不知道我把她写到诗里该是多么美,她本来就美。
一次,帕丽从乌鲁木齐回来,给金子说,旦江带着她坐飞机了,旦江开着飞机,她就坐在旦江旁边。她还说,飞机没有方向盘,旦江在天上手放开开飞机,就像那些男孩子双手撒开骑自行车一样。
那飞机转弯的时候咋办?金子问。
朝左拐的时候,旦江朝左挪一下屁股。往右拐的时候,就右挪一下屁股。帕丽说。
金子唯一能向帕丽夸耀的是我把她写到了诗里。在帕丽看来,我把金子写进诗里,就像旦江把她带到天上一样神奇。她不知道被写进诗里是什么感觉。就像金子不知道坐在开飞机的旦江身边是什么情景。
晚上熄了灯,金子给我说,她听帕丽说坐着旦江开的飞机,在云上飞来飞去,可羡慕了。说跟着我到现在只坐过小四轮,突突突突的,黑烟直往嘴里冒。
金子说话的时候,我面朝房顶黑黑地躺着,我在等一架飞机,我知道每晚这个时候,有一架飞机过去,然后到半夜,又有一架飞机过来。我得等它过去了再睡着。有时候好多天没有飞机过去,我等着等着睡着了。这个晚上飞机会不会过来呢?我眼睛朝上望时,能直接穿过房顶看见星空。
过了一会儿,金子侧身钻进我的被窝,我把金子搂到怀里,金子说,帕丽也很羡慕我,我给她说,你给我写了好多诗,她都羡慕死了。我给帕丽说,我们家老公写诗的时候,脑子都在天上转,跟飞机一样。金子说,帕丽想让你给她也写一首诗。我说我们家老公只给我一个人写诗。
就在这时我听见飞机的声音,整个天空轰隆隆地在飞,我突然翻过身,像我无数次在梦中飞翔的那样,脸朝下,胸脯朝下,手臂展开,一下一下地朝上飞,身体下面是软绵绵的云,她托举着我,越飞越高。
八
我不统计梦见的飞机,尽管我知道夜里有飞机过,被我以飞的方式梦见了。但我不统计,也从来不估计。不像我做农机报表,有的村子太远,去不了,不想去,就把去年的报表翻出来,以去年的数字为依据,再估计着加减一个数字,就行了。其实去年我也没去过这个村子,去年的数字是在前年基础上估计的,前年的数字从哪来的呢?肯定是在大前年基础上估计的。好像每年都顾不上去那个村子,它太远,站上又没小车,骑自行车去一天回不来,遇到下雨,路上泥泞,几天都走不成。我做年终报表的时间很紧迫,报表发下来,到报上去,也就一周时间,全乡十几个村子,一天跑一个,也不够。一天最多能跑一个村子,上午去到几个农机户问问数字,进了门肯定是出不来的,统计数字的时候,外面院子已经在剁鸡炒菜了,数字没统计完,菜已经摆上桌子,主人说边吃边喝边统计,酒一喝开就数指头划拳了,谁还有兴趣给你报数字,一场酒随便喝到半下午,剩下的时间,就仅够骑自行车摇摇晃晃回家。所以报表来了,就近村子跑跑,远点的就顾不上。
每年这样,我在大泉乡的好多年,年年做报表,全乡十四个村庄,有一个村庄我可能从来没有去过。我只是从统计报表中知道这个村庄叫下槽子,知道村里有一台链轨拖拉机,一台东方红28胶轮拖拉机,这个数字咋来的我忘了。可能是我到农机站那年随便填的,我调到这个乡农机站是那年的十一月,上班没几天局里的年报就来了,要求一周内报上去,下去每个村子跑数字显然来不及。我找出去年的年报,挨个地抄数字,给一些村子增加一些拖拉机,因为农机保有量每年都要增加的,这个叫下槽子的村庄竟然没有拖拉机,我觉得不可能,一个村庄怎么能没有拖拉机呢,没拖拉机地怎么耕呢,我很冲动地给它加了一台链轨拖拉机,又觉得它还需要有一辆搞拉运的轮式拖拉机。后来我弄清楚那是个牧业村,地少,一直雇用邻村的拖拉机耕地。但是晚了。拖拉机已经填在报表上,不可能画掉。只能再增加,我觉得它还应该有几台小四轮拖拉机,以后几年我就每年给它增加一台小四轮拖拉机,我的胆子小,不敢一下加太多,觉得加多了心里不踏实,就一年年地加吧,因为加一台拖拉机,就要为它编一个车主的名字。这个车编给谁家呢。我到乡派出所找到下槽子村的户口簿,把两台大拖拉机落到两个大户人家,小四轮就随便落了,反正这些人家迟早都会有拖拉机的。
每年我都想着去下槽子村看看。或找个下槽子村的人问问情况。可是,从来没有下槽子村的人到我办公室办过事。好像那个村庄没有事。我给站长老马说,我们抽空去趟下槽子吧。老马说太远了,去了一天回不来。
那个让人一天回不来的村庄,就这样阻碍了我。
九
帕丽飞机不来的日子,我一个人看飞机,听到天空隆隆的声音我从门市部出来,仰头看一阵,把飞机目送走,然后回店里,在笔记本上记下过来或过去。其实坐在店里听声音就知道飞机是过来还是过去,我出来是让飞机看见我。因为我知道飞机驾驶员眼睛盯着这条路,其他地方或许他会一眼扫过,但是这个三岔路口他会仔细看,三条岔道通三个地方,走错就麻烦了。他探头下看时,准会看见仰头望天的我。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在望。他会不会被我望害怕?
理发店小赵也喜欢看飞机。只要听见飞机响声,准能看见小赵站在路上,脖子长长地望天,有时手里还拿着剪刀,店里理发的人喊她,她也不理识。小赵看飞机的样子和帕丽一样好看,我站在对面,看一眼小赵,望一眼飞机。小赵因为喜欢看飞机,我觉得她跟别的女孩不一样。喜欢看飞机的女孩腰身、脖子、眼光都有一种朝上的气质,这是我喜欢的。我和小赵时常在飞机的隆隆声里走到一起。有时我把飞机看丢了,小赵就凑过来,给我指云后面的那个小点。小赵指飞机的时候,我看见她白皙的胳膊,细细的手指,一直指到云上。
小赵美容店的名字是我写的。配件门市部开张的第二个月,路对面开起一家美容店。店主小赵和我妹妹燕子很快成了朋友。小赵听燕子说我会写诗,是个文人,就让我给理发店起个名字。我想了半天,没想出来。小赵说,你先给我写上“美容店”三个字吧,以后想好名字再加到前面。小赵要去买红油漆,我说我店里有。我写招牌时买了一大罐红油漆,剩好多呢。
写字时我站在凳子上,小赵在下面给我举着油漆罐。“美容店”三个字直接写在门头的白石灰墙上,跟我的“农机配件门市部”一样。我写一笔,刷子伸进油漆罐蘸一下,有一点红油漆滴在小赵的手上,小赵的手又小又白皙,她的脖子也白皙,从上面甚至看见领口里面的皮肤,比手更白皙。我不敢多看。第一个字“美”就没写好,写“美”时我往下多看了几眼,下来后发现“美”写歪了。
我站在凳子上写字时好多人围着看,我写一个字,扭头看看下面。没人说一句话。写完后我下来站在他们中间一起看。还是没人说一句话。我看看小赵。小赵说,写得真好。
但我觉得“美”真的没写好。不过小赵说好了,也许不错吧。字都是这样,刚写到墙上,看着别扭不顺眼,或许看几天就顺了。我坐在配件门市部门口,看了好些天,仍然觉得那个“美”没写好,一点不美,呆呆的。等想好了店名,往“美容店”前面写名字时,我把“美”涂了重写一下吧。我想。可是,直到我卖了配件门市部,离开县城到外打工前,都没想好名字,美容店成了它的名字。
来理发的大多是过往司机,有汽车司机、拖拉机司机。好像车开到这儿,司机的头发就长长了。小赵不喜欢给司机理发,一来司机头上都是油,车坏了司机就要把头伸到机器里修,洗司机的头太费洗发水。二来司机嘴里没好话,啥脏话都能说出来,要碰到太耍赖的司机,小赵就把我喊过去,坐在一旁看她理发。
没活干时小赵就坐在门口,她知道我在看她,朝我笑。有时走过来,和我妹妹燕子说话,她过来时,手里总抓着一把瓜子,给燕子分一点,给我分一点。她给我瓜子时手几乎伸进我的手心,指头挨到手心,我的手指稍弯一下,就能握住她的手。她每次只给我几颗瓜子,我几下嗑完,她再伸手给我一点。瓜子在她手心都焐热了,有一股手心里的香气。
每天都过飞机。帕丽来看飞机的时候,我们都出来帮着看。更多时候帕丽在别处看飞机,或者帕丽的飞机没来,天上飞着我和小赵的飞机。小赵比我看得仔细,我只是看看飞机是过来还是过去,然后回店里记到笔记本上,小赵一直看到飞机飞远,看不见。
我和小赵很少说话,飞机来的时候我们走到一起,其他时候只是隔着马路看。有时我背对小赵,也能感到她隔着马路看我的眼睛。小赵也能觉出我在看她,只要我盯着她看一会儿,她总会扭过头来对我笑笑。现在想来,我和小赵只是隔着马路远远地看了两年,然后我卖了门市部走了。
十
帕丽第一次带飞行员丈夫旦江来我家是在八月的一个傍晚,正如旦江在二十多年后的网文中写的那样,正是秋天,我们家菜园里的蔬菜都长成了,养的鸡也长大了,金子高高兴兴宰了一只鸡,从菜园里摘了半盆青辣子,整个鸡剁了跟青辣子炒在一起,用一个大平盘盛上来。帕丽和旦江都没见过这种吃法,一盘菜就把饭桌占满了。
接下来就是旦江在网文中写的那个重要时刻,旦江看着堆得小山似的一大盘菜,吃了一口,味道奇香,跟以前吃过的辣子炒鸡都不同,旦江就问,这叫什么菜。我脱口而出:大盘鸡。
在以后多少年里传遍全新疆全中国的大盘鸡,就这样发明了。我却一点记忆都没有。我只记得跟飞行员旦江一见如故,酒喝得很投机,边喝我边向旦江打问飞机的事。我问飞机轮子是咋样的,多大,跟哪个型号的拖拉机汽车轮胎一样。飞机那么大的机器,上面一定有好多大螺丝吧,那些螺丝都是什么型号的。
旦江说他只驾驶飞机,保养维修都有专人负责。
我说:你经常开飞机从我们县城上空过,从空中看我们县城是什么样子,能看见啥?
看不见啥,旦江说,就是一片房子,跟火柴盒一样。
那你在天上怎么掌握方向?我们在地上开拖拉机都有路,飞机在天上也有路吗?
旦江看看我,端起酒杯说:喝。
旦江即使喝醉了也没向我透露过飞机的任何秘密,这让我对旦江更加敬佩。开飞机的人心里一定有好多不能让别人知道的秘密。但旦江做梦都不会想到,我心里也有一个有关飞机的大秘密。我也不能把这个秘密说出去。如果我说给旦江。旦江回去告诉管飞机的人,说飞机飞行的秘密已经被人知道。那样的话飞机肯定会改道,沿着别的道路飞行,不经过我们县城了。
有一次酒喝到兴头,我几乎问到了关键的问题,我问:你开的飞机在天上坏了,怎么办?比如一个大螺丝断了,假如正好在沙县上空坏了,你会选择降落在哪。
最好是返航,旦江说,找最近的机场迫降。
那没时间返航呢?就像拖拉机突然在路上坏了,动不了了。
那就选择平坦地方降落,比如麦地,麦地是平的。苞谷地棉花地都有沟,颠得很。
那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开着小四轮在天上飞,车斗里装满特大型号的零配件。我听谁说一架飞机在天上坏了,说坏的地方很高,在一堆像草垛的云上面,我开着小四轮满天找坏掉的飞机。我的梦做到这里没有了。做梦有时跟做文章一样,开一个头,开好了津津有味做下去。有时梦也觉得这样做下去没意思,就不做了。我关于飞的梦都是半截子,我从来没做过一个完整的飞的梦。也许连梦都认为飞是不可能的事,做一半就扔了。但我跟飞有关的门市部却一直开了两年。
十一
我开农机配件门市部那年,从乡里到县里,到处是倒闭的公家的修理厂和农机公司,那些公家的农机库房里,堆满大大小小的农机配件。我骑摩托车在乡里县里和附近的团场转,找到那些公家的农机库房,想办法认识管库房的人,塞一点好处,里面的东西就可以随便捡了,好多地方的机耕队撤了,农机配件当废铁处理,装一车斗,估个价就拉走。我除了捡一些好卖的拖拉机零配件,只要看到特大号的螺丝,我是不会放过的。那些特大的螺杆螺帽,库房保管员都不知道是啥机器上的,只说在库房躺了好多年,库房保管员见我买这样的特大螺丝,对我刮目相看,他猜想我手里肯定有一台了不起的特大机器。
我把收购来的大大小小的螺杆螺帽摆放在柜台。特大号的螺丝柜台放不下,堆在地上。我是学机械的,知道这些螺杆螺帽的用处。它们用来连接固定东西,机器都是由许多个零部件组成,这些零部件都靠螺杆螺帽连接在一起,连接件是最容易坏的。我还收购和这些螺丝相配的各种型号的扳手,有活动扳手、固定扳手,扭大螺丝的扳手加长管。我的门市部螺丝型号最全。这是一个汽车师傅说的,他的汽车上一个不常用的螺丝断了,去了好多地方,最后竟然在我这里找到了。还有一个搞过大工业工程的老师傅看了我的这些螺丝后,点了好几个头,说,年轻人,等着吧,等到一个大事情你就发大财了,等不到,就是一堆废铁。
他不知道我等的是一个天上的东西。我在等一架飞机。可是我不能给他说,给谁都不能说。
我的门市部卖给别人那天,这些螺杆螺帽没有同农机配件一起卖掉,人家不要。我找了两辆小四轮拖拉机,拉了三趟,把它们运到城郊村的院子,我离开沙县后,我弟弟把它们全卖给房后面搞电焊的老王,听说卖了五千多块钱。
我说,卖这么便宜。我弟弟说,称公斤卖的,一公斤八毛钱。
我买的最大一个螺帽有拖拉机轮胎那么大,当时它躺在打井队院子里,上面坐着几个人,我问这个螺丝帽的螺杆呢,这么大的螺丝帽,它的螺杆一定顶天立地。打井队的人也不知道它的螺杆是什么样子,只知道这个铁东西在这里扔了好多年,因为太重,谁也拿不走它。我花了很少一点钱买下它,叫来一辆小四轮拖拉机,又找了几个朋友,带着绳索撬杠,折腾半天,这个铁家伙只挪动几公分。最后,我只好把它存放在打井队院子里,等有用处的时候我再拉。
以后我也忘了这个大家伙。多少年后,有一天我回沙县路过打井队院子,才回想起这个大螺帽。进去找,以前放大螺帽的地方已经变成一片菜地,问锄草的老头,直摇头,说他从来没见过那么大一个螺帽。拖拉机轮胎大的螺丝帽,可能吗?那得用多大的扳手拧它。问打井队的负责人,说打井队早散了,他就是井队的职工,这个院子十几年前就卖给他了。
十二
每年都有好多新购的拖拉机。自从我开了拖拉机配件门市部,找我报户口办油料证的人直接把拖拉机开到门市部门口,事情办完顺便买几个农机配件,再请我到一旁饭馆吃大盘鸡。我能感到路上的拖拉机在年年增多,但不会多过我报表中的数字。乡领导需要我们加快农业机械化发展速度,这是年终县上考核乡上的重要指标。我们站上也需要快速增加拖拉机马力数,这样分配给我们的平价柴油就会多。平价柴油是按马力分配的,一马力一年分多少油,有规定。那些年我无端增加了多少拖拉机,那些报表中的拖拉机拥有量和马力数,有多少是真的,多少只是数字,我自己也不清楚。
好多拖拉机只是一个数字,没有耗油、没有耕作、没有发出突突的声响。它们只存在于报表中,每年增加。这些虚数字,有个别被真实的拖拉机填补,因为每年都有农民购买拖拉机,拖拉机的数量在每年增加。多少年后,这里的拖拉机数量远远超过我编的数字。有的人家大小拖拉机三四台。我虚编了那么多拖拉机数,到后来全成真的了。我没想到农机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出我的编造能力。
编造一台拖拉机,就要同时编造一个机主。在我的农机报表中,那些村庄的好多人家,拥有了各式各样的拖拉机,他们开着它干活,每年的耗油量、耕地亩数、机耕费收入、修理费都统计在报表中。这些在报表中拥有拖拉机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有拖拉机,他们雇别人的拖拉机耕地播种,给别人付机耕费。几年后,他们中的一些人真的买了拖拉机,到农机站来报户。我在户口簿上看到他们的名字。
那时我想,等哪年我调离这个乡的时候,一定花点时间,把全乡的拖拉机数搞清楚。我当了十几年拖拉机管理员,我想知道报表中的数字和实际的差距,究竟有多少虚构的拖拉机,有多少真实的拖拉机。我似乎觉得自己需要一个真实的数字。就像我梦中在天上飞的时候,知道有一个地。但我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我的调离通知下来时,已经没时间去干这个事了,我被调到另一个乡当农机管理员。
那个乡也在城郊,我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做了两次农机年终统计报表,然后我辞掉工作到乌市打工。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乡有十七个村子,是我从乡政府报表中抄的。我调去的时候是十一月,直接赶上了年终报表。
我给站长说,我刚来,对这个乡情况不熟悉,想下去跑跑数字。
站长说,你闲得没?事了。你不是老统计了吗,咋样报报表不知道吗?
我花了一周时间,在去年报表的基础上做一些改动,变成今年的。这对于我是轻车熟路。我想把今年的报表应付过去,明年开春搞春耕检查时好好把全乡的村子都跑一遍,把全乡的拖拉机数调查一下。我在大泉乡留下遗憾,工作十几年最后竟然没机会把农机数搞清楚。在金沟乡不能再胡整了。我怀疑我照抄的这些数字可能都是假的。既然是假数字,那随便改改就无所谓。还是等明年好好统计吧。
第二年我都干啥了,记不清,好像突然年终报表就下来了,一年就要结束,根本顾不上去调查那些数字。最后一年我只匆匆做了半年报就辞职走了。走之前我把历年的统计报表转交给一个同事,我好像还翻开去年的报表看了看,我对自己编的一些数字似乎有点不放心。我给这个乡新编了多少拖拉机数字现在全忘了,只记住全乡的村庄数:十七。这是我从乡上报表中抄来的数字,一直没变过。啥都可以编,村庄的数字不能编。这是我认为的一个原则。
在这十七个村庄中,有一个叫野户地的村子我始终没去过。我想起在大泉乡待了十几年,那个叫下槽子的村庄也一直没去过,我经常到村里转,转了那么多年,都没转到那个村庄。调到金沟乡的一年多,我也跟随乡上的各种检查团去村里,我以为这个乡的村庄全走到了,却没有。报表中的野户地村我一直没去过。
现在想想,即使我再多待几年,可能也不会走进那个村子。因为野户地村或许根本不存在,它只是在报表中有一个村名,有户数人口数,有土地面积,有农机拥有量,有一个户口簿,有每家的户主和家庭成员名字及出生日期,乡上的各种通知都发往这个村子,乡长在讲话报告中经常提到这个村子,表扬这个村的村长工作能力强,表扬村民素质高,从来不到乡上告状找事,乡上安排的啥事都按时做完,最难做的事情都安排给这个村。这个村庄是农机推广先进村、计划生育先进村、社会治安先进村,村里电视最多、村民收入最高,我从来没有走进这个村庄,我怀疑它很可能只在报表中。就像我在大泉乡从没去过的那个下槽子村,我也不敢保证它是否真的存在。我每次说去下槽子,马站长都说太远了,路不好。也许根本没有一条路通向那里。
十三
我一直想着给帕丽写一首诗。我觉得和帕丽有一种秘密的缘分。她经常来配件门市部看飞机。她看旦江的飞机。她不知道我在看谁的飞机。我天天看飞机,就喜欢跟我一样爱好的人,甚至喜欢走路仰着头的人。我上小学时,村里的语文老师就是一个仰头走路的人,我老担心他被地上的土块绊倒。他很少看地上。他喜欢站在房顶看远处。有一天,语文老师从房顶掉下来。我们半年时间没上语文课。听说老师把脑子摔坏了,教不成学了。
帕丽走路胸脯挺挺,目光朝上,金子也是。还有小赵。我想让帕丽和小赵认识。因为小赵也喜欢看飞机。但帕丽不跟小赵说话。帕丽穿着红裙子黑高跟鞋,高傲得很。她仰头看飞机,其他人跟着看,看完她就骑自行车走了。她上车子时左脚踩在脚镫上,右脚蹬地助跑几步,然后裙子朝后飘起,一会儿就飘远了。
一次帕丽来看飞机,等了半天飞机没来。帕丽就坐在柜台边跟我说话。帕丽的眼睛又大又深又美丽,我不敢看她的眼睛,但她硬把眼睛递给我看。她可能想让我记住她的美丽,然后把她写到诗里。
帕丽盯着柜台下一个大螺丝问我这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也不知道能干什么。在废品站看见了就买了来,肯定是大机器上的。
我知道帕丽坐过飞机,就问:飞机上的螺丝都很大吧?
飞机都被铁皮包着的,看不见螺丝。帕丽说。
那飞机轮子多大你看见了吧?
跟拖拉机轮子差不多吧。帕丽说。
那天旦江来我家喝酒,我也问了相同的问题。旦江说,飞机有两个秘密,一是飞机的动力,只有专门的技师才能接触到,二是驾驶室,这一块的秘密只有飞行员知道。所以,我们飞行员只知道怎样操纵让飞机起落飞行,但不清楚它的动力部分怎样运行。管动力的技师只知道机器的秘密,但不知道怎样把它开到天上。
旦江的话让我觉得飞机和拖拉机似乎一样,有开车的有修车的。好多开车的不会修车。但开车修车却不是秘密。为啥开飞机和修飞机会成秘密?这可能是因为从地上跑,到天上飞,这中间本来就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很早就被我们的梦掌握,后来又被少数人掌握。我是知道这个秘密的少数人。因为我学过机械,知道飞机是一个大机器,大机器由大零件组成。除此我还知道飞机顺着地上的路在飞,这一点整个沙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一直收集大零件。那些堆在柜台旁和库房里的大零配件,经常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干大事情的人。
帕丽不知道这些大零件干什么用。小赵也不知道,她天天在路对面看我,跟我一起看飞机,但她做梦都不会想到吧,我真正做的是啥生意。连帮我看店的小妹燕子都不知道。金子对那些铁疙瘩也没兴趣。在金子眼里我只是一个乡农机管理员,一个卖拖拉机配件的人。她不知道我一直挂着农机配件门市部的牌子,在卖飞机配件。这里天天过飞机,只有我想到做天上的生意。
金子一直羡慕帕丽,她和帕丽一样漂亮,在学校时都是班花,帕丽找了飞行员丈夫,挣的工资多,给帕丽买好多漂亮衣服。她却嫁给一个乡农具管理员,也调不到县上,每天骑一个破自行车往下面跑。还住在城郊村的土房子。金子羡慕住楼房的人,冬天不用早晨起来架炉子,尤其天刚亮时,炉子的火早灭了,屋里冰冷,只有被窝里是热的,那时候谁都不想出被窝。早晨架炉子一般是我的活。我把火生着,屋子慢慢热起来时,金子起来做饭,女儿要睡到饭做熟,房子烧热了才起来。
金子最年轻美丽那些年,和我住在城郊的维族村庄,土路土墙土院子,我们在院子生了女儿,门口的沙枣树跟女儿同岁,我和金子结婚那年冬天,金子想吃沙枣,我在街上买了一袋,第二年春天,对着屋门的菜园边长出一棵沙枣苗,金子先发现,叫我出来看。她用枝条把树苗护起来,经常浇点水。金子的身子渐渐丰满起来,等到十一月,我们的女儿出生,沙枣树已经长到半米高,落了它的第一茬叶子。等我们搬出这个院子时,沙枣树已经长过房顶,年年结枣子给我们吃。
我们在这个院子住了好多年,菜园里每年都长出足够的蔬菜。我结婚前不吃茄子。吃了恶心。我妈说小时候烧生茄子吃,造的病。住进城郊村院子的第一个春天,我在菜园种了一块西红柿,一块辣子,几行黄瓜,一块豆角,菜苗长出来后,金子说怎么没有茄子。我说我不吃茄子。金子说,你不吃我还要吃,我肚子里的孩子要吃。金子从路对面邻居家要了茄子苗,把辣椒拔了,栽上茄子。我从那一年开始吃茄子。金子炒茄子,里面加一些芹菜、豆角和辣子,渐渐地我不觉得茄子难吃,茄子从此成了我最爱吃的蔬菜。
我在这个院子写出了我的第一本诗集,大都是写云和梦。我的心事还没落到地上。甚至没落到这个家和金子身上。金子跟帕丽夸耀我给她写了好多诗,其实我没给金子写过诗,她正在比诗还美的年龄,我想等她老了,再给她写诗。可是她一直不老,多少年后,跟她同龄的人都老了,帕丽老了,小赵可能也老了,金子一直没老。到现在我一直没给她写一首诗。
十四
有一阵我想调到县气象局工作,乡上一个同事的媳妇在气象局上班,我在他家里吃过饭。同事媳妇说气象局的工作就是天天望天。我想,我要干这个工作一定能干好,因为我不干这个工作都天天望天。天上的事我知道得太多了。我可能适合统计天上的事情,地上的事多一件少一件,也许不重要。就像那些村庄的拖拉机,多一台少一台,有啥呢。我想让它多一台,改个数字就行了。
我统计过往飞机的时候,顺便把每天刮什么风,风向大小都记了。我把风分成大风、中风和小风。大风是能刮翻草垛的风,一年有几次,我们这里还有一种黑风,我也归入到大风中。黑风就是沙尘暴,一般来自西北边,一堵黑墙一样从天边移过来,从看见到它移到跟前,要有一阵子。路上的人赶快回家,挂在外面的衣服收回去,场上的粮食盖住。黑墙渐渐移近,越来越高,空气凝固了,不够用了。那堵顶天的黑墙在快移到跟前时突然崩塌下来,眼前瞬间淹没在黑暗中。呼吸里满是沙尘,沙尘中胁裹着大大的雨点,落在身上都是泥浆。
中风是能刮跑帽子的风。小风刚好能吹动尘土和树叶,又吹不高远。再小的风就是微风了,不用记。
我们这个地方多数是西北风,东南风少。我统计风的时候,又顺便把云和雨雪统计了。雨雪好统计,每年下不了几场雨,冬天雪下得勤一些,也没有多少场。
云比较难统计,我就用诗歌描写,看到有意思的云,我就描述一番。描写的时候还抒情。我把好多情抒发在云上。我想抒情时就逮住天上的一朵云。我把云分成忙云和闲云。还有白云和彩云。我主要关心云的忙与闲。云在天上赶路的时候,我停下看云。满天的云在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整个天空变成一条拥挤的路,云挤云,有时两朵云跑成一朵,有时一朵跑成好几朵。云忙的时候比人忙。闲云我不说了,如果云在天上看我,一定认为我是地上的一个闲人。
我一直没像描写云一样描写过飞机。我只记录每天过往的飞机。我不描写它。飞机是不能描写的。云可以描写,可以写云的诗。
我描写云的本子放在配件门市部柜台里面,我在外面看天看云,想好了回来趴在柜台上写。我不在的时候,小赵经常过来和我妹妹说话,还翻出我写云的本子看。我知道小赵喜欢看我写云的诗以后,就写得更勤了,每天写一首诗,跟过来过去的飞机数字记在一个本子上。小赵肯定看不懂那些过来过去的数字是什么意思。但她或许看懂了我写云的诗,我在门市部时,她朝这边看得更勤了。
小赵第一次给我理发是一个黄昏,我骑车回来,小赵和燕子坐在门口聊天,小赵说,哥,你该理发了。那时我头发茂密油黑,喜欢留长发。小赵给我理过有数的几次发,都是在黄昏。在渐渐暗下来的理发店里,小赵的手指在我的头发上缓缓移动,她好像在数我有多少根头发,我的每一根头发梢都感觉到她的手指,耳朵和脖子的皮肤也感觉到了,理鬓角时她的手背贴在我的脸上,她理得仔细极了。
小赵男朋友穿着崭新西装,戴着大墨镜回来那天,我正好在门市部,没看清他长啥样,以为是一个来理发的,进来出去晃了几下就走了。后来燕子说那是小赵的男朋友。
小赵的事都是小妹燕子讲给我的。我去农机站上班后,剩下的时间就是燕子和小赵的,有顾客时各自招呼一下,更多时候,两个人坐在窗口看路上过往的拖拉机汽车,小赵把自己的事全说给燕子,燕子又说给我。
燕子说,小赵男朋友是做生意的,经常坐飞机全国各地跑。他这次是坐飞机到伊犁,又坐小汽车回来。说在伊犁谈成一笔进口钢材的大买卖。
小赵让她男朋友带她坐飞机,男朋友说坐飞机危险得很,有一次他坐的飞机在天上坏了,说是一个螺丝断掉了,天上又没有修理铺,你说咋办。
那后来怎么样了,那架在天上坏掉的飞机后来怎么样了?
燕子说小赵没说她不知道。
在我记录飞机的本子里面,有好多架只过去没过来的飞机,我用红笔标着,我一直都想着那些飞机怎么样了,或许都在天上坏掉,过不来了。或许还有另外的路,不是所有飞机都从我头顶飞过。但我一直在等所有的飞机,在这个三岔路口。
十五
门市部前每天都有等车的人,去乡里的班车一天跑一趟,错过了就只能搭便车。配件门市部前是搭便车的好地方,常有拖拉机停下,驾驶员进店里买个配件,出来车斗里坐了几个人,笑嘻嘻地说师傅辛苦了捎一截子路。
每个周末我都看见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在路口等车。他背着公文包,手里提一把镰刀。等累了,到我的门市部看看,我知道他不买农机配件,不怎么搭理他。他也不没话找话,趴在柜台上看看,柜台边有一个方凳,他是盯着那个方凳进来的,他有一眼没一眼地看看他根本看不懂的农机配件,然后,把方凳搬到屋外,坐在门口等拖拉机。
配件门市部卖掉的前一个月,我在另一个朋友的酒桌上碰见了他,叫董自发,在县委工作,是我朋友的朋友。我还在酒桌上听到有关董自发的事。好多年前,董自发下乡支农时,把一块手表丢在海子湾水库边的一片草滩上。那是刚工作时家里给他买的一块表。支农是县上组织干部下乡帮农民抢收麦子,董自发的手表就丢在麦地边的草滩上,他没敢告诉同伴,也没告诉村里人。支农回来后,他每个周天提一把镰刀,去海子湾水库边割草,找手表。第一年割到落雪没找到,第二年又在同一片草滩上割草。听说为了下去割草有理由,他还养了一头牛,又养了两只羊。
我知道了董自发的事以后,看见他来搭车就赶紧招呼,帮他早早搭上车。董自发走路说话都低着头,眼睛看着地,可能是找手表养成了习惯。那块表即使不被人拣走,也早锈掉了,董自发为啥还去找它。我不方便问。结识董自发后,我就老想着他丢掉的手表。一块表掉在草丛里,滴答滴答地走,旁边的虫子会以为来了一个新动物。表在草丛走了一圈又一圈,停了。表停时可能已经慢了两分钟。因为发条没劲了,就走得慢,最后慢慢停住。表可能停在深夜的一个钟点上。表不走了,时光在走。围着草丛中一块手表在走。时间有时候走在表指示的时间前面,有时候走在后面,有那么一个时刻,时间经过表停住的那个时间点,表在那一刻准确了。表走动的时候,从来没有准确过,一天走下来,总是慢一分多钟。在草丛停住后,一昼夜有两次,表准时地等来一个时间。准确无误的时间。这一刻之前之后,草丛中的表都是错的。时间越走越远,然后越走越近。漂泊的茫然的永无归宿的时间,在草丛中停住的一块表里,找到家。一块表停住的时刻,就是时间的家。所有时间离开那里,转一圈又回来。
董自发的这块表就这样在我心中走不掉了。以后再没见董自发挎个镰刀去割草找表,也许董自发发现我知道他的秘密后,从另外的路下乡了。也许一块表的意义逐渐变得轻微,他再不去找了。但我却一直在想那块表,我卖掉门市部离开沙县前,还骑摩托车去他丢表的那个叫海子湾的村庄,我不知道他的表丢在哪块地边的草滩。他也从没把确切位置告诉过别人。我问村民,许多年前有一个干部来村里帮助割麦子,有这回事吗?还有,一个干部的手表丢了,这事村里人知道吗。
没人知道。
我带着这块丢在草丛中的表离开沙县。从那时候起,有一块时间在我这里停住了。它像躺在房顶的“飞机配件门市部”招牌。像我做农机站统计时虚构的那些跑不到地上的拖拉机。像那个我一直没有去过,不知道是否真的存在的野户地村、下槽子村。我带着这些离开沙县。离开的那年,我刚好三十岁。
十六
现在该说说我的“飞机配件门市部”了。
农机配件门市部开业不久,有一天,我买了七张一点二米宽两米长的三合板,天黑后叫一辆小四轮帮我拉到门市部前,我上到房顶,驾驶员站在车斗上帮我往上递。全递上房后我让驾驶员回去休息,我从门市部拿出两罐油漆,一罐白的,一罐红的。我用白油漆给三合板刷了底色,然后用红油漆开始写字。一张三合板上写一个字。那个晚上月亮很亮,星星也又大又亮。房顶因为离天近一些,比地上更亮。
我从来没写过这么大的字,有点把握不准。我先用大排笔刷写了“部”,再写“市”,写“门”的时候已经很随手了,接着写“件”、“配”、“机”,一个比一个写得好。写“飞”时我犹豫了一下,想写一个繁体的“飞”,笔画没想清楚,就写了简体的。
七个鲜红的大字“飞机配件门市部”赫然出现在房顶。我乘夜把从外面收购来的大零配件一个一个搬上房,压在三合板角上,每个三合板压四个大配件,稳固在房顶。沙县经常刮风,城东这一块风尤其猛。我担心三合板被风刮走。大铁配件压在大招牌边,都是给天上的飞行员看的。
第二天一早我又爬上房顶,看见七个鲜活大字对着天空,我坐在房顶等飞机。那天怪了,从早晨到半中午没一架飞机。我被太阳晒得头晕,下房去喝了口水,突然听到飞机的声音,赶紧上房,站在油墨未干的“飞机配件门市部”旁。那是一架过去的飞机,往西开,飞机到头顶时我朝天上招手,发现飞机速度慢了下来,几乎停在头顶。我似乎看见飞机舷窗里的一双眼睛,正看着写在房顶的招牌。看着压在招牌上的巨大零件。还有仰头看天的我。
“飞机配件门市部”的招牌一直不为人知地贴在房顶。上房的梯子我藏在房后面。有天刮大风,燕子在理发店跟小赵聊天,看见对面房顶一块写着红色大字“飞”的三合板飞起来。燕子跑过马路喊我。那块三合板只飞过马路,就一头栽进机关农场大渠。我和燕子好不容易把它从渠里捞出来。我抱着板子回来是顶风,感觉板子在怀里飞,要把我带飞起来。我累得满头大汗,我说你飞吧。我丢开板子。板子“叭”地倒在地上,不动。
风停我赶紧把写着“飞”的板子拿上房顶,燕子在下面递,我在上面接。还搬了几块砖上去,压在飞上面。写了飞的板子飞了三次,都被我找回来。
另一场大风中“配”和“门”飞起来,“配”从房顶翻转着掉下来,“叭”地摔在路上,正好一辆拖拉机开来,直直压过去,留下一道黑车印。“门”飞过马路,小赵和燕子都看见了,红红的“门”字朝下。我在乡农机站接到燕子打来的电话,说“门”飞过大渠掉进果园了,让我赶快回来去追。
下午我回到门市部,“门”已经被燕子和小赵追回来,立在门市部门口。小赵说,我帮你把“门”递到房顶吧。我说,就扔这吧。小赵说,没有“门”上面就缺一个字。我看着小赵,怎么上面的字小赵都知道了。我又看燕子。燕子说,有一次羽毛球落在房顶,小赵上去拾羽毛球,看见了上面的字,喊我上去看。
还有谁上去看了?房东的大儿子也上去看了。
还有呢?电焊铺的老王也看了。
那是啥时候的事情。几个月前吧。
我想起那天和小赵看飞机,小赵说:哥,你坐过飞机吧?小赵随着燕子叫我哥。我说没坐过。要有一架飞机落到我们县城就好了。小赵说。那飞机驾驶员就会找你来剪头发。我说。才不会呢。小赵说。他会找你。找我干啥。小赵看着我笑笑。没回答。原来她早就知道我写在房顶的飞机配件门市部,知道我一直挂着农机配件门市部的牌子,做着卖飞机配件的生意。
十七
飞机真的来了。那天,我骑摩托车走在两旁长满高大玉米的乡道上,看不见村庄,路一直通到田野深处。我忘了骑摩托去干什么。平常下乡我都骑自行车。因为站长老马骑自行车,我不能比他跑更快。
摩托车无声地行驶着,它的声音被高大的玉米地吸收了。我仰着头,头发朝后飘扬,光亮的大脑门顶着天空,风从耳边过,但没有声音。这时我看见一架飞机斜斜地冲我飞过来,屁股后面冒着烟。我马上想到飞机在天上坏了。飞机是从县城上空斜落下来的。飞机坏了后飞行员肯定着急地往地下看,他首先看见我贴在房顶的“飞机配件门市部”,接着看见压在招牌四周的巨大螺丝,方圆几百公路的地上,只有一个经营飞机配件的门市部。他赶紧想办法降落飞机。不能落到县城,也不能落在路上。县城边有大片的麦田。麦田都是条田,跟飞机跑道一样。高高的玉米地后面就是大片麦田,我赶紧把摩托车开到地里,飞机几乎擦着我的头皮飞过去,我被它巨大的轰鸣声推倒在地,连滚带爬起来,看见飞机滑落在麦地。它落地的瞬间,无数金黄的麦穗飘起来,一直往上飘。然后,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飞机,银灰色的,翅膀像巨大的门扇一样展开,尾翼高高翘起。接着舱门打开,飞行员下来,拿一个大扳手,钻到飞机肚子底下。可能飞机上一个大螺丝断了,要换个新的。飞行员把机舱门锁住,往路上走。他在天上看见县城边有一家飞机配件门市部。还看见了大螺丝。他走几步回头看看飞机。飞机像几层房子摞起来一样高。飞机落下时巨大的风把条田的麦子都吹到天上了。附近村庄的人朝飞机跑来。这时候,我的摩托车已经开到麦地中央,麦子长得跟摩托车一样高,我看见自己在麦芒上飞跑,车后座上绑着一个大螺丝,是我在乡废品站买来的。本来驮回店里的,正好遇见飞机落下来。我朝走在麦地里的飞行员喊,卖飞机配件,卖飞机配件。飞行员疾走过来,看见摩托车后座上的大螺丝,眼睛都亮了。他看来看去,最后说:有更大号的螺丝和螺杆吗?我说有,多大号的都有。飞行员说,太好了,你给我全部拉来,有多少我要多少。
这时拥来的村民已经把飞机围着。飞机压了他们的麦地。有的村民说要回去取扳手,不赔钱就卸飞机膀子。有的说要卸飞机轱辘。我赶紧骑摩托车往回赶,在路上拦了一辆拖拉机,又拦了一辆,总共拦了四辆拖拉机,开到我的农机配件门市部,又叫了好几个人帮忙往车上搬螺丝。小赵也过来帮忙。小赵说,你终于来大生意了。我不好意思地看看小赵,她已经知道有一架飞机落下来,落在附近的麦田。她也知道我在经营飞机配件。我装了满满四拖拉机大螺丝,我骑摩托车在前面带路,拖拉机在后面一排跟着,路边都是人,都知道一架飞机落下来了。有人滚着半桶柴油跑,也许飞机缺油了,落下来。卖馕的买买提驮了一筐馕往城外跑,飞行员肯定饿坏了。我的摩托车和跟在后面的拖拉机跑得最快,远远地跑到前面,好像路越跑越远,两边长满高高的玉米,什么都看不见。终于跑到麦地边,满天晚霞。太阳正落下去,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我让拖拉机停住,我朝麦地里走,走过一个田埂,又走过一个田埂。怎么不见飞机了。麦子也长得好好的。是不是飞机修好飞走了。不可能啊,它修好飞走了也在天上,怎么天上也没有飞机。
我呆呆地站在麦地中央,站了很久,一直到天黑,星星出来。
十八
后来的情况是,我的农机配件门市部卖掉后,租的房子退给主人,房顶上的“飞机配件门市部”招牌没动,交房子钥匙的前一天,我找出写招牌用剩的半罐红油漆,爬梯子上房。招牌上的字已经不那么鲜红,落了一层尘土。我打开油漆罐,里面的油漆结了厚厚一层漆皮,用刷子柄捣开,剩余的油漆依然鲜红。我原想把飞机的“飞”改成“农”。我不想让人知道我在开一个飞机配件门市部。尽管小赵、电焊老王都知道了,他们并没笑话我,还把我当成一个干大事的人一样尊重。但是,更多的人可不这么想,他们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当成一个大笑话去传,多少年后都是可笑的。就像董自发去海子湾割草找手表的事,现在说起来我们还会忍不住笑。我不能留下一个笑话。这个让我做了好多梦,那么悠闲地度过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这段岁月的地方:每天过飞机的城东三角地,城郊乡农机站,我有了妻子女儿的大院子、我的年终报表中有拖拉机和没有拖拉机的村庄,我希望安安静静被它记住或遗忘。
飞机配件门市部和我的农机配件门市部只一字之差,我只要把飞字改了,谁都不会知道这个招牌是给天上的飞机看的。尽管县城上空天天过飞机,但谁也不会想为飞机开一个配件门市部。“飞”改“农”很简单,上面的横改成宝盖头,再向左拉出一大撇,就基本上是农了。我在心里构思好,刷子拿起来时,手却不由自主,把这个飞字改画成了一架飞机。
我在飞机下面还画了两个吊着的轮子,我不知道飞机轮子是什么样,我照着小四轮拖拉机的轮子画。我很欣赏我画的飞机,尤其那两个轮子画得最像。我还想在飞机屁股后面画一股子烟,但是没地方了。我收起画笔正要下房,听到天上的响声,一架飞机正从东边飞来,我一手提红油漆筒,一手拿油漆刷子,仰着头。
那一刻,我知道了飞机或许不是顺着地上的路在飞,它有天上的路。除了传到地上的声音,它跟我,跟这个县城,跟我开配件门市部的三岔路口,都没有任何关系。但我为什么一直在看着它呢。我做了那么多飞的梦,花好几年统计飞机过往数字,还有云和风的数字,都在笔记本里。也许这就是我跟它的关系。它跟我没有关系并不等于我跟它也没有关系。
记录飞机的笔记本放在柜台,配件门市部卖掉清理存货那天,我拿起本子看了看,我想以后不会再翻开这个本子,别人也看不懂那些记录着“过来”“过去”的数字。我把写云的诗页撕下来,本来想送给小赵。我让燕子去喊小赵。燕子说,小赵男朋友回来了,他男朋友这次在做一个更大的生意,用钱很多,小赵把理发挣的钱加上抵押理发店贷的款都给男朋友了。我扭头看见一个穿西装戴黑墨镜的男人站在理发店门口,他就是小赵说的那个经常坐飞机从我们头顶飞来飞去做大生意的人。他不知道我和小赵经常一起看飞机,那些飞机中或许有一架是他乘坐的。或许他根本就是一个连飞机都没见过只在想象中坐着飞机满天空跑的人。
我把撕下的诗稿原夹在笔记本里,和即将卖掉的配件扔在一起。
配件门市部卖掉后不久,我便辞掉农机站的工作,去乌市打工。我本来没想要出去打工,在大泉农机站时我一直等着老马退休,那样站长就是我的了。农机站四个人,我、站长老马、出纳努尔兰,还有老李。老李快退休了,努尔兰写不好汉语,站长肯定是我的。可是,我被调到了金沟乡农机站,那个站长年龄跟我差不多,我没指望了。再加上金子也鼓励我出去。金子两年前就对我说,你再在农机站待下去就完蛋了,最后像老李一样退休。我那时还不以为然,我怎么能像老李呢,我退休时最差也会像马站长一样,被大家称为刘站长。
可是我没当上站长。我这个人,可能天生不适合在地上干事情。我花好多年时间看天,不为人知地经营天上的事,现在我明白,其实我才是一架飞机呢,经常从地上起飞,飞到一个只有我知道的高远处,然后盘旋在那里,手臂伸展,眼睛朝下,看见我生活的城郊,我开在路边的小店,看见写在房顶的“飞机配件门市部”,红色的,每个字每个笔画都在飞,看见领着一群人仰头看飞机的帕丽,看见小赵和金子,站在他们中间的我。
然后,我飞累了落回来。
有一天他们在地上找不到我的时候,会不会有谁往天上望,谁会在偏西的一片云海中看见我。我经常一个人在天上飞,左右手插在两边的裤兜里,腿并直,脸朝下。有时翘起半条腿,鞋底朝上,像飞机的鳍。我顺风飘一阵,又逆风飞一阵。逆风时我的头发朝后飘,光亮的脑门露出来。我不动手。我是一个懒人。我想象我在地上的样子,也是多半时候手插在裤兜里。我在地上没干过什么事。当了十几年农机管理员,一直做统计。现在想想,我坐在办公室随意编造的那些数字,最后汇总到县、省、全国的农机报表中,国家不知道它的农机数据是错的。这些数字中有一些是一个乡农机管理员随便想出来的。也许它根本就不在乎这点差错。我每天记录的飞机过往数字没有差错,但没有谁需要。我开了个农机配件门市部,主要卖飞机配件。配件门市部开了两年,没挣什么钱,贷的一万块钱还了,剩下的就是库房里的一大堆大螺丝螺帽,这是我两年挣的。
还有,就是我写在房顶的“飞机配件门市部”。店卖掉后房顶的五块招牌都被风刮跑了。我听小赵说的。离开沙县前我找小赵理发,我原想剃个光头,这样出去打工就不用操心头发的事了。小赵说,我给你造个型吧,你出去做事情穿着打扮都不能太随意,不能让别人看不起你。小赵很仔细地给我理了一个老板头,我在镜子前端详半天,还是觉得那个头不是我的。正在这时飞机的声音传进来,我和小赵一起出门,我看着路对面已经是别人的配件门市部,心里一阵酸楚。小赵也没抬头看飞机,她一直看着我。小赵说,那天刮大风,房顶的五块招牌都飞了,有一块飞得特高特远,上面画着一架鲜红的飞机,那个招牌飞过我的理发店,飞过大渠,飞过机关农场果园,一直飞得看不见。风停以后我还去果园那边找,没找到,飞掉了。
小赵的美容店在配件门市部卖掉的第二年被银行封了。美容店的房子是别人的,小赵给男朋友贷款抵给银行的只是两把理发专用的躺椅和墙上的一面玻璃镜子。小赵被她父亲叫回家种地。后来嫁给一个村民。再以后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这些都是燕子告诉我的。燕子初中没毕业就辍学,给我看了两年店,后来开饭馆、开歌厅、开网吧,现在是沙县最大的电脑专卖店老板。帕丽嫁给旦江后调到乌鲁木齐工作,一直跟金子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我的印象里帕丽有很多朋友,而金子似乎只有帕丽一个朋友,帕丽出车祸半身瘫痪,金子依旧是她最好的朋友,经常在家里炒了大盘鸡去看她,有时买了鸡到帕丽家炒。旦江不开飞机后在一家旅游公司当办公室主任,帕丽出车祸瘫痪,旦江辞去主任职位,给公司看大门,晚上上班,白天在家休息,照顾帕丽。至于我,农机配件门市部卖掉后,我开始专心写诗,计划写一部万行长诗,主要是关于天空,关于云以及云朵下面一个村庄的事情。写到不到一千行,我扔掉诗稿进乌市打工。我的诗人生涯从此结束了。我在乌市打工期间,把我写完、没写完的诗全改成散文。在那本后来很有名的写村庄的书里,没有一篇文章写到飞机。那个小村庄的天空中飞机还没有出世,整个夜晚只有我一个人在飞。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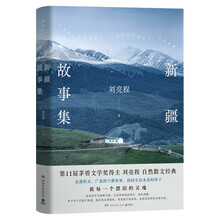
——李锐(50后代表作家,著名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