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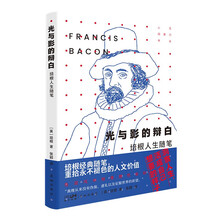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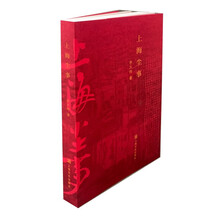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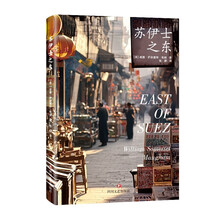
华语世界最受尊敬的写作者之一,作家唐诺散文巨制。作家数年如一日,定时定点到同一家咖啡馆写作,在圈内已成传奇,文字的故事、阅读的故事直至人的故事,经他道来都别具魅力,台湾作家张瑞芬更称其为“一个心智世界好的游手好闲者,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学问与心灵的雄辩家,和文字计较了一辈子的人”。
以尽头为坐标,探究此时此地我们的现实处境。十七篇文章,十七个人物,洋洋洒洒四十五万言,作者一次次回到历史现场,捡拾已被遗忘的那些伟大的发现、激动人心的作品,站在历史发展的岔路口,与现实相对照,追问发生了什么,让有可能变成没可能,使曾经有过的消失了,从而令极限没有到来,让无数可能成为一种且一种现实。
随书附赠别册,收录阿城、丰玮、杨照、张瑞芬评论文章,更有朱天文与唐诺的长篇对谈,回顾唐诺二十余年写作生涯,弥足珍贵。
唐诺作品首次在台湾内地同步出版。台湾诚品书店十一月选书推荐。
极限的思索,让人晓得自己其实可以更好。
尽头,常在远方,有时候却是现实。
探究尽头,为的是眺望远方与抵达远方的喜悦,是试图超出此时此地此身的努力。
以尽头为坐标,反观现实,则可发现我们身处何时何地,我们遗忘了什么,错失了什么。
作家唐诺,将萦绕多年的念头付诸笔端,以独有的诗性而思辨的语言,铸成四十五万字的鸿篇巨制。关于远方,关于写作,更关乎我们身处的现实。
极限的思索让我们箭一样射向远方,但注视它实际上的力竭停止之处,转而追究它“本来可以发生却为什么没发生”、“已堪堪发生却退回去复归不会发生”,则让我们老老实实落回此时此地来,这比较迫切,也有更多不舒服的真相,尤其是人自身的真相。
事物在此一实然世界的确实停止之处,我称之为尽头。在这里,一次一次的,最终,总的来说,揭示的是人的种种真实处境。
说明
尽头,这次这个书名倒是我自己取的,没有麻烦任何人,惟实际的内容绝没有此一书名显示的这么“巨大”,当然更不会像看起来这么悲伤这么抒情。
不是所谓的全书主题,这只是这两年半书写时间里自始至终徘徊脑中不去的有用概念,我以为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不管当下想的写的是什么,如同一种根本的意识,一种时时处处的自我提醒,因此,我特别记下它来。写上一本《世间的名字》当时,我一直想着的是“极限”,太阳会烧完自己,小说会哪天写完它的全部,各种自然的以及人的事物各自能做的和做不到的边界究竟何在,包括其空间的(何处)和时间的(何时)边界,凡此种种——但《世间的名字》末尾,我开始自省到自己的不自量力部分,事物极限的思索,其实应该由更专业的人来想来说才是,其中的潜力潜质、其中隐藏的诸多犹有可能,最终只有在日复一日专注如只此一途的实践中才(被迫)有所发现,或者说有所发明。我自己称此为希望,一处一处具体的、确确实实的希望。
另一面,极限的思索可能也是个太“奢侈”的思索,其实我们通常等不到它到来,也就无须忧虑它。也因此,这样的思索结果远比想象的要干净透明,不仅不可惧不威吓,甚至还太过美好;相对于我们现实人生,你不是感觉被无情截断,而是居然还延长延伸出去,不是少掉了,而是多出来——很快的,我们便会发现,这样的思索只一两个大步就越过了眼前的实然世界,进入到本来有可能发生但实际上尚未发生、不会发生的这“一截”多出来的世界之中。更多时候,再触到我们的并不是它的终归有限,而是它果然“美好得不像是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听到“你属于我所热爱的那个世界”这句话当场热泪盈眶,我相信,那一刻因此被叫唤出来、让人以为置身其中的,就是这一截多出来的世界。
极限的思索,让人晓得自己其实可以更好。
惟极限不会到来,事物总是在用尽自身可能之前、之很前就提前抵达尽头,这是因为现实世界同时会有很多事发生,先一步打断它中止它替换它并遗忘它。比方,民主政治本来还可以再好一些再睿智一些就像小密尔讲的那样,但实际上有另外更大的力量拉扯下它限制住它;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形式,至今仍未用尽自身全部可能,但昆德拉指出来它实际上走向另一种发展(成为一种令人变笨的东西),以至于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形式的这一道历史已提前殒没了,凡此。极限的思索让我们箭一样射向远方,但注视它实际上的力竭停止之处,转而追究它“本来可以发生却为什么没发生”、“已堪堪发生却退回去复归不会发生”,则让我们老老实实落回此时此地来,这比较迫切,也有更多不舒服的真相,尤其是人自身的真相。
事物在此一实然世界的确实停止之处,我称之为尽头。在这里,一次一次的,最终,总的来说,揭示的是人的种种真实处境。
书写工作,我仍很偶尔会想起年轻,还“无法进入到这个世界”(昆德拉语)的时日,当时,现在想来不知从何而生的空气中仿佛有个神奇的允诺,好像这是个接近无所不能、或至少足够自由轻灵到可以一再穿透各种界线、时间界线、空间界线乃至于人生死界线的太好东西,也许曾经、或本来可以这样没错。多年之后,我渐渐相信并且认定,在原来这也不能那也不能的实然世界之中,书写仍有这样一件事可以做而且得做,接近一种责任,那就是——此时此地,书写者至少得奋力地说出人的当下处境、他自身的处境。世纪交迭,万事发生,惟这一刻我们站在哪里,记得什么,看着什么,知道些什么,意识着什么,犹期盼什么。仔细看,这其实是书写时间长河中一代一代的连续工作,所以说像是个不懈的责任。
这本书,我麻烦了我的好友诗人初安民为我写序,从《文字的故事》以来这已十年以上时间,除了朱天文朱天心,他是始终在场、冷眼看着而且一直以各种必要方式协助我的人,没有他我大概还是会写,只是很难想象会是个什么光景,我于是用这样让他麻烦、让他困扰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感激,并纪念这一段逝去时光。但悲伤的是,十月里安民的母亲以八十五之龄溘然长逝,这当然比这篇序文重大,所以安民的序也只能留到我的下一本书。初安民把他几十年的生命时间多用在文学编辑工作上,我们都一起来到这个年岁了,时间所剩不多,未尽之志一堆,我仍然希望他回来认真地书写,像个诗人、像他本来应该的那样子写。
一 温泉乡的尸体露辛娜
二 回布拉格开同学会的伊莱娜
三 特洛伊十年后的海伦
四 画百美图的侠客金蒲孤
五 抄写在日本墓园里的王维
六 摆摊的写字先生卧云居士
七 不那么担忧电视的钱永祥
八 每天都在查禁书的唐诺
九 回忆四十年前柏林童年的本雅明
十 负责发明新病的小说家丰玮
十一 念自己小说给祖母听的林俊颖
十二 那位从纽约找上门来的NBA迷
十三 放弃绘画改用素描和文字的达·芬奇
十四 叛国的六十二岁间谍卡瑟尔
十五 忘了预言金融大风暴的克鲁格曼
十六 在湖水上唱歌跳舞的卡钦那
十七 随西伯利亚寒流入境的蓝仙子
这本书是一株大树,或者是一片树林。
我们在阅读此书的时候,就像看枝杈的分开,再分开,旋转,再旋转。它在生长。初时疏阔,渐渐绵密,点点芯芽,转瞬成叶。它常常引入他人话语,例如博尔赫斯,昆德拉,马尔克斯,卡尔维诺。在我看来,分布处处的引文都是大树的生长点,最后,唐诺长成了自己的大树,汪洋恣肆,随意而必然。
我读唐诺此书,经验是,不要急着读完,体会它的生长过程。
——阿城
他们都说唐诺的散文太长,我却觉得他写得已经够经济了,那里头每一小段细节要是落入凡夫手中,分明都是一本书的材料。他们又说唐诺的散文“跑野马”,我却看到了蜂巢般的结构,以及呈螺旋状前进的主导动机。这大概是因为他是一个太过优秀的小说读者,于是在和伟大小说家经年累月的对话之中,不知不觉又或者充分自省地扩大了自家写作的限度——让一篇散文恰好容纳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可能。有趣的是,这反而提醒了我们,散文原来还可以写成这个样子;不是现代文学体制意义下的散文,而是非常传统的,司马迁与蒙田式的“文”。
——梁文道
唐诺借着写无法被简化的文章,来宣达人生、社会、语言、文学无法被简化、不应该被简化的道理。唐诺的文章,既是论理,同时却也必然要是示范,示范什么样的事物情感无法被简化,一旦化约了,就变质了。
——杨照
他(唐诺)总有一种写着写着就离题了的能耐(有时与主题相关有时干脆就不管主题了),如野放牛羊一般,让读者也跟着他的思维一起跑野马跑到贺兰山去,能放能收,并且永远知道下一个枝节如何延展出去,如同海浪一波波不断拍打着岩岸,又如凡高《星夜》那一圈似成形未成形的光晕流动旋转,而内在自有韵律,自成宇宙。
——张瑞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