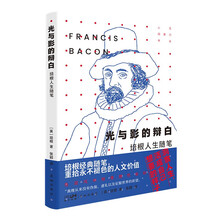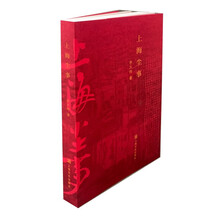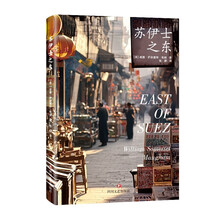到上海的学校报到的时候,路过郑州,但没绕道回家。到学校后,电话天天打,家里没电话,总是打到隔着一道河沟和山岭的表弟家。娘一次次地跑来跑去。冬天下雪了,路滑,娘摔了几个跟头,起来,摔疼的地方看都不看,继续向上爬,去接我的电话。过了几个月,娘装了电话,给我说,装电话也没什么大用,就接你电话。
又一年春天,过二月二,娘一个人在家,一直不睦的邻居,父亲的亲堂哥,跑到院子里把娘新种的几个小苹果树拔掉了,娘骂他,他把娘打倒在地。弟弟去找他,被他们一家五口人打了,没过一个月,趁弟弟不备,在路上突然袭击,把弟弟打成了轻度脑震荡。我得到消息,木在电话亭里。我没回宿舍,直接去找队政委请假,他却不批,要我冷静。我几乎要跪下求他了,眼泪不知道怎么回事,流了一脸。
晚上了,宿舍的同学都睡了。我等副队长查铺完毕,一个人跑出去,在学校的草坪上走来走去,想哭,又不敢哭,压抑的嗓音扯着心脏,疼呀,我小声喊娘。我知道,娘一定很疼的。暑假时候,我回去,弟弟说,娘去派出所,派出所叫娘来传唤那个打人的人。娘不能坐车,也没车,一个人,大热天气,从家到乡政府,再从乡政府到家,来来回回两次,加起来走了50多里的路程。
我给派出所打电话,他们推来推去,你说找他,他说找你。我愤怒了,吼叫起来,他们却挂了电话,我把话筒使劲摔了。电话亭的老太太很生气,要举报给队领导。我害怕,娘就是要我好好的,混出个人样子,我不能辜负她。我请假,到市场买了一部新电话给她。晚上时候,我没吃饭,到四平路街边,用201卡给娘打电话,我劝娘说,不要再争了,少说话,惹不起就躲吧。娘还在哭,说,不这样还能咋样呢?就忍吧,好不好?
9
那一年,冬天了,娘跟着大姨妈,信仰基督教,我想有信仰总是好的,娘喜欢,我也很高兴。只是她们频繁聚会,而且都在晚上,山里夜冷,风真的像刀子一样。我和同学在节假日到外滩转,又陪一个同学来上海看他的对象一起去过一些商场。我记得,在华联商场有一款特别适合娘穿的风衣,灰白色的那种,娘夜里出去聚会,穿上,一定温暖。
我问好的价格,是320元,真买还可以打折。元旦前几天,我一个人跑去,给娘买了,找不到邮局,拿回学校,听说五角场旁边有邮局,急忙要了一张请假卡,出门,给娘寄走了。娘收到说,这衣服她不喜欢穿,又不是城里老太太,干活穿着麻烦。我说娘你去聚会时候穿上,不冷。娘说,这是俺一辈子穿的最贵的衣裳了,留着吧,俺有棉袄呢,不必要浪费这钱,有人买俺就卖给她。
娘的话让我有点生气和失望,我想娘收到一定要夸我几句的,娘却反过来把我埋怨了一顿。冬天的上海干冷干冷的,我感冒了,同学们陪我到学校的医院看病,说是发烧。一发烧我就浑身关节疼,和同学们住在一起,晚上在睡梦中疼得叫娘。娘。娘。娘。我的叫声让其他的同学感觉不好,但大家一起很要好,早上起来,也就是说说。在宿舍病休的时候,有两个要好的女同学买了一些东西到我们宿舍来看我,其中一个叫孙楚瑜,海南人(孙是个很好的女孩,中途退学,现在不知道在哪儿);一个叫秦涟涟,湖北人(在校时与我们另一个分队的李姓男同学谈对象,毕业之后我才知道两个人的关系。现在应当在北京)。她们的看望让我感动,出去之后,我想娘,那时候,我就想:这世上最疼我的女人一定是娘。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