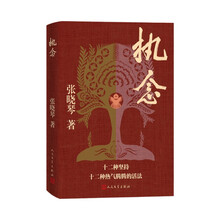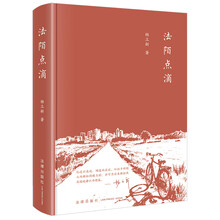凝固火焰
走出来几个小时以后,我开始后悔没有听从里铁甫的劝告。说是劝告,其实只是一个威吓的眼神和一个词:kün。里铁甫夸张地眨着眼皮,满眼都是恐怖。他翘起那个粗硬的大下巴来,让整个脸膛都浴进白熔的毒日光里。
感谢主,我幸好知道这个词,kün是太阳。我也抬起下巴,试着朝上瞟去,额间和脸颊立即淹进一片火烫的灼烤中。我当然知道kün是太阳,一个人哪怕只学了三天维语也知道这个词的。可是我觉得茫然,尽管满天都飘洒般密布着那灼烙般烤人的光线。那光芒如水如银,在天穹间流溢着逼近,从里铁甫的小庄院里出来时,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kün的厉害。
路左一字排开默默的火焰山。我们的毛驴车微微颤着,匀匀地响着一个寂寞的节奏。维吾尔人在车前斜斜立起两根交叉的木棍,使车子显得重心均衡。我微微感到有一点对里铁甫的歉意;此刻他不再劝我了。他的眉宇间流露着一丝忧郁。他有时轻轻抚摸着青驴子一耸一耸的尾巴,脸庞总是在一动之间就倏然变换明暗,阳光照耀的颧骨下巴,还是那么沉默着,硬硬地前伸成一个铲形。我猜这下巴后面的喉咙里可能也有不少生动的话,可是没有希望,我不懂维语,他不懂汉语,天上有一派刺人肌脉般灼烧着的毒花花的日光,地上是一条蜿蜒不语的鲜红得眩目的火焰山。
我每分钟都想捧起那只水壶,咚咚地把凉水灌满肚皮里面那些焦干的肠子。我觉得驴车在颤簸的时候,那些肠子像些干芦草一般叭叭地裂响,毒日头仿佛刺着它们,要快快地把它们全烤干烤碎掉。可是里铁甫瞧也不瞧那两只水壶,我不知道他是真的不渴,还是在默默地忍着干渴。
我们已经在火焰山里转了两天了。
天气实在太热了。我发现理解吐鲁番盆地好像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只要在这片土地上曝烤几天就够了。可是我已经决心走遍火焰山里的几条山沟,因为它们实在是大名鼎鼎。我找到里铁甫的时候依靠了翻译,所以我一路上总是安慰自己说,没关系,里铁甫当时肯定全听懂了,他明白我要干的事。
可是我不懂维语,他不懂汉语。我们俩在赶着毛驴车走进干裂得沟壑密布的火焰山以后,就陷入了无言的沉默。
白晃晃的蓝天上有一个烧成白炽的球,阳光撒在戈壁滩上,噗噗地溅着轻飘不落的灰尘。额上留不住汗水,举手一抹,手指沙沙有声地擦下一层白碱。
漫野摊开的青灰色砾石吸尽了光亮,黑沉沉地像是一片烧烫的铁块。只有火焰山依然鲜红地壁立路旁,一道道颤抖般弯曲的深沟交相拧扭着向上挣扎,在利齿般参差的山顶一线攒成一个个凸起的赤红的尖。
这真是一道不可思议的山。没有植被,没有河水溪泉,没有矿藏,没有能够耕作的土壤。但是有惊心动魄的鲜明的红色。无法理解的、愤怒般的焦渴的红色。
在山脚下,沿着平原戈壁和山体之间的小道,我们的毛驴车在缓缓蠕行。我最后忍不住还是摘下水壶,可是里铁甫动也不动地依样握着鞭子。我想了想,又在心里狠狠地拼了一口气,然后把水壶挂回车前板上交叉支着的木棍叉架上。“吐鲁番学”,我想着这个新名词,眯细眼皮躲开明晃晃的毒日光,眼皮不知是浮肿了还是干裂了,睁眨一下都觉得疼痛。学者们为这道荒山和这块盆地写了堆成山的书,可是他们也许从来没有被这里残酷的炎热灼烤过。对他们来说,“吐鲁番学”也许只是一个虚假的梦。青毛驴踢踏有致地踩着碎石小道,拐进了一个沟口,两侧鲜红浓重的山崖猛地挤压过来,我觉得眼帘里充斥的红色强光立即刺伤了脑子深处的什么地方。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