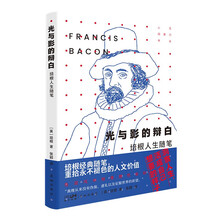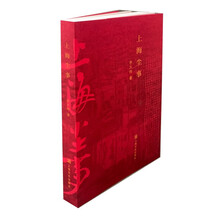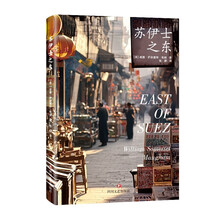沉默如谜的时光
你听过《似水年华》吗?倘若你没有听过,没有关系,多年前,有一部叫《似水年华》的电视剧,电视剧里的男主角说:“有个诗人叫聂鲁达,他说,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是不是我们的爱情也要到霜染青丝、时光逝去时,才能像北方冬天的枝杆一样清晰、勇敢、坚强。”
“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
这是聂鲁达说的。有些诗我不记得了,有些诗我依然记得,但毋庸置疑,他说的每一句我都爱。写这首诗的时候,聂鲁达多大的年纪,不可得知。他有太多的诗令人难忘,反而忘却了背后写诗之人的真实面貌。时隔多年,我由他的诗爱上了他这个人,我想了解他这个人的一生,于是我也想你,读着我的文字的你,跟随我了解他的一生,了解是怎样的人生塑造了这个伟大的诗人,我想,你一定对他感兴趣。
“如同所有的事物充满了我的灵魂,你从所有的事物中浮现,充满了我的灵魂。”
聂鲁达是天生的情圣,写着令人灵魂颤栗的情诗。越是渴望,就越空虚,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当聂鲁达诞生在智利中部的这座小城时,就意味着他将有可能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诗一般的命运。
“也许我不是自己在生活,也许我生活在别人的生活之中。在我的这些篇章里,肯定会有一些像秋天的落叶那样枯黄,还有一些如同葡萄收获季节里的葡萄,在醇香的葡萄酒中再生。我的生活是由各种各样的生活组成的生活,是诗人的生活。”
这是聂鲁达回忆录的序言,他的回忆录取名《我曾历尽沧桑》。回忆,从他的故乡开始。
关于我的孩提岁月,唯一不能让我忘却的就是雨。南部的大雨如同波洛的瀑布,从合恩角的天空降到了边界地区。在这边界地区,我的祖国的法尔维斯特,我来到生活中,来到大地上,来到诗间,也来到雨间。
我走过很多地方,我觉得任何地方的雨都不如故乡阿拉乌加地区下得那样粗犷而又细腻。雨整月地下,整年地下。雨柱好像刺破天空的玻璃针,掉到屋顶上摔成碎块或撞击到窗户上化为浪涛。雨中的每一间房子犹如一只小舟,在雨洋中艰难地驶向港口。
—《我曾历尽沧桑》
1904年,聂鲁达出生于智利中部的帕拉尔城。他的本名是内夫塔利 ·里卡尔多 ·雷耶斯 ·巴索阿尔托,从小喜爱读书,学生时代开始写作。至于他为什么改名聂鲁达,那是因为他的父亲不允许他从事文学创作,为了掩人耳目,他不得不改用笔名发表文章,于是便有了日后蜚声世界的大诗人,巴勃罗·聂鲁达。
聂鲁达从小崇拜一个人,那个人也是个诗人,扬·内珀穆克 ·聂鲁达。他是捷克人,也叫聂鲁达,比巴勃罗 ·聂鲁达早一个世纪。有人说,扬·聂鲁达是巴勃罗 ·聂鲁达从小到大的偶像,他改名聂鲁达,就是为了纪念这位诗人。
聂鲁达的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世了。聂鲁达对母亲的印象只有一张相片,穿着黑衣、身材瘦削,据说她还会写诗。在他六岁那年,全家人迁居到南部的特墨科城,父亲再婚,他有了继母。他这样形容他的继母:“她成了我的继母。我很难相信要把这样一个名称授予我童年的监护人。她聪明、和蔼,有股农民的幽默感,而且总是显得那么善良。”
聂鲁达对他的继母是喜爱的,或许是因为很早就失去母亲的缘故,他渴望一个柔情似水的女人给予他童年的关爱,哪怕这个女人不是他的亲生母亲。当然,他也是孤单的,这促使他的观察力异于常人,他总是能够看到别人忽略的事物,这也使得他变得非常细腻、敏感。
我的父亲是火车司机,他已经习惯于指挥和服从了。有时他也带我去。我们在博罗亚采石头。那是边界地区的野生中心地带,也是西班牙人和阿拉乌加人进行激烈战争的战场。那里的自然景色真让我陶醉。鸟、甲虫,还有鹧鸪蛋吸引了我。这些又黑又亮像猎枪筒似的东西,很难在山里找到。我对这些昆虫的精美惊奇不已。我还经常采集 “蛇母 ”,我们用这个古怪的名字称呼那种在智利虫类中个儿最大、又黑又亮又壮的鞘翅目动物。如果猛然在酒果树、野草果树或山毛榉上看到这家伙,真会把人吓一跳。我知道这东西很硬,我双脚站在上面也踩不坏。它有如此坚硬的保护壳,就不需要什么进攻武器了。
—《我曾历尽沧桑》
聂鲁达天生有着极高的文字天赋,当然,也得益于他生活的环境。南美洲、炎热的天气、终年不变的雨、热带丛林,这些是他文字天赋的起源。他真正与文字结缘,是偶然间翻到家中的明信片,更准确地说是情书。他迷上了这些爱意深浓的字句。
“很多年来,我只对人像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开始阅读那些字迹隽永的情书。我一直猜想那一定是位头戴礼帽、手持文明杖、系时髦领带的美男子。字里行间洋溢着动人的热情。信都是旅游者从世界各地寄来的,充满了华丽的句子和大胆的求爱。”
明信片是寄给一个叫玛丽亚 ·铁尔曼的女人,寄信者名叫恩里克。年幼的聂鲁达看着这些明信片,以及明信片上的女人头像,陷入无可抑制的想象中,想象对方是一位高傲的女演员,头冠上嵌满了明珠。于是,他也爱上了这个叫玛丽亚·铁尔曼的女人。
年幼的聂鲁达文静也淘气,安静的时候,站在某个角落一言不发很长时间,淘气的时候,和一群玩伴跑到漆黑的地下室,点着蜡烛玩打仗,胜利者就将俘虏绑在柱子上。这些都是童年的时候每个人大同小异的经历,诗人聂鲁达也不例外。他对新事物好奇,对女人与书感兴趣。他自己说,在成长的这段时光里,除了读书,就是爱情。
聂鲁达喜欢写信,或许是受到幼年那次看明信片的经历的影响。他的初恋是在与一个铁匠的女儿的书信往来中发展起来的。她叫布兰卡 ·威尔逊。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也是一次美丽的结识。起因是他的同学追求布兰卡,请求聂鲁达替他写情书。这就是他最初的文学作品,由情书开始他的创作生涯,并且俘获了一个年轻姑娘的心。
我记不清当时是怎样写的了,不过可能这就是我最初的文学作品。有一次那个女同学碰到我,问我她男朋友给她的那些信是不是我写的。我不敢否认自己的作品,惊慌失措地承认了。于是她给了我一个榅桲。我自然没吃,当宝贝留起来。这样我就顶替了我的那位伙伴。我继续写长长的情书,又不断地收到榅桲。
—《我曾历尽沧桑》
一部叫《邮差》的意大利电影,讲述一个年轻的邮差爱慕当地的一位姑娘,在送信的过程中认识了大诗人聂鲁达,并请求他为自己写情书给那位姑娘。
此情此景似曾相识,一幕在电影中,一幕在电影外,都是一样的令人心动。电影中的聂鲁达成全了邮差与姑娘的爱,年轻的小伙子对他说:“我想成为一个诗人。请告诉我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诗人?”聂鲁达对他说:“你试着一个人沿着海滩散步,走得越远越好。”他让邮差用一个词来形容渔网,邮差脱口而出道:“悲伤。”
是的,悲伤。如此靠近,又如此疏离。你可曾体味过悲伤,如影随形,月下一人时,它离你那么的近,贴近心的最深处,如一层黏膜,你的心每跳动一次,它就戳入一次,不深、不痛,可你就是觉得窒息。在喧闹的地方,人潮、噪音,悲伤瞬间消遁,无从捕捉,就像一根连接心脏的引线,稍一触碰,它就会牵扯,继而弥漫四肢百骸。
在诗的理想国,悲伤如潜流,默默无声,延伸至远方。悲伤是海潮归栖的声音,宁静、深远,是身体与心的碰撞,激荡出这个世界最沉默的浪花。《圣经 ·诗篇》中说:“我在困苦中,你曾给我宽广。”生命不仅仅是困苦,生命还有诗意和远方。
聂鲁达说:“一个诗人,如果他不是现实主义者,就会毁灭。可是,一个诗人,如果他仅仅是现实主义者,也会毁灭。如果诗人是完全的非理性主义者,诗作只有他自己和爱人读得懂,这是相当可悲的。如果诗人仅仅是理性主义者,就连驴子也读得懂他的诗歌,这就更可悲了。”
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诗人?就像电影《邮差》中聂鲁达说的,沿着海滩散步,看看海浪,听听海涛声。诗人,该有着海一般悲伤的情怀,与海一般宽广的胸襟。
这就是诗人瞭望到的真相。
我家对门住着两位姑娘。她们对我频送秋波,让我羞赧不已。我羞羞答答、难以启齿的事情,她们却早熟妄为。那次我站在家门口,根本不想看她们。可她们却用手里的一点东西勾引我。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原来是个野鸟窝,上面粘着苔藓和羽毛,里面有几只靛青的鸟蛋。我正要去拿鸟窝的时候,其中一个女孩却说要摸摸我的裤子。我吓坏了,拔腿就跑。那两个女孩边追边举起那个诱饵。我拐进一条巷子,跑进我父亲面包店的一间房子里。她们追上了我,开始剥我的裤子。这时候过道里传来我父亲的脚步声,她们才停下来。小鸟蛋也碎了。柜台下面,袭击者和被袭击者都屏住了呼吸。
—《我曾历尽沧桑》
这段经历是聂鲁达对性的一次初识,对方远比他早熟与主动。那时候,他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小男孩,羞怯、懦弱、畏缩。类似的经验不止一次,还有一次是他在家里找东西,发现院子的栅栏上有个洞。他贴着洞想看看外面,突然出现了一只手,这只手和他的手一般大小,可想而知这只手的主人也是个孩子,待他反应过来,想再看一眼时,手已经不见了。他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这只手和它的主人。
回忆,总是显得特别宽容。聂鲁达的一生,与爱情和诗歌是分不开的。他承认:“也许就是爱情和大自然从很早开始就成了我诗歌的源泉。”
聂鲁达出生的地方是一个村庄,他童年也是在诗一般的田园中度过的。这大概萌发了他对诗的兴趣与热情。他回忆儿时的经历,家乡群山环抱,他却一直想去看海。一次长假,凌晨四点就得起床,全家人都在忙碌,恨不得将全部的家当带上。尽管不算富裕,甚至用聂鲁达自己的话说可称得上贫穷,但至少一家人拥有一个充足愉快的假期,还是令人羡慕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