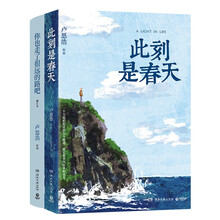把水倒进木盆里,兰姐试试水温,让我趴在木盆的边沿,低下头,把头发浸泡在热水里,帮我反复地揉,反复地搓,又用梳子反复地梳。水有点烫,又正值盛夏,我热得汗水淋漓,但只能咬牙坚持。她不断问我,烫吗?水烫吗?马上就好了。又说,姐姐不诓你,洗完就舒服了。哪有小姑娘家家的,头上长虱子的?
洗完头,我真就不觉得痒了,有种从未有过的清爽感。这时,兰姐把我的头发挽成一团,从盆里提出来,在阳光中抻开,用手巾一点一点吸上面的水,动作是那样的轻,那样的温柔。再看那只木盆,水面上密密麻麻地漂着一层白色尸体。因怕烫着我,兰姐不敢把水烧得太热,有许多虱子未被烫死,仍在挣扎。
养父来接我的时候,兰姐已经帮我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像模像样的,还找出两根红头绳给我扎了羊角辫。养父的眼睛一亮,说,哇,这是谁家的小姑娘呀,打扮得这么漂亮?然后面有愧色地向兰姐道谢。兰姐说,这有什么呀,我喜欢小妹妹,她真乖。走在小城的石板小道上,我一路蹦蹦跳跳,感到无比的轻松。养父追着我说,看我家姑娘多高兴啊,像一只小鸟。有本事你给我飞啊,飞到天上去。
从此我每次去刘家大院上课,兰姐都要给我洗头,梳头,扎羊角辫。说话间夏天到了,天气炎热,但兰姐家用的是井水,即使在正午打出来也很凉。她怕我感冒,每次都打好一桶水,先放在烈日下晒,让它回温。课上得差不多了,再给我洗头。这时桶里的水清凌凌的,不热也不凉,浇在头上特别舒服。
还不止这些。去上课的次数多了,兰姐事无巨细,什么都为我着想,好像我真是她的亲妹妹。鞋子破了,她给我做鞋;袜子露出脚趾头了,她给我补袜子。我的衣服大多数是养母穿剩的,不怎么合体,穿在身上空空荡荡的,兰姐便动手给我改,该缩小的缩小,该裁去一截的裁去一截,有的还别出心裁地加个领子,添道滚边,穿出去焕然一新,看不出改过的痕迹。这些事情,我知道凡是女人都会做,但对一个远离母亲的孩子来说,让我感觉特别温暖。
自从有了兰姐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再也不惧怕去江边的刘家大院上课了,面对老先生心里也不再觉得忐忑。如果养父在公司被事情拖住,回不了家陪我去上课,我便会烦躁不安,像丢了魂似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