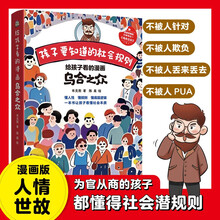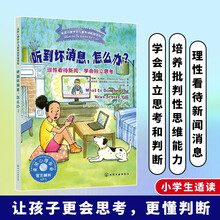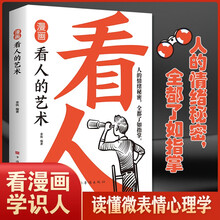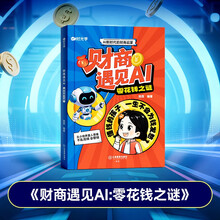少年往事
一、看灯
年代似乎是隔得太远了,说给小孩子们听就好像是在说一个十分悠远的故事。面对着一双双惊异的不可理喻的目光,告诉他们,我们儿时曾经有过的莫大快乐就只不过上街看灯时,他们人人都会大笑出声,觉得你们真是老土呀。是呀,同现在这些通过旅行、通过电视、通过电脑,什么都看到过的小孩比,我们的童年真的是很土很土。在今天小孩子的心目中,街上的各类彩灯早已看熟了眼,仿佛已经不是一道风景,而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存在,天天都有,时时可见。并且满街满房满树都是灯火粲然,想要不看都不行。然而,我们做小孩子时,那些璀璨的灯光却只在年节时分偶然地闪现在我们的眼边,平常却只是一个梦幻。
我家住在一个叫“刘家庙”的单位宿舍里,四周均是农民的菜地,最近的电车站离我们那里也得走二十多分钟。每逢年节,没有电视亦没有什么可玩之地,我和我的小哥哥便有一种寂寞难挨的感觉,常常吵闹,想要出门去玩。不知是哪一年,母亲终于作出决定,带我们上街看灯。
印象中头一次上街看灯时我还没有上小学,而我的小哥哥也只是一个刚进校门的小学生。母亲一手牵一个,沿着一家仓库的高墙走向大路。这是一段非常黑的小路,路边的菜地中还有两座坟包。当时的治安很好,妇女儿童走夜路从未有恐瞑感。母亲一路走一路为我们讲故事,在有星光的夜空下,那些故事被晚风吹拂得又神秘又动人。那时候楼房很少,我们要经过一所技校,一家空军医院,才能到我们看灯最重要的一站:父亲单位的科学院大楼。技校的灯只是用普通的灯泡将大门上的铁架围了一个圈,而空军医院的灯却更为简单,简单得配不上它所拥有的那座气派的大门。记得我们经常讨论:空军为什么不会把灯弄得好看一点?这样他们在天上开飞机时也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呀。讨论自然是没有结果的。而我父亲单位的科学院大楼却从来都不让我们失望。大楼其实只有四五层高,房形像一个“山”字,灰色的墙面,是远近最豪华的大楼。它的灯挂从屋顶一直垂下来,呈人字形。小灯是尖椒模样,红黄蓝绿交错置放。记得我小哥哥第一次见这灯时,便惊呼道:“啊,好多小辣椒呀。”他这一声叫喊,成为我家永远的笑柄,每次上街看灯都要被大人们翻出来笑上一通。站在科学院的大楼台阶上,我们拍起手来高唱:红灯绿灯,爹爹婆婆下农村。
汉口的江汉饭店一般来说是我们看灯的终点。而我们拐弯抹角地步行至此,已经耗去近两个钟头的时间。江汉饭店的灯串虽没有科学院大楼的气派,但它们却闪闪烁烁不断变幻着,给人以缤纷之感。我和小哥哥总是要反反复复地数着它闪烁的次数,不断为一些莫名其妙的数字欢呼,而那一刻的母亲,便满带着笑意望着我们。
看灯回到家,多已是很晚很晚,人亦累得够呛。但自从有第一次后,我们年年都盼望着这个日子。而我们看灯的队伍也年年壮大,先是我的二哥加入,后来又有邻家小孩尾随,再后来,连我父亲也兴致勃勃地跟着我们去了一次。一直到“文革”,不知从哪一年起,突然大家就没有了兴致,同时街上也突然就没有了灯。
其实现在想想在那样的夜晚,被母亲牵着手,走上很远的路,有时还顶着风,去到远处的街上看灯,真的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绪在此刻的心中涌动。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电灯而已,却给少年的我们带去了那样多的快乐,那是一种怎样简洁的生活和单纯的兴意呢?但它留在心中的韵味却是这样的绵长。只要在日历上看到那日子,仿佛想都不用想,少年时代的灯便和母亲的笑意一起在心里亮了起来。
二、我惨痛的穿衣经历
上小学的时候,我家的经济条件一直是同班同学中最好的。父亲每月有一笔不错的工资。在猪肉和鸡蛋都只需几毛钱一斤、学费只需要三块多钱的年月,那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尽管如此,我的哥哥们所穿的衣服,同别的家庭一样,仍然是小的拣大的不要的旧衣穿。那时候最值得小孩羡慕的人便是家中老大,因为新衣服总归他(她)们穿。
但我却比较幸运。我是家中唯一的女孩,没有姐姐穿小的衣服可拣,再加上家里经济条件不错,母亲又有闲情来打扮女孩子,于是我便总有新衣服穿。因为这个,在我的穿衣史上便也有了一些小小的“挫折”。记得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因穿一条大花的长裤,被班上男生说是“地主婆”,气得我哭着回家大闹一场,从此与“地主婆”划清界限。那时母亲特别喜欢为我做灯芯绒外衣。南京路一带有几家裁缝店能在做好的外衣上另外缀上一朵朵的小花,搭配起来特别好看,母亲便常常到那里去定做外衣。一九六五年底,母亲又带我去定做了一件外套,质地依然是灯芯绒,颜色是粉红色的,式样有些像娃娃衫,胸前缀着一排小花,穿出去人人都说漂亮。但只几个月,便开始了“文革”。人人都说好看的衣服在那个年月里就显得特别刺眼了,一穿出门,就仿佛被无数异样的眼光注视。我大不自在,于是又对穿此衣采取反抗态度。母亲万般无奈,为了不致浪费,只好把衣服上的小花拆掉,然后拿它到洗染铺,把它染成了一件全黑色的外套。这件外套后来就被我一直穿到高中。现在想来真正是不可思议。几乎同时,母亲还为我做了一件缎面的起着蓝色暗花的丝绵短外套。记得当时我特别喜欢,但不幸的是它也遭遇了“文革”。过年间,我穿着这件棉衣去邻居家玩,邻家三哥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纯粹为逗我开心,硬说我这件棉衣是“四旧”,无论我怎样同他辩论都没有用,直到我恼羞成怒,跑出门外,不管天有多冷,脱下这件棉外套,将它塞进了弃放在走廊上的煤筐里。急得我的父母拿我没办法。
有过这样的经历后,再加上家里成分不好,一旦穿上什么便容易招来非议的客观存在,我对自己所穿衣服是否好看有了一种无所谓的情绪。当我的个头长到与母亲差不多高的时候,就更多地去穿母亲以铁灰、深蓝或咖啡色为主的衣服。以后我参加了工作,当的却是装卸工,工作性质颇为脏累,便更是以三件工作服倒来倒去,时间一长,倒也觉得十分省事。女孩爱美和考究的天性仿佛全都被埋了起来。我家对面的一个老工程师曾经几次当人的面大声表扬我,说方方这个女孩子真朴素,从来都只看她穿工作服!
说起来现在的女孩恐怕都不相信,“文革”时我十一岁,从那以后,我几乎就没有穿过裙子,非但是我,我的同学也都是如此。不是不想穿,而是因为当时的气氛压抑了我们穿裙子的欲望。直到我大学毕业,分配到电视台工作,有一次应《长江文艺》之邀去鼓浪屿开笔会,会间逛街,才在厦门买下一条深蓝色的短裙。只是那一年我已经二十八岁了。从十一岁到二十八岁,一个女人最青春最漂亮的岁月,我却都是穿着长裤过来的。这是整整十七年毫无色彩毫无美感的日子,现在想起来,真有一种惨痛的感觉。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