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之毒
——铁骑党少年
…………
雪化之后回到医院的时候,彪悍的金马好像换了个人,他同意和我见面,继续接受治疗。听说他刚经历了一次惊恐发作,突然之间无法呼吸、血压骤升、失去控制,然后被送到当地的医院急救。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操!”金马双脚一如既往地翘在桌上,椅子一边着地,来回晃着,“都他妈的傻×,蠢得一塌糊涂。我都说过他妈的多少次了,我没有吸毒,你们什么时候让我走?”
我突然觉得愤怒,我们依然像两个陌生人,他还在无止境地说着脏话,不把我当人看。
“我既不是审判你的法官、关押你的狱警,也不是听你抱怨的垃圾接收站!你有没有想过我很讨厌你的脏话和侮辱,你什么时候尊重过我吗?”我第一次提高声调。
金马一愣,竭力掩饰脸上的震惊。他正眼看着我,也许第一次把我当作平等的人看待,而不是中餐馆里的女招待,或是带着口音的可笑女人在一直说着不着边际的废话。
“那种感觉很……”
“很什么?”
“很可怕。”
他点了点头,身体不知何时停止了晃动,反倒有些不自觉地颤抖。
“我会坐牢。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害怕过,就连小时候我爸用鞭子抽我的时候也没有。有一次好几个星期都只有我和我哥在家,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爸爸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家里没有吃的,我到后院找一些野果子吃,忽然看见一条蛇对着我。我抄起爸爸的刀,把它剁成了很多块,我现在都还记得蛇头冲着我的样子。我哥跟我说:‘示弱是通往死亡之路,力量才是唯一可靠的真理。’那个时候,我都没有害怕过。可是现在,为什么?为什么?”
我很想开心地宣告自己的胜利,可是他看起来像一只被雨淋透了的公鸡,耷拉着的身体,有种等待被拔毛割颈的绝望,就连无时不在的脏话也消失了。金马被完全打败了。
我第一次见他垮下来的样子,也许他头一次遇到失控的感觉,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死亡的恐惧。
“你在童年必须强悍才能生存,这是你所知道的唯一生存之道。因为父母的缺失和家庭的动荡搬迁,毒品一直是你生活中唯一稳定不变的存在。也许你一直都在掩盖自己的真实情感,把自己隐藏在强悍的面具后面,只有在一个人吸毒的时候,才可以放下面具,做一回真实和软弱的你。”
金马没有作声,他的双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着陆,他低头盯着它们,依然抖动。
“试着感受一下你的恐惧,如果它藏在你身上的某个部位的话,会在哪里?有颜色、温度和质地吗?”
与思想和情绪相比,身体的感觉是更为深入、真实且难以掩盖的自我,而心理的伤痛也或多或少会在身体上有所表现。
“胸口。紧!红色、硬、冷,很压迫。”
“你问胸口需要些什么?”
“抚摸。”
“不要压制这种恐惧感,想象它是一片云,缓缓飘过蓝色的天空。你就在这里看着它经过,不要催促,只是看着。”
“里面有一个盒子,一个打不开的盒子。我想打碎这个装满恐惧的铁盒,把它们都放出来,可是一想到这里,好像又要惊恐发作。我办不到!”
他突然睁开双眼,瘫倒在椅子上。
“也许你还没有准备好。”
在金马眼中,我似乎看到了那个饥饿无助的小男孩,他惊恐地对着蛇头,颤巍巍地举起尖刀。
过了两天,报纸上又登出一条金马哥哥的消息,陪审团已经通过有罪的裁定,法官判决其终身监禁,二十五年后才可以申请假释。
金马又恢复了一贯的暴戾不合作,他拒绝面谈,拒绝服药,拒绝上课。
一天,他用身体威慑一个壮硕的工作人员、一名业余橄榄球运动员。大家都很奇怪,世界那么大,他为什么偏偏选一个最高大结实的人找茬呢?
我知道,他以卵击石似的故意挑战,是用来掩饰自己的恐惧和软弱。在这个他坚信只有靠征服才能取胜的世界里,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选择了披上战袍,头戴盔甲,决不投降,继续战斗。
医院下了最后通牒。
几天后,金马被逐出医院,移交给了执法部门。
半年之后的某天,我去沃尔玛买杀虫剂。屋外的蚂蚁和爬虫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我在寻找最剧烈的毒药。
“小姐,你很美,看起来有点面熟,在餐馆工作过吗?”
“没有。”我笑了笑,继续盯着那一瓶瓶色彩斑斓的杀虫剂,一定要找到能瞬间杀死的那种,必须一击而中,“不过,谢谢你的搭讪。”
我想到金马,那个也曾问我是否在餐馆打工的年轻人,他身在何方?是否悔悟了呢?他是否也卸下了盔甲,变得柔软,和我一样呢?
我祈祷自己在他的心里播下了一粒种子,哪怕五年、十年后的某一天,这粒存活下来的种子突然沐浴到了阳光雨露,发芽抽枝,生长起来,再不枯萎。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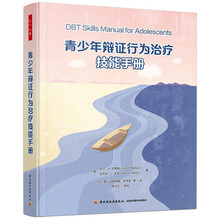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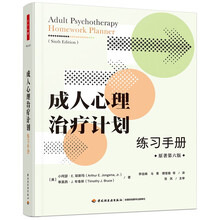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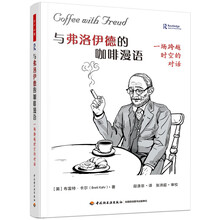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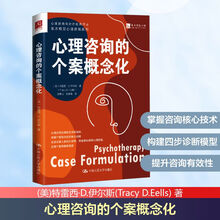

——刘瑜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作者在心理咨询的实践中既是百分百投入的共情参与者,也是理性分歧、有距离感的观察者;既有对于不同理论的介绍和实践,又有对于现行医疗体制的审视和批判。虽然讲的是美国病人的故事,其实每个人在其中都可以发现自己的影子。
——王建平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灵魂的伤痛zui难言说,但言说却是愈合的必经之途。春媚的记录真诚袒露,因而也格外勇敢。死亡和罪恶固然无法逃离,但仍有悲悯和接纳;勇气和自由,使生者可相互支持,击破人间的迷你地狱。
——覃里雯
著名新闻人、作家
那些破碎的内心如同绽放在地狱边缘的恶之花,凄清无助,展现了世界的复杂和人性的脆弱。作者重温这段治疗病人的心路,也是一次自我治疗的跋涉。那种反抗绝望的意志如同一道亮光,指引作者穿越风雨交加的夜路,走向远方晴朗的黎明……
——黄发有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