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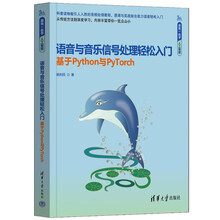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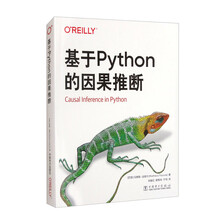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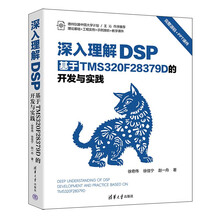
1. 余秋雨新作品集,首度发布大量在境外演讲的珍贵篇章。
首度较完整汇集余秋雨先生在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及澳门等地的演讲稿,对文明、文化进行了本质性的深入思索,并得出了一些重要的文化结论。笔触鲜活而精到,思索真诚又专精,对人生和社会的感悟令人振聋发聩。
2. 真正的冲突,真的发生在文明之间吗?中华文化为何长寿?为什么说汉字是活着的图腾,永恒的星辰?中华文化有哪些历史性缺憾?中国文人有哪些习惯性心理隐疾?
对于上述这些重大而棘手的问题,余秋雨在书中作了敏锐而真诚的思索,并得出了一些珍贵的文化结论。他既分析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优势,也以“由负深入”“由负得正”的责任感,对中华文化中的缺憾进行了严肃的探索。他说,以痛握脉,以痛传代。只要凭着这种真诚,我们就能与文化同在。
3.带你感受外部世界的精彩、人类历史的厚重、道义的神圣、生命涵义的丰富!
余先生说,开阔胸襟、坦然情怀,是中华文化的首要品性,与数千年历史相关,与五湖四海相关。只有让自己接受陌生,接受未知,生命才有延伸的希望,精神才有拓展的可能。
在历险考察人类绝大多数重大古文明遗迹后,余秋雨对文明、文化进行了本质性的深入思索,并得出了重要的文化结论。他深感自己有责任把万里历险变成万里演讲,向更大的空间、更多的人群,进行论述和提醒。这就是余秋雨境外演讲的来由。
本书首度较完整汇集了余秋雨在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及澳门等地的演讲记录,其中许多篇章是首次在大陆面世。全书分“联合国演讲”“文化总论”“从纽约到香港”“从新加坡到澳门”四个部分,对“文明冲突论”作了有力质疑,对文化的本质加以总结性论述,并且系统而清晰地阐述了中国文化的利弊得失、中国文人的习惯性心理隐疾、让人头疼的遗产问题等。
余秋雨深信,中国文化的前途取决于年轻的创造者,既然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那么年轻人的品行、等级、力量、眼界、气度、心态,就是中国文化的未来。
自序
联合国演讲
中华文化为何长寿?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的演讲
中华文化的非侵略本性
——在联合国“世界文明论坛”上的主旨演讲
驳文明冲突论
——对话博科娃
文化总论
何谓文化
——在接受荣誉博士称号后的学术演讲
从纽约到香港
汉字
空间
不极端
不远征
想起罗素
社会公德
实证机制
伪饰之瘾
整人之癖
耻感之痹
遗产问题
从新加坡到澳门
第四座桥
——在新加坡“跨世纪文化对话”上的演讲(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日) / 233
文化之痛
向市长建言
余秋雨文化大事记
自序 境外演讲自序
& 内文摘选
自序
一
先要对书名做一点说明。
中国一般所说的“境外”,是指中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范围之外的辽阔世界。香港、澳门回归后,管辖权已属于中央政府,但是因为还有“一国两制”的划界,也仍然习惯性地称之为“境外”。
因此,所谓“境外演讲”,是指我在中国内地之外的世界各地发表的演讲选辑。因为已经单独有一本《台湾论学》出版,这本书也就不包括在那里的演讲了。
我不管在哪里演讲,都没有讲稿。有时,主办方会根据录音整理一份记录稿给我,征询能否发表。可惜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种记录稿绝大多数都无法采用。只有很少几份还算不错,我动手整理,总觉得比另写一篇文章还麻烦。这本书里收集的,就是这些“麻烦文本”。
二
我为什么会在境外做那么多演讲呢?
这有一个重大契机。
大家都知道,我曾经接受香港凤凰卫视的邀请,历险考察了人类绝大多数重大古文明遗址。考察结束时,在尼泊尔的一个小山村,面对着喜马拉雅山的宏伟山壁想了很久。
我想得最多的,是目睹一系列最辉煌的文明发祥地,现在几乎都衰落了,而且都被恐怖主义包围着。我发现,真正激烈的冲突并未发生在文明与文明之间,而是发生在文明与野蛮之间。
特别让我震动的是,我在远方的废墟间想起了中华文化。为什么在其他老者逐一沦亡之后,它却能单独活了下来?我们似乎对它还不太了解,当然,世界对它更不了解。
正好,那时有一位一直关注着我脚步的外国时事评论家远道赶来对我进行“半途拦截采访”。他一见面就急急地问我在世纪之交进行数万公里历险考察所得出的文化结论。我回答他,结论有三方面——
第一,重识中华文化;
第二,质疑文明冲突;
第三,惊觉恐怖主义。
他一听就来劲了,诚恳地要求我在这次万里远行结束之后再来另一次万里远行,那就是满世界讲述这三个结论。他反复向我阐述,这三个结论非常重要又非常及时,如果不讲,是一种失责。
回国后我深入观察了国际文化思维的基本动向,终于明白那位“半途拦截采访”的时事评论家是对的。我确实有责任把万里历险变成万里演讲,向更大的空间、更多的人群,进行论述和提醒。
这就是一大串境外演讲的来由。
三
这本演讲录的第一部分,都与联合国有关。
按照时间顺序,我在联合国发表了以下三个演讲——
2005年7月,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主要论述中华文化的非侵略本性;
2010年5月,在联合国发布第一个有关文化的“世界报告”的庆典上,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进行对话,我发言的主旨,是反驳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
2013年10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发表演讲,主旨是论述中华文化长寿不衰的原因。这个演讲,一度成为联合国网站的第一要闻。
这三个演讲都有明确的反驳对象,第一个演讲反驳了“中国威胁论”,第二个演讲反驳了“文明冲突论”,第三个演讲反驳了“中国崩溃论”。反驳的似乎是政治概念,但我是在纯粹的文化高度上完成的。因此,当时的现场反应和事后的社会反响都非常热烈。
我本人的生态,离政治十分遥远,一切思考都出自文化本身的逻辑。不小心碰到了政治,只能说明文化对政治具有覆盖能力。
收入本书时,我并未按时间次序排列,而把第三个演讲放到最前面了。原因是这个演讲更有历史的概括性,也是我以前很多思考的总结。很多因繁忙而无暇阅读全书的朋友,可以把它作为首读之选。
四
这本演讲录的第二部分,是对文化本体的总论,只收录了一篇已经很出名的演讲《何谓文化》。这个总论我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讲过,反响一直很好,首讲是在澳门。
接下来的第三部分,标明“从纽约到香港”,是对第一部分内容的准备和延续。在美国,我除了在联合国总部演讲外,还到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马里兰大学等地巡回演讲,中心内容还是围绕着对中国文化的解读。
从2006年开始,我又在香港凤凰卫视开设了一个《秋雨时分》的谈话栏目,仍然谈中国文化。这是一个每天都要播出的“日播节目”,话语量相当庞大。播出后曾有很多出版社来找我,希望根据录音出书,一本本出下去,而且担保畅销。对此我都没有同意,因为这样的“电视衍生书籍”会损及我心中对出版事业的独立尊严。
直到很多年后,我才从巡回演讲和电视谈话的残存记录稿中剪出一些零星话题收起来,作为一个时期思维痕迹的留底。但事情太多,刚留就忘了。又过了几年,因整理书房,在一个陈旧的纸袋里发现了这些留底,匆匆翻阅,倒是觉得可以印在哪本书里。因为这些思维痕迹呈现了我为联合国演讲所作的“备课”过程。因为是“备课”,读起来可能与那些演讲有点重复。
按照我平素对文章的要求,它们似乎不太合格,很像一串串“思维随笔”和“杂文”。当然,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些攻击性的“杂文”不同,它们包含着环球考察的体验和历史文化的探掘。而且,篇幅也比较长。
这些文章既然已经拉扯成串了,也就有了一些内容上的大致划分。第一串,着重在聊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优势,例如“汉字”、“空间”、“不极端”、“不远征”之类;第二串,着重在聊中华文化的历史性缺憾,例如在“社会公德”和“实证意识”等方面;第三串,着重在聊中国文人的习惯性心理隐疾,例如“伪饰之瘾”、“整人之癖”、“耻感之痹”等等。此外,还聊到了让人头疼的遗产问题。
看得出来,第一串的内容完全是正面的,第二、第三串则探索了正面背后的一些内容。
我们历来的话语习惯,提倡弘扬正面。但是在我看来,弘扬正面固然不可缺少,而由负深入,以负得正,也是严肃思考者的责任。我既然已经在联合国大会上一再讲述中华文化的种种优点,为什么不能切入负面,使中华文化变得更立体、更完整、更真实呢?
当年罗曼·罗兰读到《阿Q正传》而落泪,是因为他突然发现一个被世界列强百般欺侮的民族也有了自我调侃者,并在调侃中显现了觉醒的可能。现在中国的面貌已与阿Q时代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更不必再遮盖和掩饰了,尽可以大大方方地坦示一切、讨论一切、思考一切。
我在境外讲述中华文化中的负面现象,多半还是为了回应海外华人,尤其是大批出国留学生的要求。他们见到我之后,谈得最多的是“文化差异”,也就是自己身上已经渗入肌体的文化传统与所在地文化生态的距离。他们有时很沮丧,有时很激愤,有时很自卑,有时很自傲。因此,遥远的海外,已成为中外文化进行比较、过手、嫁接、淘洗的前沿阵地。一切最深层的文化思考,也会在那里产生。我觉得,在那里讨论中华文化的得失利弊,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家丑不可外扬”的说法已经太老旧,我要用一系列演讲来突破。
在这部分内容中,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是对中华文化重大缺憾的探索。其中,尤其是探索了中华文化漠视公共空间,随之漠视社会公德和审美公德的长年弊病。
五
这本演讲录的第四部分,标明“从新加坡到澳门”,汇集了我论述文化的几个专业演讲,演讲地也不止标出的这两处。《第四座桥》是在新加坡讲的,论述了中国文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表已有二十年。现在中国文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与当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基本思路仍可参考。
另有一篇专论城市文化的演讲,是在澳门一个研修班上首次发表的。
六
选编这本书时,我一次次暗自发笑。
尽管书里所收的内容只是我所有演讲的很小一部分,但也已经够多的了。我,一个从小就极其腼腆,开口就脸红的人,怎么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中讲那么多话?
记得十三岁那年我获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在上海市青年宫举行的隆重颁奖仪式上被指定必须讲话。那天肯定是我的一场大灾难,所有在场的听众都在窃窃私语:“这孩子文章写得那么好,怎么完全不会讲话?”
其实,从小学开始,我每天在课堂上都会默默祈求,希望老师不要点到我的名,叫我站起来回答问题。一点到名,就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老师问的问题我都能回答,怕的只是当众讲话。怕的程度,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但是,终于发生了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 过了一些年,我居然成了每一届“国际大专电视辩论赛”的“现场总讲评”,而且受到各国主办单位一致赞扬,很多年都未曾安排第二人选。我也随之被他们称为“最会讲话的中国文人”。
从“完全不会讲话”,一变而成为“最会讲话”,中间有没有经过特殊训练?没有。是否受到特别启发?没有。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很会讲话了,而且一上讲台就浑身轻松,听众越多就越是从容。
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却经常用自己的这个例子启发苦恼不堪的年轻人: 你感到自己最不行的地方,很可能恰恰是你的特长所在,正像在一个特别贫瘠的沙漠下,藏着一个富矿。
——我借着演讲的话题,顺便说了一点难解的人生悖论,写在自序之尾,供读者一乐。
二〇一七年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