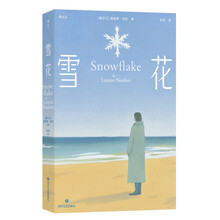《秋风袭人》:
一杜鹃知道,总编辑找她没好事。
作为《每日早报》的社会新闻记者,她报道过许多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这些新闻成为报纸的卖点。
街头的报贩子,常常以此夸大其词叫卖,招徕读者。
眼瞅着报社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稳稳地屹立在如林的都市报之中。杜鹃想不当报社的台柱子都不成,便自然而然人了理万机的法眼。理万机是记者们对总编辑的戏称。入了理万机法眼,往往凶多吉少。又多了双眼睛盯着她,警惕着她别惹出事端,要是搞得报社关门大吉,是闹着玩的吗?几百号人喝西北风去?今天一大早,理万机粗粗看了她的长篇特写。放下稿子,便拿起电话召见她。理万机一边用手指敲打着杜鹃的稿子,一边盯着她的眼睛,缓慢地,一字一字说:“你有什么证据,说大都酒店存在着一个地下赌场?”杜鹃低声说:“我有线报。”理万机哼了一声:“线报?能告诉我,线报有什么证据吗?”杜鹃底气明显不足:“线人没说。所以我才去暗访。”理万机不以为然:“这就是你的暗访?在人家酒店东游西逛,道听途说,还私自闯入人家办公区?更低级的是还在酒店咖啡间搭讪陌生男人,差点让那男人把你当成了鸡,带去客房。要不是记者证帮了你,还不定闹出多大笑话,收不了场呢。”杜鹃嘟囔着说:“那男人就是个赌徒,谁知还身兼嫖客。”理万机把稿子扔给杜鹃说:“赌徒也好,嫖客也罢,我们不是警察,是记者。我看你是福尔摩斯、克里斯蒂看多了。尽管你报道过许多社会新闻引人关注,但不能听风就是雨。新闻是什么?不光有时效性,还要有真实性,是真实发生了的事实。不是你的推测、想象,也不是大概、可能、差不多。再说,大都酒店是个外资独资企业,关系到国家的许多政策,负面报道要慎之又慎。今后再有这样的线索,要经我同意,你才能采访。”杜鹃嘀咕着:“您说的慎之又慎,就是给我这稿子毙了?”总编理万机反问:“你还想怎么样?这稿子没有修改的价值。毙了就毙了。”杜鹃疑问:“那这线索?我怎么听着像不了了之?”理万机和蔼地笑笑:“你听着像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至于那个线索,有些时候,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初春午后的阳光,暖暖地照耀着大都酒店那高大的银灰色的玻璃幕墙,于是那玻璃幕墙金碧辉煌起来,且把那金色的暖暖的阳光反射到对面的楼宇上,反射到街道两旁的紫穗槐树冠上,反射到途经此处的每个行人的脸上。树欣欣向荣,人也暖洋洋的。
一辆出租车停在这座三十层的酒店门前。一个一张娃娃脸,胖乎乎,顶多十八九岁的门童笑脸相迎。
他躬身为客人拉开车门。一个一身牛仔装的中年男人从车上下来。男人并没有打算马上就进酒店,他把一只很精致的棕色皮箱放在脚边,然后从衣兜里摸出一盒万宝路,抽出一支点燃,看似悠闲地吐了个烟圈,眼睛却迅速地前后左右扫视了一下。直到那支烟吸完,才吐出吸剩下的烟头,用鞋底跟碎,拎着那只皮箱进了旋转门。
几乎与此同时,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驶进酒店的地上停车场。车上坐着一个年轻人,戴着耳麦,目送着走进旋转门的男人说:“目标已经进了大都酒店。
”大都酒店宴会厅里,服务员忙着摆台,餐碟碗筷、酒杯茶杯、餐巾纸巾在他们手中来来去去,让人看着眼花缭乱。报社的两个年轻人爬到人字梯上,扯起一条红色横幅。横幅上写着:每日新闻报社成立20周年庆典。
一个年轻人在梯子上回过头来,冲下面的一个女人叫:“兰翎,看看正不正?”被叫作兰翎的女记者,一直盯着横幅,说:“你那边再低点,对,这就成了。”酒店顶层,总裁宇文关山宽大的办公室里,一个名叫侯建,绰号猴子的员工,对大班台后正在看财务报表的宇文关山说:“有个叫任国忠的人要见你。”宇文关山放下报表,抬起头来,猴子发现总裁的脸上惊诧、疑惑、忧虑,五味杂陈:“谁?你说谁要见我?”猴子小心地说:“他说他叫任国忠。”说着,将手中一个纸包递给宇文关山,又说,“他说,您只要看到它就一定会见他。”宇文关山疑惑地将纸包打开,里面是一本陈旧的小书——《格瓦拉日记》,翻开封面,扉页上是一个钢笔签名于红旗。宇文关山闭上眼睛,快三十年了,这个名字差不多已经被遗忘了……缅甸的热带雨林。炮火冲天。56式冲锋枪响得跟炒豆似的,弹壳砰砰往外跳。散落在几个年轻人身边,又一发炮弹呼啸着飞过来,一个年轻人将身边的战友扑倒,炮弹落地,就在不远处,一个人被弹皮削开的肚子,五脏六腑红红绿绿的都往外流。被炸开的泥土埋了的两个年轻人,从土里钻出来。下面的那个年轻人说:“任国忠,我欠了你一个人情……”大都酒店宴会厅里灯火辉煌,人声鼎沸。晚宴已进入高潮。总编辑理万机率领报社其他领导轮番给每桌属下敬酒。祝酒词从新的利润增长点到如何创收,从员工的福利待遇到对未来的展望,虽说不过片言只字,该说的都说到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感染着在座的每个人。笑声叫声响成一片。理万机注意到兰翎旁边的座位还空着,就问:“谁的?怎么还不来?杜鹃呢?”兰翎随口说:“还在画版面呢。”说着,伸长了脖子,望着餐厅的门口,掏出了手机,接通后说:“你怎么还不过来?报社的人都到齐了,就你清高?快点着啊。”理万机说:“你这人,这和清高不清高有什么关系?一会儿,她来了,连罚三杯。”兰翎说:“她说了,这就来。”理万机说:“来了就好。”说着,又率领报社其他人去别的桌敬酒了。
酒店四楼的一个标准间里没有亮灯,借着从对面大厦透过来的天光,可以看到一个男人悄然无声地站在窗前,掀开窗纱的一角往外看,顺着他的目光,酒店的地上停车场尽收眼底。他的眼睛一眨不眨,看着车子进进出出,来来往往,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终于,一辆毫不起眼的白色拉达,缓缓驶进停车场他指定的车位,他看在眼里,才吁了口气,转身走到行李架上,搬过一个巨大的黑色旅行箱,搁在床边,然后,抱起床上的一个已经没气的男人,折叠着放进箱子里。他要合上箱盖时,还露出挺宽的缝隙。他便把屁股坐上去,压了几回,还是有缝,他索性跳到了箱子上,跺了几脚,蹦了几蹦,不愧是法国Delsey原装货,弹了几弹,那箱盖便扣了个严丝合缝。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