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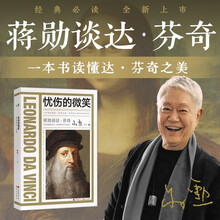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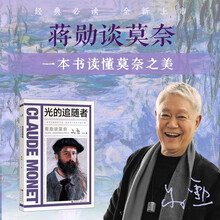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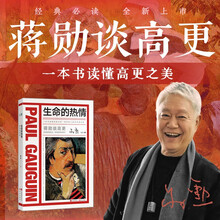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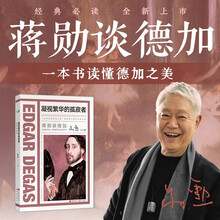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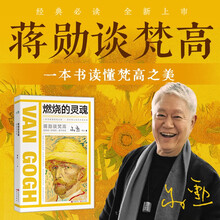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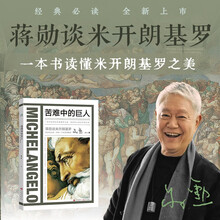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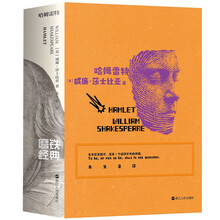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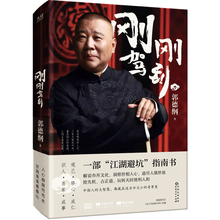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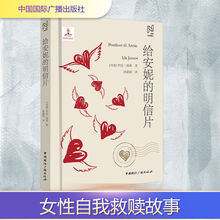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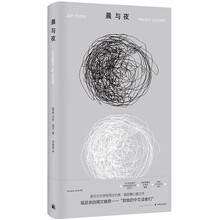
这本小说集收选了于晓威近年来在国内外文坛创作发表的有影响性的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继承了作家一以贯之的风格取向,即题材各异,手法多样,语言凝炼,观念新颖。做为国内“七O年代出生”代表作家之一,作家对小说的诗学态度、对人性的洞悉、对叙述机制的睿智了解、对艺术表达的独辟蹊径,令读者惊叹与痴迷。
“字码头”读库丛书第二季是反映辽宁省当代作家高创作水平的经典文学作品出版工程,集结了一批省内高水平的知名作家的优秀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去年“字码头”读库第一季的出版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力,如今,第二季的作品整装待发,这一经典文学丛书,将会在辽宁省内文学界、出版界、文学爱好者群体之中产生更大的反响。
这本《“字码头”读库·辽宁舰:午夜落》辽宁籍著名作家于晓威的小说集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几部具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于晓威的写作风格是多变的,本书中几篇都市题材的小说中,他将都市的现代性转化为个体生命体验,在诱惑、抗争、屈从、无措和无奈的淆乱中,闪现着体恤和冷酷;而在打破了虚构和体验界限的向内叙述中,他又专注于文本自身,在历史与虚构、现实与书写边界模糊地带,倾听到来自日常褶皱中的躁动和平常感知所无力察觉的惊雷之声。
厚墙没想到这条路会这么寂静,静得像不被风吹动的雾一样。路两边的缓坡上长着密实的野草,下面是明亮的沟渠,再远处,是无尽的庄稼和几排稀疏的树林,空气新鲜得简直如头上传来的鸟叫一样清晰可辨,真是太好了。
他几次想停下来脚步,毕竟不是年轻人了,晨起跑步锻炼还应适可而止,但是那条洁白驯服的路面不断吸引他继续跑下去。是啊,城市里可供跑步的道路越来越少了,像他念中学时,每天上学路上,会看到许多老年长跑队穿梭在马路上,如今各种汽车越来越喧嚣拥挤,尾气的排放危害远大于锻炼得来的益处,况且交通意外指数也不断增加,那些一茬茬喜爱晨跑的老年人,只好挤在广场或公园里的固定处,由下身运动改为上身运动,打打拳或敲敲背了。
这是秋天。看着远处的房屋,他停下脚步。他再一次想起当年下乡插队的情形。无数的城里年轻人,怎么会突然潮水般涌向农村呢?与当地农民在一起,那完全是两种不同形态的人。他什么都不会做。他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农活,也是秋天,与当地的农民一起割地收玉米。他们的目标是脚前宽阔无边的玉米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坡下,每人割六垄。大队书记一声令下,当地农民争先恐后,等他脱去衣衫卷好裤腿提着镰刀下地时,人家已经放倒了几十棵玉米了。他割呀割的,汗水很快出来了,乱七八糟和粗糙柔软的玉米叶子,很快将他的胳膊、肩膀、脖颈划出一条条印子,被汗水一浸,火辣辣地疼。他这才知道自己太嫩了。十八九岁的年纪,他会懂什么!难怪人家大热天也都长衣长裤的,开始他还笑话人家呢。他不记得其间休息了多少次,反正从早晨割到中午,从中午割到傍晚,人家都早已收工了,只有他和另一位个子矮小的大连知青还在割。大队书记说了,明天有暴雨,时间太紧了,一天的工夫必须割完。好,夜了,星星出来了,他太乏了,就躺在割倒的玉米秸堆子上,不知不觉睡着了。那位大连知青在行动上似乎比他还要笨拙和沮丧,直到他醒来了,那位同伴才割到与他相同的进程。他们一直割到凌晨五点,天快像碗里的白水一样亮了。这才发现,这片广袤的玉米地因地势差别,南边地头距离山坡很近,而北边地头距离山坡奇远,自然,南边的田垄也短,劳动量也少,难怪当地农民都争先恐后奔向南边,谁有他们熟悉地形呢?
远处有更多的炊烟升起。他看了一眼手表,差五分钟六点了。今天是周一,回去后要早点上班。他慢慢转过身子,向来路跑去。就在这时,他看见了他,一个举止敏捷而胆怯的少年。
其实最先闯入他眼帘的是路边一辆笨重而破旧的自行车。它停放在那里,身上负重的程度让人误以为它是一台三轮车。它的货架子上载着颜色昏暗的行李,虽说天热,可那竟是棉被,打着补丁。车的一侧横拴着比邮递员装邮件还要大的帆布口袋,东倒西歪,不知里面装着什么破烂物品。自行车的前把子上,一边吊着一只涂着红漆的旧茶缸,另一边绑着一条毛巾。毛巾洁净得刺眼,反倒昭示出它的主人身处的何等凌乱而扭曲的生活。再一扭头,他看见了那个少年,正背对着他,蹲在路旁,用沟渠里的水一把把洗脸。
他已经经过少年两步了,可是忍不住回头。少年应该是一个乞讨的人,落魄的样子让他感觉自己早晨的锻炼显得多么奢侈。他下意识掏了一下运动服的裤兜,还好,竟然有触碰纸币的手感,掏出来一看,是拾圆钱。他想起来了,自己跑步锻炼的运动服里是从来不揣钱的,是早起时妻子塞给他,让他顺路买豆浆和油条。他怕打扰了少年,悄悄回去,把捏着的钱放到自行车上,掖在捆行李的细绳下面。
那一刻,少年恰好回头看了他一眼。少年只恍惚看到他一张短暂照面的脸。他转身继续跑动的时候,只听到身后传来清亮亮的拂水声,一下一下的。
他和包工头站在自己新买的房子里,他们已经核计好久了。这个包工头,是他找的第四个包工头了。他也感觉自己必须得抓紧时间。北方的秋天正是装修忙季,装修工人奇缺,便是眼下联系的这个包工头,手上还有好几个业主的活要做。他们两人站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谋好了装修方案,算好了材料费,定好了工期,就在他送包工头下楼的时候,包工头又踅回身子,叮嘱了一句:“记住,这三堵墙一定在两天内全部砸掉,否则误了时间,我只能先去干别人家的活了,把你排在后边,”
“啊?”他问,“这墙不是你们砸?”
“当然不是,”包工头黑瘦的脸,只叼着的烟卷和牙齿是白的,“连这规矩都不懂?我们只管装修,砸墙是另外的人的事。”
“我到哪里去找啊?”他问。
包工头从兜里掏出个小本本,低头翻了一翻,“这样吧,我给你介绍一个,这是他的电话号码。”
包工头走后,不到十分钟,砸墙的人来了。按包工头的设计,他要砸掉客厅和主卧室的一面墙,使客厅变得阔大明亮;要砸掉客厅与厨房间隔的墙,把那里装成一个电视背景墙;要砸掉储物间与副卧室的墙,变成日本式拉门。砸墙的人弄清了他的意图,开价八百元。
他在心里叫了起来。这个价钱,是他每月工资收入的一半。他摇了摇头,问:“便宜一些吧?”砸墙的人不屑地摇摇头说:“一分钱不能少,你知道这要出多少力?要不你去找别人试试吧。”
他想把价钱讲到四百五十元,砸墙的人死活不同意。末了,他只好放他走,又给包工头打电话。包工头说:“没关系。装修的工人不好找,砸墙的民工到处都是,你到街上去转转看。”
其实包工头也是个农民,但是他习惯了这么说。
他来到街上转了转。真是不转不知道,一转下一跳,他转了不过两条街,就看见许多下岗工人和农民们,蹲在路边,面前竖着小牌牌,上面写明各样技能和工种,待人雇佣:什么瓦工、电工、油漆工、保姆……当然也有砸墙工。以前他上下班,心思不往这边想,竟对这些人熟视无睹。现在看来,这些人不知存在多少年了。他上去搭讪一个砸墙工,立刻有五、六个砸墙工围了上来,问他砸什么样的墙。
“你们去看一看吧,不过话说回来,价钱谈不好,我可不付腿脚费。”
大家簇拥着来到他的家,在七楼。进了门,简单听他一指点,一个五十多岁的砸墙工说:“怎么少也得五百元。”
他心里暗觉此性颇有收获,不过他还是想把价钱压到四百五十元,那是他给自己定下的一个可以承受的限度。争讲了七、八分钟,谁也无法说服谁,有一个砸墙工最先低着头出去了,接着又出去一个,剩下的几个人互相瞅了瞅,干脆都出去了。他愣了一下,也只好跟着往下走,倒不是出于礼貌送客,而是他还得继续上街找砸墙工。
就在刚刚下到一楼门口的时候,他觉得身后衣摆被谁扯了一下,应该是那些砸墙工当中的某个。回头看,是一个少年,大约十七八岁,很瘦弱。他不认得这个少年,自然,也不知道他扯了他一下是什么意思。“我砸。”少年小声说。少年觉得这个房主似乎面熟,但是记不住在哪里见过他。“你?”他问,打量了少年一眼,似乎不相信少年的手艺与体能。“我砸。”少年又小声重复一遍,比第一次说出的这句话多出一点口吃,但是一下子说到他心里去了。“我只要四百五十元。”
在一个小他差不多三十岁的少年面前,他不好意思立刻表露他的暗喜。他看看已经走远了的那些砸墙工的背影,冲少年点了点头。
少年径直向大街上走去。
“喂!”他喊。
“我去拿工具。”少年说。
没想到这条路会这么寂静,静得像不被风吹动的雾一样。路两边的缓坡上长着密实的野草,下面是明亮的沟渠,再远处,是无尽的庄稼和几排稀疏的树林,空气新鲜得简直如头上传来的鸟叫一样清晰可辨,真是太好了。
他几次想停下来脚步,毕竟不是年轻人了,晨起跑步锻炼还应适可而止,但是那条洁白驯服的路面不断吸引他继续跑下去。是啊,城市里可供跑步的道路越来越少了,像他念中学时,每天上学路上,会看到许多老年长跑队穿梭在马路上,如今各种汽车越来越喧嚣拥挤,尾气的排放危害远大于锻炼得来的益处,况且交通意外指数也不断增加,那些一茬茬喜爱晨跑的老年人,只好挤在广场或公园里的固定处,由下身运动改为上身运动,打打拳或敲敲背了。
这是秋天。看着远处的房屋,他停下脚步。他再一次想起当年下乡插队的情形。无数的城里年轻人,怎么会突然潮水般涌向农村呢?与当地农民在一起,那完全是两种不同形态的人。他什么都不会做。他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农活,也是秋天,与当地的农民一起割地收玉米。他们的目标是脚前宽阔无边的玉米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坡下,每人割六垄。大队书记一声令下,当地农民争先恐后,等他脱去衣衫卷好裤腿提着镰刀下地时,人家已经放倒了几十棵玉米了。他割呀割的,汗水很快出来了,乱七八糟和粗糙柔软的玉米叶子,很快将他的胳膊、肩膀、脖颈划出一条条印子,被汗水一浸,火辣辣地疼。他这才知道自己太嫩了。十八九岁的年纪,他会懂什么!难怪人家大热天也都长衣长裤的,开始他还笑话人家呢。他不记得其间休息了多少次,反正从早晨割到中午,从中午割到傍晚,人家都早已收工了,只有他和另一位个子矮小的大连知青还在割。大队书记说了,明天有暴雨,时间太紧了,一天的工夫必须割完。好,夜了,星星出来了,他太乏了,就躺在割倒的玉米秸堆子上,不知不觉睡着了。那位大连知青在行动上似乎比他还要笨拙和沮丧,直到他醒来了,那位同伴才割到与他相同的进程。他们一直割到凌晨五点,天快像碗里的白水一样亮了。这才发现,这片广袤的玉米地因地势差别,南边地头距离山坡很近,而北边地头距离山坡奇远,自然,南边的田垄也短,劳动量也少,难怪当地农民都争先恐后奔向南边,谁有他们熟悉地形呢?
远处有更多的炊烟升起。他看了一眼手表,差五分钟六点了。今天是周一,回去后要早点上班。他慢慢转过身子,向来路跑去。就在这时,他看见了他,一个举止敏捷而胆怯的少年。
其实最先闯入他眼帘的是路边一辆笨重而破旧的自行车。它停放在那里,身上负重的程度让人误以为它是一台三轮车。它的货架子上载着颜色昏暗的行李,虽说天热,可那竟是棉被,打着补丁。车的一侧横拴着比邮递员装邮件还要大的帆布口袋,东倒西歪,不知里面装着什么破烂物品。自行车的前把子上,一边吊着一只涂着红漆的旧茶缸,另一边绑着一条毛巾。毛巾洁净得刺眼,反倒昭示出它的主人身处的何等凌乱而扭曲的生活。再一扭头,他看见了那个少年,正背对着他,蹲在路旁,用沟渠里的水一把把洗脸。
他已经经过少年两步了,可是忍不住回头。少年应该是一个乞讨的人,落魄的样子让他感觉自己早晨的锻炼显得多么奢侈。他下意识掏了一下运动服的裤兜,还好,竟然有触碰纸币的手感,掏出来一看,是拾圆钱。他想起来了,自己跑步锻炼的运动服里是从来不揣钱的,是早起时妻子塞给他,让他顺路买豆浆和油条。他怕打扰了少年,悄悄回去,把捏着的钱放到自行车上,掖在捆行李的细绳下面。
那一刻,少年恰好回头看了他一眼。少年只恍惚看到他一张短暂照面的脸。他转身继续跑动的时候,只听到身后传来清亮亮的拂水声,一下一下的。
他和包工头站在自己新买的房子里,他们已经核计好久了。这个包工头,是他找的第四个包工头了。他也感觉自己必须得抓紧时间。北方的秋天正是装修忙季,装修工人奇缺,便是眼下联系的这个包工头,手上还有好几个业主的活要做。他们两人站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谋好了装修方案,算好了材料费,定好了工期,就在他送包工头下楼的时候,包工头又踅回身子,叮嘱了一句:“记住,这三堵墙一定在两天内全部砸掉,否则误了时间,我只能先去干别人家的活了,把你排在后边,”
“啊?”他问,“这墙不是你们砸?”
“当然不是,”包工头黑瘦的脸,只叼着的烟卷和牙齿是白的,“连这规矩都不懂?我们只管装修,砸墙是另外的人的事。”
“我到哪里去找啊?”他问。
包工头从兜里掏出个小本本,低头翻了一翻,“这样吧,我给你介绍一个,这是他的电话号码。”
包工头走后,不到十分钟,砸墙的人来了。按包工头的设计,他要砸掉客厅和主卧室的一面墙,使客厅变得阔大明亮;要砸掉客厅与厨房间隔的墙,把那里装成一个电视背景墙;要砸掉储物间与副卧室的墙,变成日本式拉门。砸墙的人弄清了他的意图,开价八百元。
他在心里叫了起来。这个价钱,是他每月工资收入的一半。他摇了摇头,问:“便宜一些吧?”砸墙的人不屑地摇摇头说:“一分钱不能少,你知道这要出多少力?要不你去找别人试试吧。”
他想把价钱讲到四百五十元,砸墙的人死活不同意。末了,他只好放他走,又给包工头打电话。包工头说:“没关系。装修的工人不好找,砸墙的民工到处都是,你到街上去转转看。”
其实包工头也是个农民,但是他习惯了这么说。
他来到街上转了转。真是不转不知道,一转下一跳,他转了不过两条街,就看见许多下岗工人和农民们,蹲在路边,面前竖着小牌牌,上面写明各样技能和工种,待人雇佣:什么瓦工、电工、油漆工、保姆……当然也有砸墙工。以前他上下班,心思不往这边想,竟对这些人熟视无睹。现在看来,这些人不知存在多少年了。他上去搭讪一个砸墙工,立刻有五、六个砸墙工围了上来,问他砸什么样的墙。
“你们去看一看吧,不过话说回来,价钱谈不好,我可不付腿脚费。”
大家簇拥着来到他的家,在七楼。进了门,简单听他一指点,一个五十多岁的砸墙工说:“怎么少也得五百元。”
他心里暗觉此性颇有收获,不过他还是想把价钱压到四百五十元,那是他给自己定下的一个可以承受的限度。争讲了七、八分钟,谁也无法说服谁,有一个砸墙工最先低着头出去了,接着又出去一个,剩下的几个人互相瞅了瞅,干脆都出去了。他愣了一下,也只好跟着往下走,倒不是出于礼貌送客,而是他还得继续上街找砸墙工。
就在刚刚下到一楼门口的时候,他觉得身后衣摆被谁扯了一下,应该是那些砸墙工当中的某个。回头看,是一个少年,大约十七八岁,很瘦弱。他不认得这个少年,自然,也不知道他扯了他一下是什么意思。“我砸。”少年小声说。少年觉得这个房主似乎面熟,但是记不住在哪里见过他。“你?”他问,打量了少年一眼,似乎不相信少年的手艺与体能。“我砸。”少年又小声重复一遍,比第一次说出的这句话多出一点口吃,但是一下子说到他心里去了。“我只要四百五十元。”
在一个小他差不多三十岁的少年面前,他不好意思立刻表露他的暗喜。他看看已经走远了的那些砸墙工的背影,冲少年点了点头。
少年径直向大街上走去。
“喂!”他喊。
“我去拿工具。”少年说。
……
沿途
眩晕
一曲两阙
厚墙
今晚好戏
午夜落
房间
天气很好
勾引家日记
在淮海路怎样横穿街道沥青
让你猜猜我是谁
不屈不挠的生长
★冷静、温情、敏感、机智,不断地尝试与游走——这使于晓威看上去没有定性,同时成了一个文学名利场外的游手好闲者。不过,这确实是一种难得的品质。于晓威让人看到一种对于题材、形式、内心探索、精神空间永不满足的探求,这种不屈不挠的生长性,较之于那些迅速成熟、并且世故了的作家们,或许正是文学尊严的最后阵地。
——刘大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