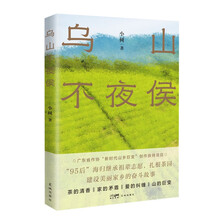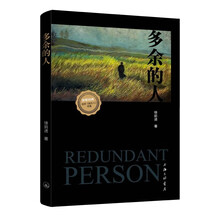我跟知了掰了。
即便掰了,我们还死缠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上下课,一起散步,一起打球,一起睡觉,一起欣赏俊男靓女……一起个没完没了,没终没止,简直可以地老天荒。
真他妈虚伪!而虚伪是我俩在T大的唯一收获。
我们把这标签贴在表层,逐渐深化到皮肉里,渗入肌肤,待它腐烂,便伪装成保护色,让我俩重新大放异彩,可与花魁媲美。我们每天就带着重重盔甲一起行事,劳心劳力到骨子里。
看看其他女孩儿们的二人世界:一群群、一对对都是有说有笑的,肩并肩,手拉手,亲密得叽叽喳喳,吴侬软语,一个人的眼里映着另一个人的眼,容不得第三者插足。
而我和知了,我们走路一前一后,看不出谁跟着谁,拎着各自的包,想着各自的心事,甚至避免眼神相撞,却又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默契。下课了就会自动走到一起;一方有事,另一方不动声色地恭候。不像有的女孩,等情人约会般,眼睛死盯一处,焦急得恨不能一下暴长十公分,脖子做长颈鹿状,就差打出一块广告牌,昭告天下朋友:本小姐在这儿呢!
我们呢,哼,我们相互挤压,相互消耗,相互折磨,彼此窥探又怀着恶意,却谁也离不开谁。我们是小丑,我真想对着我和知了的灵魂作呕。
这天,下了课,到食堂,我们照旧对面而坐。
知了又点了那份让我受不了的白菜萝卜汤。
多少次我暗地里发狠,想把那要死不活、色泽瘦弱的汤迎头泼在她脸上,再啐口唾沫。她就好那口,怪谁呢?我记不起她自打什么时候起现回原形,俗态毕露,连点菜都千人一面,千面一腔,如此没有创意。我心里嗤笑,表面上却不露声色。
我瞟了她一眼,但没有看她。为了防着作弊时如间谍般敏锐的知了,我对这些暗里来阴里去的动作招数颇为熟稔,我决不允许因为我的一点失误而让她侥幸及格。
我曾一度因此害怕自己得斜视。
她也在看我,同样没有直视我的眼。
我怀疑自己看错了。
我又装作不经意地瞟了她一眼。
她真的在看我。
如果不是“身在此山中”,我想那情景一定非常可笑:两个人偷偷摸摸地看着彼此,视线贼溜溜、毛茸茸地扫视过一排不相干的事物,各自停在一个诡异的角度,趁对方知觉放松时侵入,却在半路中遇到敌方两相交缠的视线。这过程好比饿狼捕食,先佯装小憩,再扑入猛攻,没料及两相行动,便当场鸡飞蛋打,血肉模糊。
我和知了的目光相遇,短兵相接,那目光便停了,死了。
我猜想她有话对我说。
我们各自不自在地闪开眼,我们不习惯对视。
果然她开口了,清清喉咙,如同整理淤积的下水道,她问我:你最近好吗?
哈!如果不是在公众场所,我真想放声狂笑。我们每天死缠在一起,彼此为伴的时间过得如此艰难而缓慢,一天可以凭空长出四十八小时,简直是拨弄着秒针过日子,而她居然恬不知耻地问我最近好吗?她真蠢!她想挑衅?她想修补我们的旧日情缘?没可能!我不会给她机会了。她是在向我示好吧?肯定是!
我盯着她庞大臃肿的体态,那身形装下两个我还富富有余,我有些可怜她。
我表情散淡,挺好!
我想这回答可进可退,没一点儿屈尊向她示好的意思。
她再续前话:你觉得我们这样有劲吗?
我涣散的神经瞬间集合起来,脑子一阵发蒙。什么意思?她想散伙?
她的突然让我紧张得嘴唇都发虚。我琢磨着摊牌的阴谋她策划已久,就是要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我恨透了她的阴险。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又担心一个不小心,失了口,连目前这种名存实亡的关系也在我嘴上葬送掉,只得强打精神,紧急拼凑出一副声色俱厉的眉眼,语言却绵软得不具备任何攻击性: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恨不得为自己的嘴拙跳楼。
她逮到机会爆发了:我受够了!你明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虚伪得直想扇自己耳光,可我真的害怕失掉她这个可怜可鄙的陪伴。它是我在T大得以浮生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嘴上装傻:怎么了?我们一直是好朋友啊!
她嗤笑出声,露出一口白牙,她是如此明目张胆,她用唇齿在追杀我。
她举起汤碗,又重重放下,“砰”地一响,汤洒出一半,沾在她手上:我需要换换口味。
我抬起眼帘看她,那下面掩藏着我蔑视而又哀求的目光,我厌恶我自己这副嘴脸。
就好像这汤,我每天都喝白菜萝卜汤,每天都喝,喝成习惯,喝成依赖,可是总有喝够的时候。
她居然把我比喻成那令我作呕的汤,前一秒我还想把它泼在她脸上,可现在我成了那秽物,她想像丢残汤一样丢掉我。
我死死看着她,看她还能用什么辞令侮辱我。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噪声里任她鞭笞。
她动用了别的手段,她只是拿眼睛——她身体上唯一美丽的物件——看着我,我恍若又看到了在我们身上业已灭绝的哀伤和真诚浴火重生。
放过我们自己吧。她说。
不行!
我真的拿汤泼了她,她的脸成了一锅鸡蛋汤饭,我抽了她耳光,一个接一个,那声音在偌大的食堂引吭高歌,反复回响。知了匍匐在我脚下,口吐鲜血,乞求我原谅她,所有的人都在鼓掌为我喝彩。我赢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