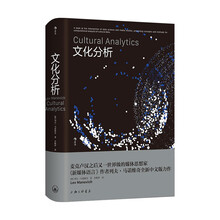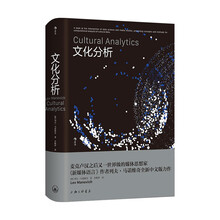《砚田集》:
序一 本相剧学浅论
宁宗一
本相,本相,这个平常又亲切的称呼,被叫了几近一个甲子,我比他长一岁,他有时称我为宁先生,有时叫我宁兄。而五十八年的友谊就是在情意和信任中缓缓地,有时疾速地度过了!五十八个岁月相聚相会大多是围绕着戏剧,戏剧又确实使我们有了一条连结线。这期间,我经常接受他的“指令”参加一些并非我专业方向的学术会议,其中最多的是围绕曹禺先生的纪念与研讨活动,甚至建立曹禺先生故居和纪念馆的设想的研讨会他也会拉我参加。我深知他有意把我这个学术上没啥创获的教书匠拉入这个层次的学术圈子里,而我也确实在这个圈子里提升了见识。这一切我心知肚明,因为这是老友温情的关怀与安慰,同时也含有激活我的生命因子的期盼吧。
但是,不久前我接到本相的电话,他直奔主题,提出想让我为他的《砚田集》,有关他写的和主编的著作的评论集写一则小序,并说立即把有关的文章发到我的邮箱中。过去我对本相的任何指令都是照办无误。可是这次我却几乎不假思索地在电话中拒绝了。我坦诚地对他说,让我干什么都可以,唯独书写“评论集”的序言我实难应命,因为我完全可以估量到,写这些文章的朋友肯定是戏剧研究界的行家里手,并深知本相在曹学与话剧学方面的贡献,随便抽出一篇都可以是上佳的书序!本相电话中说他是斟酌再三才觉得我是合适人选。当然,最后是以我的妥协而敲定。这番周折绝非是我的谦逊,也非我的懒散,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我心态上的胆怯。对,胆怯。这是我过去在给友人书写序文和书评时难见的一种心态。可以坦诚地说,面对本相的十二卷大作和诸多评论大家,我已为自己设定为“外人”了。如果说我还有点“本钱”,不外乎我是曹剧的忠诚的崇拜者,对话剧艺术也曾痴迷过。但我深知和本相及其同行不是站在一个层次上,说出的话难免露怯!
说这些话,既不是为今天这篇漫笔式小序做什么铺垫,也非为自己的浅薄遮丑,而是想与本相的挚友们一道参与本相剧学的研讨,交流一些我的点滴体会,其中肯定会有诸多外行话,趁此机会也望诸位朋友给予指正。
一
对于本相剧学,无论是近距离还是远距离去观照,我认为他是循着这个脉络发展而来的: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在读李何林先生的硕士学位时,三年探索,他对曹禺先生剧作的精魂与诗意已有所发现。有这样一个故实,当时在我们这些喜欢戏剧艺术的师生中流行一部被授予斯大林文学奖的书:叶尔米洛夫的《论契诃夫的戏剧创作》。一次我们俩就他的硕士论文初稿聊起了这部书。巧合的是我们都对叶氏的“潜流”说发生兴趣。本相从中获得了灵感和启示,他发现了曹剧也有一股“潜流”;而我则是从关汉卿的剧作中看到了这股“潜流”。我们俩都认为对戏剧巨匠的创作,必须挖掘其底蕴和把握这“潜流”,因为这是理解文本的要穴。也许由于大师的剧作都具有这种直接的现实背景下一股缓缓流淌的“潜流”,它的生活底蕴往往不是一眼就可以看清的,因此挖掘它就成为理解文本审美价值的关键。叶氏找到了契诃夫剧作中的“潜流”,于是他把契诃夫研究提升到一个新高度;而本相也找到了曹禺剧作中的“潜流”,于是本相的曹禺剧作论就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发现了曹氏剧作取之不尽的隐性价值。话剧艺术发展史也充分证明曹禺的经典剧作都具有这种超越题材、超越时空的象征意蕴,而这象征意蕴正是有待我们开发的隐性价值的“潜流”。
我们那时还和黄克一块交流过悲剧性和喜剧性交叉点的问题,这个命题,追溯其根源,是别林斯基提出来的。就我的论忆,别氏是在《一八四三年的俄国文学》一文中提到:“群众只懂得外部的喜剧性,他们不懂得有一个喜剧性和悲剧性交叉之点,所唤起的不是轻松的、欢快的,而是痛苦的、辛酸的笑声。”本相正是在长期的曹禺研究中看到了他的人生、心灵和剧作不仅仅是悲剧性的正剧性的,而是看到了他的人生历程与剧作潜隐着那“悲剧性和喜剧性交叉之点”所产生的人生的永恒遗憾和不尽的况味所产生的强烈的艺术冲击力。本相在把握曹剧的审美价值时没有停留在体验、感悟黑暗王国的深渊中,所有正剧性的、喜剧性的东西都会激起悲剧性的回想,他体悟到的则是在悲喜的交叉点上人性的正负面和心灵上的冲突,这是他深一层次地理解戏剧的辩证法,当然也是历史的辩证法的表征。在我看来,本相的曹学研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初步看到了曹禺剧作悲剧性的独特性,即伟大的剧作家从社会悲剧出发,创造了自己的戏剧性体系,在他的经典剧作中把悲与喜,美与丑,崇高与滑稽融合无间,构成了一个浑然一体、独具一格的艺术世界。因为本相已经一步步透视出曹禺剧作乃是他苦闷心灵的外化,他想唤起人们的不仅是沉重的、痛苦的、不能抑制的泪水;正如他的剧作中出现的某些喜剧性,也不是要唤起轻松的、欢快的笑声,而是想启迪人们思考他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这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笑和泪只隔一张纸,恐怕只有尝过泪的深味的人,才真正懂得人生的笑。”曹禺剧作中揭示的正是人生的深味。这是一种“智慧的痛苦”。我们从本相的《曹禺剧作论》中看到曹禺剧作中的诸多“隐喻”,和生命中的痛苦,所以我才敢于说,本相的曹禺研究起点很高,而后更提升到心灵史和戏剧美学的新的层次上了。这样的研究成果已经昭示,他以后的“诗化现实主义”戏剧观念此时已开始萌发。
如果说《曹禺剧作论》还是以文本诠释作为本相的研究策略的话,那么,它在研究界产生巨大影响又被曹禺所首肯、所赞赏后,本相没有放慢脚步,而是以采访形式直接走进曹禺的内心世界。这种面对面的心灵对话,开始了他的文本与对话相互参订、同步研究的新阶段。《曹禺传》、《苦闷的灵魂》就是这项同步研究的积极成果。这里,我倒想横插一笔,本相的这种研究策略引发了我的反思。因为,从前我一直遵循的是“回归文本”的理念,这是受了海涅和海明威等作家只言片语的影响,所以对作家生平资料和访谈录缺乏信任感,总怕他们“心口不一”,于是宁肯以文本第一的态度来对待作家心史的另一半。其实,今天一经反思,就会发现,历史过程和社会发展及诸种生活方式影响着作家的心灵,所以现代人对自己心灵历程的兴趣或许大多与对政治经济历程的关心有关。作为反映人类历史中成为精神文化底层基础的感性、意绪、伦理模式和思维习惯的作家心灵应该也必须成为研究者从事探索的重要课题。因为这一切不可能在文本中都得到体现。本相正是在多次与曹禺面对面的心灵的直接交流过程中,他们之间的心灵终于在互动中得到契合。于是在我们打开《苦闷的灵魂》时,才会如此明快地看到,在书的纸底和纸背,蕴藏着“两个人”的郁勃之心灵脉动,蕴藏着对于文化专制主义的反抗之音。因此,我们不透过作家的直面现实的话语去追溯其灵魂深处,又如何能领会曹禺以自己的心灵所感受的时代和人民的心灵呢?所以我才在一次和友人闲谈时提到本相的《苦闷》一书,对我过去的认知和理念是一次很重要的校正。他启示了我,对待具有心灵史性质的经典作家及其文本,我们既要深入作家的灵魂,也要纵目他们所受规范的社会心灵总体。具体到本相解剖曹禺的苦闷灵魂时,正是他透过了曹禺的感性深处乃至一个发人深思的心灵悸动作为突破口,去综观时代风云与思潮。所以,本相的曹学绝没有停留在所谓“人学”的层面,而是深入到心灵史这一更为重要的层面,并给予审美观照。于是我们既感受到了本相的发现,随之,我们也得以认知了曹禺的心灵底蕴,明白了曹氏剧作中的诸多“隐喻”。《苦闷》一书让我联想到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的那句至理名言:“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一切关于心灵的知识都是历史的。”信哉斯言。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