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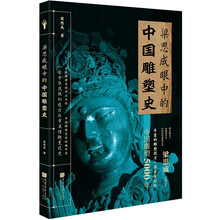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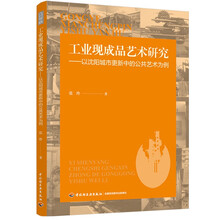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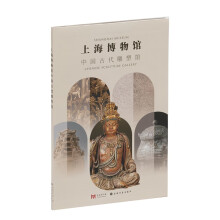
《雕塑艺术宏层说》:大多数雕塑家、雕塑工作者和爱好者在从事雕塑创作时少有系统的理论,加之许多美术史论研究者又很难对相对于绘画更复杂的雕塑有更切身的感受和理解,至多展开的是史学研究,因而,百年来中国不仅少有中外雕塑史的深入研究理论著作,对雕塑创作实践进行系统的梳理,尤其是结合现当代世界雕塑发展潮流和整体趋势来展开相应的论述和理论研究,切实能够指导雕塑艺术创作实践的理论著述则少之又少。胥建国先生是中国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清华大学文学博士)的雕塑家,《雕塑艺术宏层说》的出版即适以于当今中国雕塑现实发展需要,具有理论引导和解惑答疑的作用,也适应于在较长时期作为雕塑工作者和爱好者的工具书,作为理论指导。
本书为16开本图文版,附有七十多幅图片,其中还有十几幅作者1994年出版的《黑白装饰画》插图。
《雕塑艺术宏层说》:本书以论文和访谈形式,宏观比较了中西方雕塑的文化内涵,论述了中国传统雕塑的艺术精神、造型观念和西方雕塑的造型语言、空间演变,从本体角度多层次探讨了传统与现代、抽象与意象等问题。通过艺术实践,从理论上对公共艺术和城市雕塑设计、大型雕塑活动策划以及国际雕塑公园建设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音乐与雕塑漫谈
说起音乐与雕塑,浮现在眼前的就会有大足大佛湾的《吹笛女》和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窟顶莲花宝盖四周的飞天。《吹笛女》是大佛湾《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巨龛中的一座人像雕刻,它突破了佛教造像宣教的范围,表现了一个面容秀丽、全神贯注吹奏筚篥的女孩子形象,造型生动朴实,展现了四川女孩儿典型的相貌特征。龙门宾阳中洞窟顶的八个飞天,环绕莲花弹琴鼓瑟,天衣飞动,裙带当风,营造出了一派欢乐祥和的气氛,体现了《法华经·譬喻品》所讲述的“诸天伎乐,百千万神,于虚空中,一时具作,雨花光华”的景象。①
这种表现音乐演奏的作品在中国传统雕塑中值得提及的还有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北平王王处直墓中的散乐图汉白玉敷彩浮雕。浮雕画面最前面塑造了一位身着男装的引道者和两个跳舞的小童,后面上下两队站立着15位女乐,演奏的乐器有竖箜篌、筝、曲颈琵琶、拍板、大鼓、笙、方响、答腊鼓、筚篥、横笛等,俨然是一个完整器乐演奏队的形象。女乐们身着长裙,体态丰腴,高髻簪花,面色圆润,展现出了盛唐美人的风韵。形象和动态在统一中有变化,头饰与服饰在变化中又有统一,堪称后唐时期的经典作品。
从世界范围看,以音乐家或音乐演奏为表现题材的雕塑更是举不胜举,但能将音乐节奏与雕塑形式完美结合的雕塑则当属吕德为法国巴黎凯旋门创作的《马赛曲》。这件反映1792年法国人民为保卫祖国,奋起抵抗奥地利入侵的作品,整个构图上下呼应,节奏鲜明,如同一首雄壮的进行曲,号召着人们奋勇向前,在精神上给予了法国人民极大的鼓舞。
然而,音乐和雕塑虽说都从属于艺术,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但毕竟两者间还有着诸多的不同。音乐是听觉艺术和时间艺术,依靠声音的高低、强弱以及节奏的快慢在时间延续过程中与人进行交流,进而产生情感共鸣,或陶冶情操,或振奋精神;雕塑是视觉艺术和空间艺术,主要通过各种材质制作成的不同形象,以及形象诠释的内容和在空间中占据的位置大小、分量轻重所引发的心理感受,来实现其艺术创作的目的,达到纪念性、标示性或装饰性等功用。
源于音乐和雕塑艺术形态的不同,音乐比雕塑拥有着更加宽阔的想象空间,可以跨越时空,用音符描述大自然的万千景象,回到远古或走向未来,也可以超越族群,超越语言,挖掘人内心最深处的情思,成为连接人类共同情感的纽带。
雕塑不同于音乐的地方是在于它的直观性,通过视觉可以直接传达作品蕴含的寓意,触及人的心灵,并通过体量、质感和肌理在空间中给予人不同的感受。雕、塑、刻的方式涉及到人类许多的创造性劳动,包括音乐所有乐器的外部造型、表面纹饰、内部构造等。
韵,最初指声音的和谐,声为起、为主,韵为和、为从。气与韵的关系就如同声与音的关系,韵的产生依赖于气,无气则无韵,但没有韵的气也会缺乏生机,会“死气沉沉”。气偏于刚,韵偏于柔,二者融为一体方能刚柔并济,达到对立的统一。这也是谢赫“六法”将“气韵生动”放在首位的原因。
山西平遥双林寺第二院落东侧千佛殿主像右侧的韦驮像和山西华严下寺薄伽教藏殿彩塑菩萨立像就是中国传统雕塑中表现“气”和“韵”的两个范例。前者姿态夸张,气韵贯通,通过挺胸收腹,侧首斜视,右臂后甩,左手执金刚杵,头、躯干和四肢左右扭转的运动变化,刻画了人物武而不鲁、武中蕴文的性格,显示了人物的威武与雄健。后者通过菩萨微侧的头部,左转的上身,轻扭的腰胯和缭绕双臂长垂足下的天衣,展现了人物轻柔窈窕的身姿和妩媚婉丽的风韵,堪称中国古代雕塑的精品。
追溯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断定音乐和雕塑哪一个先出现显然不现实,但两者都起源于对自然物象的模仿却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雕塑领域,除了百年来西方抽象主义中的部分纯粹以几何形组合的雕塑作品,几乎所有古今中外的雕塑都源自于对物象形态的模仿。
模仿,是人的天性,只不过音乐模仿大自然中的声音,雕塑模仿大自然中的物象而已。中国古代雕塑中有大量模仿动物、人物、器物和自然景物的雕塑,如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距今已有7000年之久的陶塑猪,虽然尺寸才6厘米左右,但那短小的四肢、下垂的腹部、耸肩伸背好似正在觅食的样子却表现得惟妙惟肖,十分可爱。牛河梁红山文化中著名“女神庙”出土的女神全身像残留头部,也是一件明显模仿真实人物的塑像,圆润丰满的面部,陡直的额头,上挑的眼梢,尖圆的下颌,外咧的嘴唇,以及低鼻梁、浅眼窝等诸多细节都显示了对真实人物结构的理解。
雕塑如此,音乐也不例外。从古曲《高山流水》对自然山水的模仿到现代唢呐独奏曲《百鸟朝凤》和二胡独奏曲《赛马》对百鸟争鸣、蒙古赛马会万马奔腾景象的描摹,都可以聆听到对大千世界声音和形象的模拟。据《列子·汤问》记载:伯牙善弹琴,钟子期善听琴。一次,伯牙弹了一首高山屹立、气势雄伟的乐曲,钟子期赞赏地说:“巍巍乎志在高山。”伯牙又弹了一首惊涛骇浪、汹涌澎湃的曲子,钟子期又说:“洋洋乎志在流水。”钟子期对音乐内涵的深刻领悟不仅使两人结为知音,也被传为千古佳话。这首模仿自然山水景色的名曲不仅流传至今,还在1977年8月22日被录入到美国太空探测器的金唱片中,发射到太空,代表人类到茫茫的宇宙中寻找“知音”去了。
关于模仿说,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柏拉图就在他的《法律篇》中说过:音乐“(模仿)善或恶的灵魂”②,亚里士多德发挥了柏拉图的思想,进一步说道:“音乐的节奏和旋律反映了性格的真相——愤怒与和顺的形象,勇毅和节制的形象以及一切和这些相反的形象,其他种种性格或情操的形象——这些形象在音乐中表现得最为逼真③”。可以说,这种由古希腊哲学家奠定的模仿说不仅主导了西方艺术两千多年,至今仍然是雕塑创作的重要手段。
关于对艺术理论的探讨,中国古代雕塑不仅与西方无法比拟,与中国古代音乐在理论上做出的探讨成果相比也显得极其匮乏,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两者在礼乐文化中作用的不同。这种不同既形成了音乐与雕塑自身发展和相互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影响了中国古代雕塑对审美的自觉和对本体的深入探索。
在中国,音乐的诞生比《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的“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④早得多,可以上溯到“人猿相揖别”的洪荒时期。那时的音乐还像《尚书·尧典》记载的那样:“击石拊石,百兽率舞”⑤,只是用来配合舞蹈,模仿动物声像,达到“通神”、祭祀或祈求丰收的目的。这也是古代音乐创作的第一个时期——图腾作乐时期。到了《诗经》时代,乐一分为三,变为“风”“雅”“颂”。“颂”为帝王所作,“雅”为官员所作,“风”为民间所作,音乐从图腾作乐转化到了第二个时期帝王作乐和第三个时期民间作乐,神性经帝性转换到了理性,将音乐从人神以和经由乐以调风转变到了帝王享乐,彻底改变了音乐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