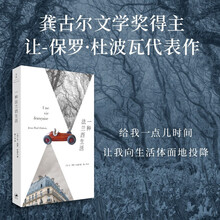木头大,怎么办?这是唯一的办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把人往死了逼,逼急了,逼疯了,逼着去拼死命。剩下的4个人,真没有抬不动的,抬不起来就别在山上混了,别说抬小杠,就是当尿壶都没人愿意滋。
老爷子后脖颈上有个拳头大、很硬很硬的肉包,叫“血蘑菇”。成手木把的后颈都有那样一个“血蘑菇”。总挑担的,比如,挑水挑粪或挑菜上市的农民,挑担四处游走的锡匠、货郎,后颈都不长“血蘑菇”。只有在木把身上,只有很重很重的力量在肩上压、在肉上碾,碾破皮肉,再长,刚封上口,再碾,连血带肉一层层地长,才成了“血蘑菇”。据说,“血蘑菇”不会烂,木把死了,肉烂了,骨头烂了,“血蘑菇”也不会烂。老爷子也是放排好手,他有个绰号叫“刘大瓦杠”。把木排从河里放到江里,再放到城里,要经过十几道哨子。哨子就是水急弯险的地方。哨子过不好会出大事。木排撞到石壁,插立起来,后面的木排又蹿上去,戳大堆,木排散了还在其次,赶排的人轧在乱木当中,死了连个影都找不着。
哪年都有出事的,常听说哪个哪个放排的死了。拆解乱木叫挑垛子,能挑垛子的没几个,老爷子是数得上的一员。
出名的哨子,像恶风口,弯险流急不说,两边立陡的砬子,像铡刀,江狗子每年放排前都要到恶风口的庙里烧香许愿,那也没少出事。像鞅子哨那样的地方就多了,鞅子哨是说那里的弯像牛鞅子,弯急弯硬,一长趟木排在那里转过来不容易。
老爷子放排多少年,从来没出过大事,让人佩服。老爷子当了大掌柜,年纪也大了,不能再抬小杠、放木排了。可经营木场,还是他在行,现场离不开他。运材归不了楞、摊煎饼了,放木排穿箭子、扎堆了,他还得挺身出来。
我在干公差,你叔叔在读书,我们两个都对他不放心。后来想了个办法,请你小舅爷,就是我老舅,老爷子最得意他,请他上山帮着管事。咱家又在四方街开个大车店,捎带开个杂货店,这一摊子事也要有个当家的,顺着就把老爷子从山上撤下来了。
咱家开的大车店在四方街的边上,地场宽敞。
大车店的四周,是用柞木、水曲柳、色木做的栅栏,一色的硬杂木,一丈高,几十年不烂。每年过了春,地化透了,看哪个桩子歪了斜了,扶扶正,重新竖好、扎好,几十丈长的栅栏齐刷刷的。
大车店的房身可不小,3丈宽,10丈长。墙基是用开了方、錾出边的花岗岩砌的,有3尺高。除了侯爷的府第、城里的洋房,四方街的钱庄、当铺,还没有谁用这样好的材料呢。墙基上边是用合抱粗、上好的红松做的木刻楞,层层紧贴,接头咬合,严丝合缝。房顶是用苇草苫的,苫这么大一个房子,雇人割了好大一片苇塘。苇子硬实、不烂、保暖,是苫房草中的极品。苇草苫的房顶,挺括、齐整,太阳光一照亮崭崭的。
大车店的大门是用粗大的圆木做门楼,对开的板门很宽,车辆进出宽宽绰绰,车老板不是出于礼节走着出入院子的话,不用下车也刮不到门柱。门楼的右边挂着一块木匾,上写“悦来大车店”,墨顿顿的颜体字,谁见了都忍不住夸一句,这字,有劲儿。
进了大车店,各个房间是一通到底,一进是账房、柜台、前厅,我和老爷子总待在这里;二进是饭堂,能摆8张桌;三进是灶房,总是叮叮当当乌烟瘴气的;四进是对面大炕,炕角一排行李卷,很长,能睡30多人;五进是用木板隔出来的单间。
从前厅到火炕间穿出来,有个杂货店,两开间,泥草房。据说墙是用木杆子钉好框子,中间填泥母猪。泥母猪就是把洋草滚上稀黄泥,圆圆滚滚,3尺长一个,又黏又沉,两三个小伙子才能叉起来。这种墙垒起来不容易,要拆也是没门。杂货铺卖日用百货,也收购山货。
再往前走是马棚,马棚能拴30多头牲口,茅草顶,墙是用花岗岩垒的,石灰灌缝,结实劲儿没得说。
大车店的院子宽敞得很,停20辆大车,磨车也磨得开。就是地面不太平整,牲口蹄子天天刨,车轮子天天碾,再硬的地面也给搅翻了,一到下雨天泥泞吧叽的。
建大车店,什么都按百年大计打算,做得结结实实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