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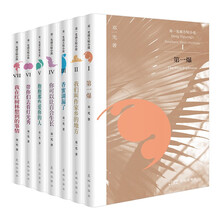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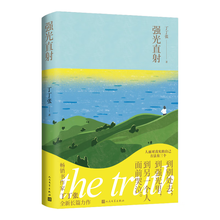




莫言、池莉、阎连科、陈思和、贾平凹一致推崇
“当代文坛刺客”宁肯的经典之作
1980年代一个人的内心生活史
入选“红楼梦文学奖”、“鼎均文学奖”等多项大奖
“建国五十五周年优秀小说奖”、“北京市优秀图书奖”获奖作品
《沉默之门》讲述的是一个人的内心生活史,始于童年,在中年渐获“成熟”。童年时,李慢在废弃的图书馆结识了学识渊博的老人。他帮老人整理图书,在老人的指引下阅读。老人成了他的启蒙者,带他进入了人文的世界,也培养了他沉默内省的性格。他梦想着“永远待在图书馆”,枕着书过完一生,与他人无关,与世界无关。长大后,他失去工作,写过诗却毫无成就,当过推销员却遭受饭馆老板侮辱。恋人神秘失踪,生活破碎,精神崩溃。他与世界格格不入,最终进入了精神病院。康复后,他来到眼镜报社工作,遭到上级轮番侮辱,在尔虞我诈中求生存,不断地受到伤害。李慢沉溺于过去,退回到内心,最终在书法世界中寻得了内心的平静与灵魂的归属。“我愿有一个重重的壳儿,在安静时伸出触角,感知世界,有动静就收起自己,一个内倾的壳,在壳子中实现自我世界,透过壳子仰视天空。”
眼镜报停刊了,我再次失去了工作。不同于十年前,我甚至感到某种程度的愉快,因为从孙老头身上我感到一种喜剧精神。预言家被自己的预言击中,但毕竟拯救了他之所想拯救的,哪怕只是部分。我不会再失魂落魄,到处呼号、叫卖,以至需要白色病院的电击才能安静下来。经过十年努力我练就了自己的手艺,不用再依附什么,这点至关重要。我的字已可以卖钱,虽然暂时还要经过了唐漓之手,但我相信任何人也控制不了我的字的未来,依托我的字我的整个人已多多少少可以站立起来。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我所住过的精神病院竟然再次向我发出邀请,而我自己也竟然匪夷所思地欣然前往。
杜眉医生向我发出了邀请,她希望我到她那儿任教,她这样说就好像她那儿不是精神病院,而是一所学院。当然,认真说起来,它的确具有大学性质,它附属于首都医科大学,正如协和医院附属于协和医科大学一样。杜眉医生让我给她的病人讲授书法,并且如果我答应会配给我一个完全属于我的工作室。我每天授课不超过两个小时,其余都是我的时间。多年前,我离开病院不久,杜眉医生就在病院开设了书画课,书与画成为重要的治疗手段之一。杜眉医生从一开始做院长助理、到副院长、院长,这些年尝试一系列精神治疗养与重建的变革措施,比如病人不必统一着条装,每个病人每天有三种以的上衣着可供选择,亲属不但可以探视,还可以陪住、陪床,可怕的文革时期的水疗遗址改成了花房、游乐室,病人可以健身、游戏、做手工、学习水墨画和书法艺术,定期举办书画展,以及各种才艺比赛。现在诺大的院区事实上已成为一个具有理性精神的几何形条状的大花园,中国书法与欧洲园林式的结合不仅让病人置身于灵性与理性世界,甚至一些从未见过的野生动物也前来做客,出现了多少年未见的鸟类。杜眉医生说现在病人每天早晨不是再听着哨音起床,而是听着各种鸟叫起床,有的病人早晨起来竟能分辨出七种鸟的鸣叫。我觉得七种并不算多,我记得我在时也不下七种,我至少听到过九种鸟叫。病院的野生环境一向不错,仅从鸟叫来判断,我告诉杜眉医生她几乎无成绩可言,不仅如此,甚至有所倒退。杜眉医生笑弯了腰,说过去我听到的九种鸟是病态,现在七种鸟才是正常。作为病人,七种鸟与九种鸟有什么区别呢?我问杜眉医生。另外,不能说鸟越多越不正常,越少反而越正常吧?你这是什么逻辑?杜眉医生说我,你有这样批判能力真是我的杰出的病人,我都快让你搞糊涂了,到底我是对的还是错的?
工作室落成那天,故地重游,感叹连连,杜眉医生几乎把病院当成了私有财产,一切都建设得精致规整,很多地方已完全不认识,以至整体上好像完全是另一时空,是我从未到过的地方。我必须努力寻找才能找到记忆中一些地方,比如某一棵树,某一处墙壁。我几乎有些怀念过去,觉得“今不如昔”,反倒怀念过去医院那种阴暗可怕的地方。杜眉医生说我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的,当然了,这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但在精神的本质上它是有道理的,我对杜眉医生说。这里不像医院,而像社区,花园,人类宜居之地。杜眉医生创造了小环境、理想国,甚至把艺术家也招了来。杜眉医生是一个职业医生,甚至纯粹技术化的医生,这点我在入院期间就体现出来,现在更加充分。以至我觉得多少有些过分,因为我不知道病人离开后还能不能适应社会,比如就像眼镜报那样的社会?你都适应了,还有谁不能适应?杜眉医生说。可我适应得多么不容易,我说,况且之前我还有李大头,还有许多恶,比如电击,有这些垫底我才适应了,我到了眼镜报没觉得自己是出院,只是比过去更加严酷。这又是个悖论,杜眉医生说,精神病学解决不了哲学问题,我不能人为设置恶,以适应恶,这和一个医生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驰。我只能把我的事情做好,做到最好,外面的世界我管不了,也不归我管,我只是个医生,做我所能做的。我这样说主要是让你知道你做的不是绝对正确的,任何理想都是只是一种精神而不是一种律令。你这个意思以前就说过,我印象深刻,所以我并没理直气壮。适度的怀疑自己会让自己平和。你不该仅仅是写字。当然,慢慢来吧,在这儿我确实有了某种冲动。
凭吊水疗遗址让我“伤感“,这儿改建得太漂亮,基本由玻璃构成,完全可以透视病人在里面活动,大家都是可视的,快乐互相传染,有人竟在写字。这里曾是李大头的陵园,梦想的宫殿,蟋蟀的王国,现在成了公民乐园。这当然非常好,简直让我感动,我多年没流泪了,这会儿想流。他们不用老师,我对杜眉医生说病人其实天生会写字,你看他们写得多好。可是你知道病人同时需要权威,杜眉医生说,权威往往是他们的镇静剂、心灵的工程师,老师是权威的一种。是呵,我说,你说得很对,那时我心里是多么盼望着救星。书写是一方面,杜眉医生说,有老师指导是另一方面,它们都对精神的重建有重要帮助。我怕我不象权威,我说。像,头发都这么少了还不象,杜眉医生笑。
杜眉医生也拿我稀少的的头发玩笑,不过极少,且非常温和。
离开“水疗遗址”,终于看到我熟悉的地方病院围墙以及围墙的一孔黑木质的沧海的角门。看到角门不由得想起刚才走的路就是当年走的路,就是当年谈论李大头的路,而现在我们又在谈论。
角门没变,就像围墙没变一样,而出了角门,我一下呆住了,一切好像回到了从前。阳光如注,干河无水,大墙之下,角门洞开,墙里墙外,两个世界。
你没有改变墙外,我说。
干嘛要改变?这样多好。
还记得那群羊吗?
当然。杜眉医生望着远处。
远处,白色羊群静卧在一处干涸的河洲上,一动不动,形态各异,高高低低,不像生命,像一组雪的浮雕,风吹它们不动,云走它们不动,不是绵羊,是那种有角的山羊,没有牧羊人,没有水源,它们寂静得简直恐怖,不像是真的羊。?
牧羊人躺在羊群之中,是个老人,或许不太老,戴着草帽。忽然站起来,并没高出多少羊群。羊群缓慢地走下河洲,老人走在中间,老人如此孤独的睡眠之后,又是如此孤独的行走,与世界无关,与天地无关。
那群羊呢?我问杜眉医生。
有时还在,杜眉医生说。
今天怎么没有?
比以前少了。
我们养一大群羊吧,杜眉?
杜眉医生笑。我们再次给各自拍了照片。
还用自拍并合了影,就像当年一样。照片放大后做了金属框放在了我的工作室正面墙上。我很满意我的工作室,完全是书和字的世界,诗意地栖居。
二○○二年,我四十岁,杜眉医生四十二岁,我们结了婚。
杜眉医生是院长、教授、博导,我们共同完成了一本精神学专著。见到了老社长,对我非常满意,帕金森综合症使老人看上去非常幸福,整天笑,鹤发童颜,目光如炬,喝葡萄酒,并不知道我是谁。
……
第一部 长街
第二部 唐漓
第三部 医生
第四部 南城
第五部 幸福
宁肯,一个天生的作家,一个文学书写疾患者。池莉(著名作家)
我喜欢这部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宁肯写出了我们这一代人亲身感受过的许多隐秘经历。陈思和(复旦大学教授)
宁肯是横路杀出的程咬金。他写的小说有自己鲜明的印记,是当代小说的刺客。陈晓明(北京大学教授)
《蒙面之城》写了三年,《沉默之门》也写了三年。三年中,他数易其稿。一次我们谈起这部小说的写作,他形象地说:“像熬中药,慢慢儿熬出来的。” 解玺璋(知名评论家,《梁启超传》作者)
如果说这不是一本完美的书,它绝对是一本奇特的书。《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