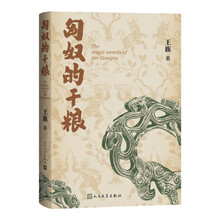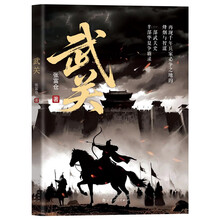“三爷,老臣的心有点没底!”骑在一匹黑马上,身穿紫色纱袍的大干户亦鲁格,取下凉帽扇了两下。他黄面皮刀条脸,一字眉,雄凤眼,年过六旬,胡须已经花白。他因最小的女儿嫁给了窝阔台的三子阔出,被窝阔台尊为“亲家”。他将黑马贴近“五花骢”,眉头拧着,忧心忡忡地道,“王爷未出霍搏,四爷使节不断,说得甜言蜜语。臣以为一路必安排得妥妥帖帖,现在行程过半,却连个兔大人影都不见,这不符合常理呀?”
纵马跟随的大千户田镇海,八字眉下一双鹤眼,下巴上留着棕褐色大胡子。叹了口气,说道:“四爷对三爷入主汗廷,一直置若罔闻,突然来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变。如此前倨后恭,这潭水不浅呀。咱们出了大本营,真的中了伏兵,五百人能管什么用?”
亦鲁格被田镇海说得浑身发冷,懊丧地道:“看来是老夫有点大意,目前是得想个办法补救一下。”
两位大幕僚的话,说得窝阔台心情沉重起来,他那张线条分明的脸上显现出一种令人很难察觉的困惑。窝阔台不愿在下属面前暴露忧思,颔首笑道:“你们多心了吧!本王听说老四拖雷在向欧洲罗马传教士发的帖子说,在蒙古汗国土地上,哪怕是一个孩子赶着数十辆勒勒车,车上拉满黄金,也不会有人动抢劫的念头。现在本王可带着五百精兵,难道还会路碰劫匪吗?”
田镇海红着脸,争辩道:“三爷的话,卑职不敢说错!可事涉大位,父子相残,兄弟变脸的历朝历代都有。远的不说,唐有玄武门之变,后周有陈桥兵变,辽有诸弟之变。况且先帝在世时,四爷就有争位之心呀!”
窝阔台长吁一声道:“先帝留有遗诏,老四是改变不了的。”
亦鲁格苦着脸道:“三爷,老臣觉得情况不太妙,得坐下来商量一下。”
窝阔台望着亦鲁格点了点头,说道:“一会打尖时再议,我觉得形势还没有你们想得那样坏。”
亦鲁格勒住黑马,对身边的传令兵吩咐道:“快,传三王爷旨意,告诉巴特尔千户,前面密林处宿营。”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在窝阔台指定宿营的那片山林,一棵长在崖壁上的大松树格外高大,一位古铜面、长胡子的将军攀上大松树粗壮的虬干,透过叶隙目不转睛地向谷底张望。当他望见谷底一团黄尘由远及近腾起时,脸上立即现出一种得意的窃笑……
随着马队蹄声冰雹般进入埋伏圈,长胡子在树上缓慢地举起令旗∞。牛角号呜呜呜吹响,一场围猎开始了,急雨般的箭镞,从两面山梁上一齐向谷底倾泻。伏兵全线出击,喊杀声响彻山谷……
冲在最前面的巴特尔千户胸甲被利箭穿透,他的脚没有脱出马镫,尸体就栽于马下。遭遇迅雷般打击的前锋卫队纷纷落马,如被飓风掠过的庄稼地,人尸、马尸塞道。转眼工夫,鲜血浸透了狭长的山谷……在一片较宽阔的谷地间,王纛落地。高个子掌旗官心口射人一支箭镞,当死亡之光笼罩他的躯体时,大纛还紧握在他的手上。
仓促间,窝阔台紧勒马嚼,五花骢嘴里喷着粗气,前蹄踏向空中。头脑一片空白的窝阔台足踏银镫,悲愤地仰天大叫:“长生天呀,回答我,是谁对我下的毒手呀?”
窝阔台的喊声,像在质问苍天,又像在询问青山,而回答他的只有两侧山头摇动的旗帜、擂动的鼙鼓和震耳欲聋地喊杀声。
田镇海策马贴近他,指着山头愤怒地喊道:“三爷,旗帜、横幅,分明是有人在瞒天过海,欲盖弥彰!”
伏兵似乎并未掩饰他们的身份,牙旗上绘着白狼的族徽。树间白绸子扯起横幅,用朱砂大字写着:“父债子偿,上天至公”,横幅边上一行小字:“撒卜刺汗”。
窝阔台将目光收回,对围拢过来的亲军喊道:“不要慌乱!”
突然到来的袭击,让亦鲁格懊悔无地,他眼里喷火,大声喊道:“二十五年前,此地的乃蛮国,为铁木真大汗带兵所灭。乃蛮太阳汗有两个儿子,长子曲出律逃到西辽,被哲别将军诛杀了;幼子叫撒h剌汗,逃进阿尔泰山之后就如投进草丛的石头,没了音讯。”
一个亲军望着窝阔台说:“三王爷,是乃蛮人兴兵造反了?”
“他们的刀,咱们就没有刀吗!”窝阔台恢复了自信,刚毅的目光掠过卫队勇士的面庞,高亢地鼓动道,“伴当们——长生天在上,愿做羔羊的去死吧,愿为猛虎的,随本王杀上山去——”
“奴才誓死追随王爷!”亲军愤怒地吼叫着。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