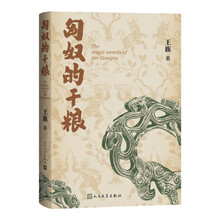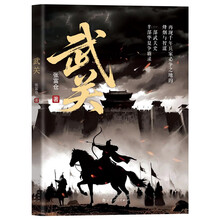山坡上散落着一些小地块,像一块块补丁,随着地势起伏,把沟沟岔岔缀连起来,地里种的都是些谷子玉茭,庄稼成熟前,庄户们怕雀蹬兔踏,就在地块里立一个“看谷老汉”,其实就是扎个架子,顶个烂草帽,披件破褂子,吊个破扇子,有个人样就成了。现在谷穗掐了,玉茭穗掰了,“看谷老汉”也没用了,剩在地里东倒西歪,山风吹来,枯叶摩擦出声,“看谷老汉”摇晃婆娑,老远看去,就有六七份人味儿。
有牲口的人家,早早就砍倒秸秆,弄回家里,等天冷下来,铡了喂牲口。也有不少地块,谷草和玉茭棒还黄耷耷长在地里,要等西风慢慢吹干,劈砍起来不费劲,挑担起来也轻省。手懒的人家,甚至会让它们一直长在地头,成了石鸡野兔田鼠跑马存身的场所,也给漫长的冬日预备下苦寒的山景,经历了风吹霜打雪压以后,它们就像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饥殍,倒伏一地。
下地回来的农民,远远看见骑着胭脂马的黑川,早早把担杖镰刀搁地下,垂手低头,立在路边,把路让开,等黑川他们过去,然后才能挑担上东西再走。
走到圪针沟时,黑川的胭脂马不安地偏转马头,四蹄“嗒嗒”踏着乱步,使劲往后退,好像前头有什么怪物挡道,黑川将马嚼的皮绳用力往怀里勒,胭脂马四蹄刨地,摇头摆尾,喉咙里“咴咴”,打着响鼻,不肯安稳。
黑川朝坡底望去,看见一个人弯腰割草,和“看谷老汉”一样,戴了一顶霉黑了的草帽,只顾低头忙活,好像没有听见人马过来,黑川和护兵俩人都看见那个割草人了,就在他们眼皮底下,他们没介意。
黑川控住马头,催马前进,和护兵走出十几步,几乎同时听见后边有响动,黑川刚转回半个身,就见护兵正往地下倒,脖子里喷出一股血雾。黑川伸手去摸佩枪,手还没有到,就被人从洋马上揪下来,倒栽跟头摔到路上,红洋马受惊,往前一蹿,落荒逃逸,来人也不说话,摁住黑川,用煞草的苘麻绳把他从嘴到腿绑扎停当。护兵断开脖颈发出湍急的倒吸气的声音,胳膊腿还在抽搐。来人拣起步枪,熟练地卸掉枪栓和刺刀,抛掷到远处,然后悠开枪托狠狠砸向护兵的头颅,护兵的挣扎随即停止。黑川瞪圆眼珠,他已经认出杀人者,他想叫他的名字,但嘴巴里勒着绳子,他满面流泪,这不是他设计过的末日,他还有许多事情没处理,他恐怖地看着来人转过身,悠开枪托,朝他的脑袋砸下来……
憨水在谷地里虾腰割草,他直起腰杆,往路上瞭望,竟看见一个“看谷老汉”胳肢窝挟着人飞跑,憨水吓了一跳,跟活见了鬼一样,张大嘴,眼瞅着“看谷老汉”顺着圪针沟一直往下,拐转弯。
虽然沟底没了阳光,憨水还是一眼认出“看谷老汉”了,放羊出身的人,眼尖记性好,一坡七八十只披毛顶角的畜生都能分开,莫说是一个人了。憨水觉得好玩儿,打了一个响亮的呼哨,呼哨有回声,憨水看看天色,拎起镰刀,跳下地墙。他饿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