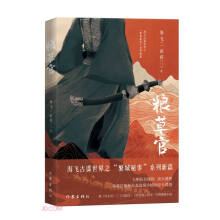黄昏里橘红色的半边天渐渐褪去了色彩,仅剩最后一丝余温的阳光穿过锈迹斑斑的铁窗,给置于古老的实验架上的福尔马林溶液镀上了一层金边。
这是浓度百分之三十七的甲醛水溶液。那块大脑切片静静地悬浮其中,默默等待着世人的遗忘。尽管“他”生前有着旷世惊人的荣耀,此刻却仅仅是被浸在发出浓重刺鼻气味的溶液中,和普通人的大脑切片放到一起,没有人还能像过去那样一眼便认出“他”。但是他太优秀,太接近于完美,没有人愿意就此遗忘他的存在。
因为,他是爱因斯坦。
对于世界上所有的生物学家来说,爱因斯坦的大脑切片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研究对象,而对于致力于大脑研究的华裔科学家张教授来说,得到那颗如核桃纹理般复杂的大脑比得到任何东西都让他兴奋不已。
他的手在发抖。
他慢慢拧开溶液瓶的盖子,强烈的刺鼻气味马上扑了过来。但是他似乎忘了自己还有嗅觉,贪婪的视觉霸占了他所有的神经。
“您好,您好!”连绵不绝的问候和欢迎的声音让他有些眩晕。
回国的客机上,他在阶梯上望着高楼林立的城市,望着似乎触手可及的云朵。
二十年没有回国的他突然辞去了在美国秘密研究中心的所有职务,在国内一个偏远的村落安居了下来。他不会再被其他事打扰,不翼而飞的爱因斯坦的大脑切片也永远不会被公之于众。
五十多岁的他头发早已花白,值得欣慰的是他美丽的妻子在三个月前怀了身孕。他依稀记得年轻时的那次运动会,遗憾的是冠军的桂冠最终并没有戴在他的头上。他曾经梦想过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作为一名生物学家,他也许可以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改变自己的体能。他的嘴角忽然翘起,窗外瑟瑟的风声随之停下,仿佛连风也在惧怕着他魔鬼般的实验蓝图。
怀孕第三个月。
爱丽丝抚着自己的肚子,脸上洋溢着满意的表情。
张教授摸摸她的头发,将耳朵贴着她的胸脯缓缓向下移动,到了腹部就停了下来。
爱丽丝“噗”一声笑了:“别急,胎动要等到十八到二十周才有呢。”
“我们的宝宝可不是一般人,他是第二个爱因斯坦。”张教授调侃着,重又将耳朵贴在了妻子的肚皮上。
爱丽丝刚要开口,却看见丈夫一脸惊异的表情。他竖起食指,做了一个“嘘”的手势,低声说:“真的有声音。”
爱丽丝平静甜蜜的脸忽然变了色,取而代之的已是一种难以形容、只有人类在死亡时才会出现的表情。张教授承认,他从未见过这种表情在妻子的脸上显现过。
“啊!”爱丽丝嘶喊着,双手紧握,倒在地上,蜷曲着身体来回挣扎着。
这是待产的症状,但是妻子刚怀孕三个月,连预产期都还没到。“难道是……”张教授将手指插入头发里来回游走着,小声嘀咕着,“一定是哪里出了错……一定是……”
“护士,快点!”移动病床的四个轮子飞速转动着,四面围着喘着粗气的医生。
“对不起,先生。”一个体态高瘦,皮肤白皙,看样子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护士拦住了张教授,“您需要回避一下。”
他没有说话,久经风浪的他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而使他夜晚般平静的心生起波澜。“究竟是哪里出了错?”按他的计划,妻子应该怀孕十三个月才可以生产。“也许是那些该死的动物基因在作祟。对,一定是那样。这么有创造性的实验有一点微小的副作用也是难免的。”他安慰着自己。
“不要过来!”披头散发的爱丽丝疯了一样抓咬着一切能够得到的东西。她紧握的双手触到了护士的衣角,像落水时忽然碰到了可以救命的稻草,她猛烈地把护士的一只袖子扯了下来。
“快,快!”几个人一拥而上,终于按住了她。“给她打安定剂!”爱丽丝摇摆的脑袋忽然停了下来,她绝望地望着护士手中残忍的针尖:“不要打,不要。”这几个月以来,她已经被注射了太多她的身体本不该拥有的东西。对于她来说,这个世界上最可怖的已经不是魔鬼,而是药水,是注射器。
“莎莉,快点!”一个年长的老护士急促地催着年轻高挑的小护士。她叫莎莉,张教授在门缝里看着她。他认识她,刚才就是她拦住了他,并且说医院规定,不准家属入内之类的话。
最后几个气泡被莎莉从注射器里推了出去。“可以开始了。”她点头示意。
爱丽丝已经停止了哭闹,平静得像是睡着了一样。她注视着一点点接近的注射器,并计算着它与皮肤的距离。
张教授从门缝向屋里瞟了一眼,突然的安静让他有些意外。那个笨手笨脚的护士应该从业不到两年,他完全有信心说,自己的扎针技术可以超过屋子里的任何人。
他回过头,靠着写着“产房”两个大字的玻璃门点燃了一支烟。
“喔……”一阵奇怪的声音从屋里传了过来,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妻子鼓鼓的肚子,“应该不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莎莉走过去拿消毒药棉,正好挡住了张教授的视线。
“啊!”一声尖叫和几个不同的声音几乎同时响了起来。张教授猛地回头一看,“产房”两个血红的大字已经不见了,真正的血遮挡了它们的存在。
黏稠的血液附着在门的每一块玻璃上,仿佛在隔绝着门内外两个世界。
他看不见,他不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爱丽丝!”他喊了一声,刚要撞门进去,却被破门而出的医生撞了个踉跄。浑身滴着鲜血的医务人员疯了一样嘶喊着四处逃窜。
他怔在门口,他的实验失败了。
爱丽丝安静地躺在产床上,蓬乱的头发下,死鱼般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她再也不用惧怕什么了。
从屋顶上看,她的产床完全成了一件别致的艺术品。
是一朵巨大的红色花朵。
红色的花瓣遍及屋子里的每个角落,而花心的部分,爬起一个浑身是血的新生命。第一次呼吸到空气的它不知道自己奋力撕裂的并不是蛋壳,而是母亲孕育了它三个月的肚子。
它红白相间的大脑裸露在空气里,像是刚剥好的核桃一样错综复杂。摇摆的尾巴正在甩着身上的血污。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