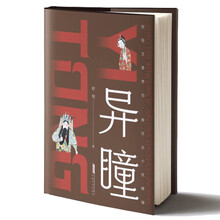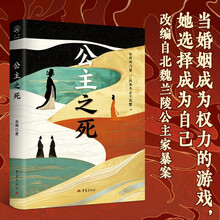三
这位被王金枝用嗲声唤作“老贾”的人,叫贾国志。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是高西店奔东两里地,高碑店的片儿警。高西店,给一东一西的高碑店跟水南庄夹在当间儿,是个三不管的地段。早年间,打高碑店那头搬过来的人渐多;日子一长,这边一有事,人就爱奔贾国志待的派出所跑。
贾国志比王金枝大十岁。初中毕业去内蒙当了兵。当的是炮兵。那阵子,中苏关系特别吃紧。贾国志在的炮兵团,一级战备了好几个月:枪不离手;衣不解带。各连队都加班加点地训练。
有回,紧急演习,贾国志给七十毫米无坐力火炮的后架子,砸碎了左踝骨。在部队医院,一躺就是俩月。岁数小,人恢复得快;岁数小,犯纪律犯得也快。回营刚不几天就跟个卫生兵,营里头唯一的女兵好上了。
那会儿,贾国志的伤还没好利落,教导员派他刻蜡板。北京兵,有才。教导员让他把“最高指示”油印成红的绿的传单,发到各个连队去。贾国志一瘸一拐地在营房里乱窜,时不常撞见小刘护士。他俩一般大。小刘护士叫刘爱华。内蒙赤峰人。农村孩子,从脸到身子,哪哪儿都圆鼓鼓的。一双大眼睛,特别透亮。
话说女兵有女兵的装束,衣裳都带掐腰。穿上去,既贴身,还好看。刘爱华的胸又大又挺实。一不小心,总把上衣扣子撑开。不开,平时也咧着个口。贾国志每回撞见她,都拿胳膊肘奔人那儿顶一下子。沉甸甸的,像铅球。这可不能叫调戏。俩没过二十的孩子,纯属调皮捣蛋,耍着解闷儿。如果旁边有人,贾国志正好一瘸一拐的,赶到小刘跟前,一歪,还是顶个正着。俩人都憋着不乐。这么耍着耍着,工夫一长,想法就多了。胆子也大了。
犯纪律那天晚上,贾国志跟小刘护士约好喽,还在老地方见。他俩都当教导员出去了,没在营房里瞎转悠,就裹着两件军大衣,在一辆黑绿色儿的“大解放”底下鼓捣那事。这不是头一回了。小刘护士滚烫的身子,有股特殊的香味,弄得贾国志神魂颠倒的。那是女兵才有的香胰子味。没等贾国志动手,刘爱华的上衣扣子早就撑开了。
眼瞅着,烈火干柴就要冒烟的节骨眼儿上,“轰隆”一声,教导员开走了他俩脑瓜顶上的“大解放”。空荡荡的操场上,就剩下了他们俩。
四
教导员开出去十来米远,停下。跳下来,戳在车边儿。在黑暗里挥了下手。“刷刷”,两道雪亮的探照灯打在他俩身上。教导员上前走了两步,来在亮处。朝他俩,一个炮兵一个卫生兵,发令:
“三连4班贾国志,立正!”
教导员嗓门儿压得挺低,可在贾国志的耳朵里比炸雷还响。他站在一铺一盖的俩军大衣上,笔管溜直的。教导员:
“向前三步——走!”
贾国志穿着件军绿背心,朝前迈了三步。小腿肚子直转筋。教导员:
“向左——转!”
贾国志穿着军绿大裤衩,侧歪着身子,奔左边转了小半圈儿。刚才,那个火烧火燎的玩意儿,现在缩得不知哪去了。接着,教导员冲刘爱华,发出同样的口令:
“向左——转!”
刘爱华给臊得满脸烧火,铅球也缩成了个泄气的皮球。恨不得搁脑袋扎进裤裆里。
他俩并排站着。脸朝北;朝着五排平房。熄灯号已经吹过了,营房黑压压的。贾国志知道,教导员让他俩朝北站着,不是让冲着营房,是让他俩冲着教导员常念叨的,打营房奔北八百里的外蒙古;冲着打外蒙古再奔北的地方。每回,教导员都斩钉截铁地说:
“那里,就是我们的敌人。”
五
搁往常,贾国志听教导员这么说,打“敌人”这个字眼,会想起小时候一顺口溜儿。
他家住牛王庙。在东直门外。那儿有个厂子,挺大。里头通火车,叫北京造纸厂。贾国志他爹是这厂子的工人。贾国志自小在东直门大街,反修路小学念书。反修路,早先不这么叫,叫友谊路。它是苏联大使馆门口的一条大马路。路两边栽着槐树。槐树上头老是挂着彩色的三角儿旗子。红红绿绿的。惹得贾国志老想去揪,可揪不着。一到年了节了的,花团锦簇的,友谊路立马成了北京顶好看的马路。
等他上小学二年级,这路就改名了。叫反修路了。跟他这么大的孩子都知道:赫鲁晓夫那孙子,骂咱毛主席是双又老又破的鞋,该扔了。毛主席没法儿不跟丫翻脸!上二年级的贾国志这么想。打这儿起,这条路上没了彩色的三角儿旗子。这条路变得灰暗了。
贾国志跟几个同学,摽着膀子,放学奔家走。每回,离苏联大使馆门口老远,就一步一蹿地一块儿大喊那顺口溜儿:
“苏修老浑蛋,睁眼看一看,中国人民不好惹,打你丫个稀巴烂!”
倒不一定每回都来这么有政治性觉悟的。时不常也换换花样。你比方:
“傻逼青年过马路,稀屎拉一裤,捡块糖纸擦屁股,越擦越黏糊!”
这种,一般都是两拨子对骂。挨骂的那头,一准儿拿出玩儿得更“猖”的架势。不等你这头话音落地,立马不忿儿地回骂。先一人起头:
“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大伙儿铆足了劲:
“你妈屁股擦油漆!”
他们越到苏联大使馆门口,喊得声越大。脚也蹿得越高。
有一回,贾国志真瞅见一位“苏修老浑蛋”,正搁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车里钻出来。身穿黑色猎装。结实的身量儿,活脱儿一个《列宁在十月》①里的瓦西里②。那可是他心里头的偶像。那人朝他们这边瞅了一眼;嘴角上挂着微笑。努了努翘着的小胡子,好像要跟这帮小子说那句台词了。太有名了,贾国志记得烂熟。
“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上二年级的贾国志,突然跟瓦西里的目光碰在了一块。顿时,他放低了嗓门儿。定格在那儿,一动不动。身不由己地目送人家进了大门,消失在黑暗的门洞子里。老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撒丫子,跑了。
教导员早走了,什么都没说。他一走,探照灯也灭了。
贾国志跟刘爱华站在寒风习习的大操场上,他想起了这些个顺口溜儿。快八月十五了。月亮挺亮。对过儿营房,挨个窗户垛子上都写着个大字。连起来念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他俩对着这十六个大字,哆哆嗦嗦地站了一宿。他俩一般大,那年十六。贾国志的耳朵里老吵吵着那些个顺口溜儿。他确实挺想回家了。
六
三天后,他俩都背了个记过处分。上头掂量这俩岁数忒小,没给开除。一块儿提前复员了。炮兵团,在他俩走了的第二天接到紧急命令,连夜开往中蒙边境了。
转过年来,一九六九年三月的一个晚上,北京下起了大雪,纷纷扬扬的。挺冷。暖气烧得热腾腾的,烤得人嗓子眼儿发干,睡不着觉。贾国志打报纸上瞧见,中苏在珍宝岛③爆发了军事冲突。他打床上一骨碌坐起来:
“我操!真鸡巴打起来了!”
兴奋,来劲,得意,美。贾国志就跟过年似的。也难怪,这么大个事,怎么就给这十七八的,才当了八个月的兵,还背着个处分的半大小子蒙着了?话说几个月前,他没日没夜地刻蜡板那会儿,在教导员给的材料堆里,贾国志不光闻着股火药味,还大概其猜对了打仗的地方:万不能是营房正北;该是奔东边的中苏边境。据说那儿有条河。广播电台成天放的“乌苏里船歌”,唱的就是那地方。那河叫乌苏里江?没错!珍宝岛,就在那条江上。远看,那小岛是月牙形的。岛这头是咱们;对过儿就是苏联。那一宿,贾国志琢磨完珍宝岛,又嘀咕歌词里唱的赫哲族④人。满脑子都是些茹毛饮血的生番。打头的那句歌词,怎么唱来着?
“阿拉拉赫尼拉……”你说挺各色吧,还真不难听。您说,这算是哪国话呢?
珍宝岛之战,成了贾国志一辈子最爱捣鼓的事。真不知道他打哪儿敛巴来那么些个珍宝岛的烂纸片,简直能撮成堆儿了。嘎七马八的。长的,扁的,黄的,油的,沾菜汤的,揉巴烂的。这事,能让他絮叨三天三夜。珍宝岛事件,当真给了他不少寄托,大了说,能算一笔精神财富。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