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郑长乐从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离婚。
从街道办事处的旧楼出来,他重一脚轻一脚,有些恍惚。外面的热浪波涛般涌来,他躲在屋檐下的阴凉处,望了一眼外面惨白的天空,就感觉身体冒烟了。这是一片旧城区,临街的房屋破旧低矮,安上空调后,散热器都架在马路边上,轰隆隆地朝外排放热气。天在烧,地在烤,内心在煎熬。郑长乐感觉自己快变成一缕轻烟,被骄阳蒸发。
廖艳从后面跟上来,因为穿了双恨天高凉鞋,走路一摇一摆,像跳脚尖舞,见郑长乐在门口踌躇,以为是等她,眼睛一亮,就快步上前:“老公,要不……我们一起去喝点什么?然后再一起吃顿晚饭,算我们的最后晚餐,好不好?”
“婚都离了,不要再乱喊!”郑长乐眉头一皱,满脸厌烦。
这离婚手续也太简单了,简单得让郑长乐很失落。他准备了一堆堂皇的理由,比如说性格不合,要给廖艳留些面子。结果呢,人家根本不问。红本本缴上去,绿本本领回来,五分钟不到就解决问题。这时代真是现代化了,什么都追求高效率。只是,十八年的婚姻,也曾经温馨幸福的家,就这么眨眼之间灰飞烟灭,让郑长乐实在有些恍惚。十八年呀,从青春到中年。自欺也好,欺人也罢,欢乐痛苦,层层叠叠加起来,毕竟是一段厚重的岁月,就这样轻飘飘一笔勾销?郑长乐头重脚轻,恍然如梦。
廖艳见他踌躇不语,还以为他心痛钱。她太了解他了,一贯节俭,就豪气道:“那算我请你,好不好?天这么热,我们去那边的水吧坐坐,歇一会儿凉。那里有空调,环境不错。你不晓得,现在的年轻人才会享受哟,哪像我们年轻那阵,你一支四分钱的香蕉冰糕就把我打发了。现在耍朋友兴讲情调,喝啥子‘钟爱一生’,‘月亮代表我的心’,没听说过吧?名字都取得嘿(很)好听,其实就是当年的清凉饮料,只不过加了些花哨的颜色。走吧走吧,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我们也去学回年轻人,浪漫一把。对了,我请你喝一杯‘激情岁月’,保证你喜欢。”
郑长乐白她一眼,厌烦中却又有些好奇:“啥子‘激情岁月’哟,我听都没听说过,啷个会喜欢?”
廖艳神秘一笑,暗暗得意。她是与时俱进了,趁郑长乐上班,悄悄跟人溜出来潇洒。泡水吧,逛迪厅夜总会,洗脚泡澡,享受生活。郑长乐还是老一套,每天只晓得上班下班,买菜做饭,最多周末跟兄弟伙搓两圈麻将,喝杯啤酒,完全还生活在上个世纪,简直就是个土包子,也可怜。不过她不想刺激他,就装出一脸不以为然:“咳,就是过去八分钱一杯的酸梅汤,你不是最爱喝吗?现在换个名字叫‘激情岁月’,卖八块钱一杯了,说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是生活的味道,是岁月的味道。说你落伍跟不上形势吧,你还不承认。走走走,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我请客,带你去开个洋荤,也时髦一回。”说完就上前要挽他的手。
这个女人,昨天还哭哭啼啼,求他不要离婚,说要痛改前非,要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可今天真离了,她竟屁事没得,甚至还有点欢天喜地。真是没心没肺啊。郑长乐胳膊一抖,甩开她,说:“傍大款了?有钱学会玩洋格了?”
廖艳收起笑意,顿时又一脸楚楚可怜:“老公,人活一世不容易,能快乐一天,就享受一天。就算我跟你赔礼道歉,还不行吗?”说完身子一软,又贴上来了。
郑长乐突然烦了,觉得她真是不要脸。一把推开她,掏出刚领的离婚证说:“你看清楚了,这是啥子?国家法律,打脱离。啥叫打脱离你懂噻?不懂我再跟你解释一遍,就是从今天起,我们两个断绝关系。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是井水,你是河水,我们互不侵犯,懂了噻?所以请你放尊重点,不要再跟我拉拉扯扯,乱喊老公。我不是你老公,也担当不起!”
廖艳立即眼睛红了,嘴一嘟,也有些愤愤道:“那只是你的说法!要我说呢,你是小龙的爸,我是小龙的妈。只要小龙还在,我们两个就脱不了关系,一辈子都断绝不了,除非哪天小龙死了。”
郑长乐一听,火冒三丈:“啥子呢,你咒小龙死?咒我们郑家断子绝孙?”他一生气就瞪眼,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郑家就这一根独苗,她居然这样咒人,太歹毒了。
廖艳慌了,她最怕郑长乐这种眼神,凶神恶煞,能把人恨出一个洞来,何况她并没有那意思,却百嘴难辩,急得满地打转,跺脚赌咒:“哎呀!天打五雷轰的,我哪里是那个意思嘛?我不过想说,打断骨头还连着筋。不管离婚不离婚,我们都永远是小龙的父母。人家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们都做了十八年夫妻……”
廖艳心一酸,眼一眨,长长密密的睫毛下,竟滚出长串泪珠来。“小龙是你们郑家的独苗,难道不是我廖艳的独苗?当妈的再是罪该万死,也还不至于咒自己身上落下来的肉吧?”
“哼,你还好意思说这些?”郑长乐最恨她说一套做一套,“你心里要还有这十八年婚姻,还有小龙这个儿子,就不会干出那些丢人现眼的丑事来!”说完咬牙切齿,用离婚证狠狠去戳她的脸,“我怀疑你这里长的不是脸,是城墙拐拐!”
廖艳一个踉跄,后退几步,呜呜咽咽得更伤心了。郑长乐转过身去,不想看她。受伤的是他,该哭的是他,她倒抢先一步,先演起戏来。身旁有行人停下脚步,朝他们张望。郑长乐觉得很没面子,就抬头望天。是下午的光景,天空惨白,像火焰深处的那团白光,看一眼就眼发花,心发毛,感觉身体也着火了。郑长乐努力让自己不燃烧起来,就压低嗓音:“算了,廖艳,别的我也不想多说,说多了伤心,也伤身。一句话,我们夫妻缘分尽了。从今以后,你就好自为之吧。”
他说完一抬腿,一脚踩进阳光里,走了。
郑长乐是典型的重庆男人,身材不高,却干精火旺。即使三天不吃不喝,也精神抖擞,脚步铿锵。太阳火辣辣的,身上的T恤衫成了刚刚出锅的烙饼,软塌塌地贴着他烫。他仿佛听见身体被炙烤得“吱吱”冒油的声音,索性抬起头来,迎着太阳,自嘲道:“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困难?我郑长乐,死都不怕,还怕离婚?!笑话!”
廖艳目送郑长乐渐行渐远,一跺脚,丢下一句:“哼,敬酒不吃吃罚酒!郑长乐,你个茅厕头的石头,又臭又硬!”一扭一扭,也走了。昨天她哭哭啼啼,不想离婚,是真的。今天真离了,她无所谓,也是真的。她会这么想,都是多年来郑长乐调教的结果。郑长乐常说:“塞翁失马,看起来是祸,其实是福。”“天塌下来,大不了扯来当铺盖。”“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由此推来,离婚也不只是坏事,因为所有的坏事都有可能变成好事。婚姻的枷锁失去了,换回的,是爱的自由。她才三十八岁,不算太老,喜欢她的男人还有几个。离了婚正好如鱼得水,至少还可以在老男人的湖里去畅游几年。她有时恨自己生不逢时,如果能晚生十年八年,她就不仅仅在湖里游了,她得去畅游大海,人生一定比现在精彩。
穿街过巷,郑长乐毫无目的一路疾行,不觉竟来到一段旧城墙上。再往下就是嘉陵江了。夏天的嘉陵江,没有了春天的碧蓝如带,却也温温婉婉,像个羞涩的旧式女人去赴约会。那长江大河一路由西咆哮而来,经过了千里万里的追寻,似乎早已迫不及待,一过朝天门,就将恋人揽裹入怀。你如果见过这两江相遇时的激情澎湃;见过它们交合时的沉醉忘情,狂欢舞蹈;见过它们义无反顾难分难舍,滚滚东去,你就知道江河的爱情,比人类的爱情更久远坚贞。那才是真正的不离不弃,永不分离。郑长乐站在旧城墙上的黄葛树下,望着前方起伏的山峦,奔涌的江河,人就有些发呆了。他半眯着眼睛,任目光抚过远处的山峦,对岸的楼宇,最后疲惫地落在江边戏水的孩童身上。这情景既熟悉又陌生,让他感到隐隐的酸涩。山城是著名的“火炉”。小时候,哪家临江而居的男孩子,没有偷偷溜下河,去享受烈日下江水的清凉?那种光着屁股,纵身跃入水中的舒畅,恍若昨日,而他已经人到中年,连儿子都早过了戏水的年龄。人生真是如梦啊,梦醒之后一场空。郑长乐心里一悲,想哭。
沿城墙是一溜低矮破旧的居民房,被骄阳烤晒得无精打采,东倒西歪。一对老夫妻躺在路边的竹椅上乘凉,懒洋洋地沉默无言。与江对面渝中区的热闹繁华比起来,这里像一个被时光遗忘的角落。如果从天空俯视,你一定会惊诧这一江之隔的城市两岸,居然有这样大的不同。就像时间的两只脚,一只已踏进21世纪,另一只还停留在20世纪。江那边的渝中区是一张彩色照片,色彩浓烈,线条清晰,亮晶晶新崭崭透着华丽的现代气息;江这边的江北城呢,却是泛黄的黑白照片,影像模糊,色彩暗淡,是一段衰败的旧时光。
郑长乐的家,就在这段旧时光里。那是单位几年前分的集资房,就在后面不远的半坡上,一室一厅,不大,但他已经知足了,好歹算是自己的窝。现在这里却成了伤心地。一想到刚刚经历的离婚手续,前后不到五分钟,近二十年的婚姻就解体了。人散了,家没了,他就又一次感到了痛。黄葛树上的金阿子一声比一声叫得凄厉,像钝刀割人,割得他的心一颤,又一颤。他点上烟,深深吸了一口,再仰头狠狠吐出来,看着软绵绵的烟圈在空中挣扎着散去,脸上便有了一种英雄的壮烈。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呃呃呃……”
嗓子里突然自己就冒出这歌来,同时身体也站出相应的姿式,就像当年舞台上的那个英雄。郑长乐生于20世纪50年代,青年时代喜欢的那些歌,早已血液一样融于生命,成了他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挺然屹立傲苍穹。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烈日喷炎晒不死,严寒冰雪郁郁葱葱……”
他紧闭双眼,摇头晃脑,声情并茂,几乎是一口气将歌唱完,才慢慢睁眼。那歌声像一道光,让他纷乱的思绪渐渐显出清晰的轮廓。他这才缓过神来,无意中发现,那对老夫妻正伸长脖子,一脸惊愕地望着他。他尴尬地笑笑。老人担忧的眼神让他突然想起母亲。他得去看母亲。都说女人受了伤,喜欢回娘家去寻找安慰。其实男人也一样,只是不如女人那样直白而已。母亲老了,已失去了庇护孩子的能力,那就在她身边坐一会儿吧,陪她说说话,重温一段旧时光也好啊。妻子走了,儿子不归。有母亲的地方,仍然是家。
“咳,离了也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天涯何处无芳草。现在这世界,钱不好找,两条腿的人还不好找么?满大街都是,任我挑,任我选。”郑长乐潇洒地甩了甩头,自言自语道。
“世间溜溜的女子,任我溜溜地爱哟……”他哼着小曲,又幸福起来,直奔不远处的菜市场。
02
母亲住得不远。一爬上坡顶,再往下,就是母亲住的老房子了。那地方叫谢家沟,沟背后是一面山坡,一边是菜地,另一边是低矮民房,密密麻麻,直至江边。翻过山去是金厂沟,沟那边又连着一匹山--这里处于长江北岸,地势起伏,有爬不完的坡,翻不完的坎。这也是典型的重庆地形。有首歌是这么唱的:“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
这些民房大都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老式的竹木混搭的吊脚楼,油毛毡盖顶,也有篾笆条加黄泥巴敷的棚屋,最好的要算砖房了,却都无一例外低矮破败。这里曾经是大型国营企业如织布厂、港务局,以及长江航运的家属区,后来随着国营企业的不景气、织布厂的倒闭、长江航运的凋零,这片曾经火热的生活区才衰败下来,只剩些退休老人和下岗工人,整天无所事事,聚在一起靠搓麻将、摆龙门阵打发不死不活的光阴 。
郑长乐每次去看母亲,走在熟悉的山路上,都有梦回童年的感觉。遗憾的是,山坡上绿油油的菜地不见了,到处都是荒草和垃圾。路上的石板也松了,脚踏上去晃晃悠悠,似乎再难承载行人。
母亲住的房子位于菜地和居民区交界处,共有四户人家,三户都是和母亲一样的空巢老人,一窝儿女翅膀硬了,飞出去就很少回来。只有一户年轻些,是一对下岗的中年夫妻带个读书的儿子。小院的木门敞开着,里面清丝哑静。郑长乐一进去,就感到一股舒适的凉意。母亲不在家,她一定是打麻将还没回来。他掏钥匙开门,才有邻居探出身子跟他说话:“哦,原来是长乐回来了。我还以为是贼娃子进屋了耶。”因为没有好心情,郑长乐跟邻居支吾两句,算打过招呼,便进了屋。里面黑咕隆咚的,只见一个人影一动不动坐在床头。那是大哥郑长宝。
郑长宝是傻子,十六岁那年被一颗流弹击中,就傻了。那一年重庆搞武斗,几家兵工厂的轻重型兵器都被造反派们搬出来。子弹在天上如焰火乱绽,大炮隔着江,轰来轰去。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郑家家教严,怕孩子们出去惹事,就把他们统统关在家里。长宝是老大,最懂事,负责在家看管弟妹和煮饭。母亲在织布厂上三班倒。有一天,他为母亲送饭回来,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被一颗不知从哪里飞来的流弹击中了后脑勺。送去医院取出了弹片,捡了条命,人却傻了。后来他的左边身体慢慢萎缩,只剩右边身体还能动弹。耳朵能听懂些简单的句子,却说不出话来,从此就只能吃喝拉撒,跟植物人一样。死也不死,活又活不抻展。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一直是郑家最沉重的痛。
“大白天的,屋里怎么这么黑?”郑长乐有些不适应,去拉开用旧床单改做的窗帘。
屋子顿时明亮起来,一屋的破败便一览无余。发黑的竹碗柜,油漆脱落的木饭桌,粗糙的水泥地面,墙上发旧的年历画。郑长宝似乎不太适应这样的明亮,头压得更低。郑长乐厌烦地皱了皱眉,瞥一眼他身后的床,又用鼻子吸吸,没发现怪味,才说:“长宝,你今天没有画地图呀?”郑长宝抬起头来,用呆滞的目光望他一眼,算是回应,又低下头去。郑长乐不再看他,把篼里的菜拿出来放在桌上,藤藤菜、豆腐干、瘦肉、番茄,还有鸡蛋。都是母亲爱吃的。爱情实在靠不住,唯有这母爱,任时光荏苒,仍坚如磐石。
这房子依山而建,几家住房在坡下,共用厨房在坡上。中间由几步石梯相连。郑长乐脱下衣衫,光着上身,拿了脸盆和毛巾,就去厨房,想接水洗脸,这才发现接不了水,水龙头都加了锁。那小木盒还是自己的杰作,怎么就忘了?便自嘲地笑笑,想他真是老了啊,忘性好大。从前几家人共用一个水龙头,费用平摊,几十年都相安无事过来了,近几年才突然有了隔阂,计较起各家用水不均,平摊起来不划算,最终想出这个法子,不仅各家分装了水表和水龙头,还嫌不够,又在水龙头上加了盒子上了锁,邻里之间当贼防。他悻悻转身,揭开旁边的水缸盖,发现水缸也空了。再看旁边母亲的灶台,也冷锅冷灶,就想,母亲一天没生火,难道中午没吃饭?赶紧下楼回屋去,打开冰箱,发现里面除了一锅绿豆稀饭,就是一碗泡豇豆,几块豆腐乳。母亲把日子过成这样,郑长乐心酸起来,便拎了水桶去打水。过了门前的小河沟,对面不远处的菜地间,有一口老井。郑长乐一桶水打起来,先把自己擦洗得浑身清凉,再一桶一桶拎回家,直到把母亲的水缸灌满,才关了门,去找母亲。
屋背后的半山坡上,有一个当年为备战而挖下的防空洞,从没派上防空用途,倒成了这一带居民夏天里的避暑天堂。郑长乐人还没走拢,就听到一阵稀里哗啦的洗牌声,和着阵阵浸骨的凉意,向他袭来。有人远远见了他,扯起嗓子通风报信:“郑婆婆,你家长乐来了。”
郑母正在兴头上,没料到儿子突然来了,既惊喜又慌张,抬起头来嗔怨道:“啷个今天不上班有时间了?”旁边看牌的人就趁机打趣:“难怪郑婆婆今天手气好,连打自摸。原来是儿子带来的好运气。”
郑长乐跟众人打过嘻哈,就站到旁边看母亲打牌。郑母哪里还有心思,吃了一个包席,自己都不好意思了。直到最后点了个炮,掏出五角钱来索性撤退。说儿子难得回来一趟,她得回家为儿子煮饭。
母子俩就手牵手回家。郑母瘦瘦小小的,笑眯眯的一脸慈悲。走到拐角无人处,她伸手去摸了摸胀鼓鼓的荷包,高兴道:“长乐,妈今天手气好惨了,接连打了几个自摸,还做了一个清一色,赢惨了!”郑长乐也顺势侧过身去,伸手拍了拍母亲的荷包,夸张道:“当真!看来这两天的菜钱又有着(落)了。”
等拐下山坡,快到家时,郑母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仰头望着儿子说:“对了,这么大的事,你看我怎么就差点忘了?长乐,下个月这里就要拆迁了。这回是真的。还说,提前搬走有奖励。五千块钱的搬迁奖呢。你赶快帮妈找房子吧。”
“真的?”郑长乐也有些不敢相信。早就传说这里要拆迁,沸沸扬扬好几年了,耳根子都起老茧了,却一直是只吹风,不下雨,没动静。
“煮的!难道妈还骗你?今天上午都来人了,正式通知,说下月初开始正式拆迁。有两个方案让我们选,一个是领拆迁补贴,自找住处;另一个是不领钱,得安置房。听说安置房偏远得很,在机场那边。我是不想搬那么远。你们几个娃儿都在城里,妈年纪大了,不想离开你们住得太远。你说呢?”
“那当然。妈,你住远了我们也不放心啊,去看你一趟都不方便。”
“就是。这一天一天的,腿脚越来越不利索了。你就赶快帮妈找房子去吧。早搬有奖,五千块呢。”
两个人的心都要飞起来了。谢天谢地,终于要搬了。“看报纸上说,政府准备把整个江北老城都拆掉,重新规划,要建文化中心、歌剧院。今后市政府都要搬过来。你们下面这一动,我们上面也快了。”
“那就好了,这沟沟头我住了几十年,早住够了。正愁这人啊,一天一天就老了,出门爬坡上坎的,买菜都难。还以为妈这把年纪,等不到搬新房那天了呢!真是老天开眼啊!”
一张老脸都笑开了花。
一进屋,郑母就直奔里屋,迫不及待,在门背后的尿罐上解了一泡长长的小便。然后出来站在老头的遗像前,嘀咕道:“老头子,这里马上要拆迁了。拆迁后,我们就要搬去住楼房了。新楼房都建在大街上,出门就是菜市场,方便得很。房子还有厕所,就不用再倒尿罐了。厨房呢,不烧煤,都烧气。开关一拧火就来了。那日子才叫幸福哟,就像进入共产主义。你个人要早走,没那个命。不然也跟我们一起搬新家,享福去了。”
郑父一副慈眉善目,在黑框里朝她微笑,听了也不嫉妒,依然笑眯眯的,仿佛在说:“去吧去吧,把我的福也一起享了。”
郑长乐嘴里叼了根烟,皱着眉头在厨房发火煮饭。他动作娴熟,先掏空煤灰,往炉芯里塞些废纸碎柴,上面再搁上几块煤球,打火机往炉底一伸,“咔嚓”一声,火就来了。郑长乐拍了拍手上的灰,站在楼梯口,朝下喊:“长宝,扇火!”就见屋里那雕像动了动。郑长宝佝偻着背,手里拿一把烂蒲扇,一颠一颠走上来了,坐在小木凳上,对准煤炉口,一下又一下,有力而准确地扇起火来。这是他干得最好的家务活。
郑母一边理菜,一边说:“长乐呀,今天又不是星期天,啷个突然就跑来了?害得妈火也没发,饭也没煮,家里连像样的菜都没得。还好你带了菜来,不然今天晚上就只有稀饭咸菜了。”
“咳,想妈了,就来,难道还要预约么?我就是专门搞突然袭击,看你过得好不好?结果呢,不行哟,妈,你看你都吃些啥?就是稀饭下泡豇豆呀?有啥子营养?自己的身体都不要了,还说不要我们操心,你会自己照顾自己。你就是这样照顾自己的?”
郑母有些不好意思:“唉,这么热的天,也吃不下东西。再说了,出门买菜,爬坡上坎的,懒得走。反正两个人也吃不了多少,不想太麻烦。”
洗菜水被倒进桶里,拎到屋外。郑母走进里屋,端出藏在门背后的瓦尿罐,一颠一颠出了门。还有长宝床下的尿壶,也满了,也得倒掉。这是她每天必做的工作,黄昏时分,倒掉蓄存了一夜一天的宿便,洗菜洗衣剩下的水,正好用来冲洗尿罐。
郑长乐在厨房煮焖锅饭。把米放进锑锅,加水煮开,滗干米汤,再侧起锅来一圈一圈慢慢焖。灶旁边的石板下,上次买的煤球已所剩无几。看来又该买煤了。他从前不觉得,自从从这里搬出去,住进单位集资的楼房,用上天然气,才发现烧煤太麻烦了。买煤挑煤,发火背火,通火时煤灰乱飞,用后还得掏渣清理,太落后了。拆吧拆吧,他都有些等不急了。
趁焖饭的间歇,郑长乐去厨房门外抽烟,正看见母亲端着尿罐颤颤巍巍走出来。门前的小溪沟 ,终年流水叮咚,从后面坡上的大堰塘流出,一路往下,流过三洞桥,再流进长江。母亲站在溪沟边,一边跟邻居说着话,一边动作熟练,把尿罐往条石上一放,揭开盖子,朝前一倾,郑长乐就闻到一股浓烈的臊臭味在空中飘来。
不能住了,不能住了。都进入21世纪了,看看城里的有钱人,都住洋房开小车了,过起电影里外国人的生活。这里还这么原始落后,简直还像旧社会。郑长乐愤愤然,把手里的烟头用力一扔,弹进沟里。记忆里的这条溪沟可不这样。夏天一场暴雨后,溪水猛涨,从上面的农田漫涌下来。郑长乐还记得当年在沟里撮鱼的情景,小伙伴们纷纷偷出家里淘菜的筲箕,在水草间这里一撮,那里一搂,总能捞到几条活蹦乱跳的鱼虾。那时的沟边石缝里,还时常可见螃蟹出没。夏天人们还喜欢在沟里淘菜洗衣。这才过去多少年啊,清澈的溪沟竟然变成露天公厕,浊水横流,臭气熏天。这一坡下去的居民才惨,如同生活在粪坑旁。只是美了溪沟两边的杂草野花,一年比一年更长势丰美。
可这又能怪谁呢?先是坡上的农田荒芜,纷纷建立的皮革厂、塑胶厂等,都把废水排进这沟里。沟水一会儿是刺鼻的污红,一会儿是呛人的浊黄,有一阵还冒着一层厚厚的白沫,令人一闻就恶心想吐。
这一带民房都没有厕所。早几年还有农民每天黄昏挑着木桶,来挨家收粪。人还没走拢,悠长一声“倒桶了--”,家家户户就行动起来。那时候三洞桥外的长江边上,总泊着一只收粪的木船。也不知从何时起,木船不再来了,收粪人也不再见踪影,推算起来,应该是从农村用上化肥开始吧。有了化肥,便不再稀罕城里人的粪便,也因此苦了城里人。刚开始大家还讲文明,把尿罐端到附近的公共厕所去倒,但很快就放弃了。因为厕所也没人来清理。这一带坡地,车来不了,上下全是狭窄的石梯路,运输只能靠人力,肩挑背扛。公厕的便池满了,一场大雨,冲得四处横流。不久公厕就被封了,人们只得把家门前后的阴沟水渠,当成天然的排污设施。流水也真是好东西,能冲走一切污浊秽物。至于冲去哪里,他们就不管了,也管不了。只求眼不见,心不烦。也得感谢这山坡地势,这江河东流,再臭再脏,来一场大雨,稀里哗啦水一冲,又干净了。这真是老天对重庆的厚爱。
晚饭时又说起拆迁的事来。郑母兴奋道:“长乐啊,我们下面这一动,你们上面也快了。依我看呢,今后我们买房子,也买到一堆儿,好不好?妈是一天天就老了,不想离开你们住得太远,害怕到时候想看你们一眼都难。”
“那当然,还用你说。最好是一幢楼里,楼上楼下,就更方便了。”
他们一边吃饭,一边憧憬美好未来。刚吃完饭,郑长乐腰间的小灵通突然响了。是熊大哥,问他事情办妥没得。说身边有好几个候补人选,都等着郑长乐合法解套,恢复单身。
郑长乐接完电话,情绪高涨。郑母耳背,在机声隆隆的织布厂当了三十多年的织布工,听觉早就迟钝了,就盯着儿子:“啥事啊,这么高兴?捡到钱包了啊?”
郑长乐这才把离婚的事情告诉了母亲,说今天刚刚办了手续,就有人要帮他介绍女朋友。他都还没喘过气来呢,想歇歇再说。郑长乐边说边装出一脸的轻描淡写和对别人热心的不耐烦。仿佛离婚是一件美事,他梦寐以求很久了,终于如愿。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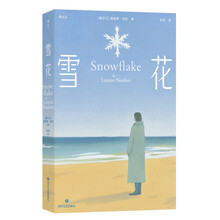

——余德庄 国家一级作家
海娆文笔柔软,而目光尖锐,《早安,重庆》有生活感和当下感,这是《红岩》首发这部长篇的主要原因。
——刘阳 《红岩》主编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读罢令人掩卷深思。人生是一部痛苦史,主人公却能在心灵的沉淀中寻找希望,战胜挫折,一个绝对的现代阿Q。作者旅居德国,却关注国内民生疾苦,为弱势群体写作。这种写作良知,让人敬佩。
——大仙 作家、诗人,“北京青年报”资深编辑
我很喜欢这个书名,它让我想到我的故乡,亲切而忧伤。还有作品中那些“没有意义的小人物”,他们的故事不仅让我感动,还让我看到一种民族坚韧的精神力量。
——Arold Stadler 德国作家,以“故乡三部曲”闻名
小说生动地展示了一幅当今中国底层百姓的生活图。尤其精彩的是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他虽然经历过文革,却没有生活在阴影中,反而让自己更加坚强。他面对困难时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的情景,尤其意味深长。
——Frank Quilitzsch 德国作家、文学博士,“图林根报”文化主编
作者通过主人公的命运,展示了当今中国高速发展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如城乡差距、看病难等。这是一部扣人心弦的小说,它不仅引人入胜,而且告诉我们怎样在绝望中发现希望。主人公细腻的内心体验,让读者感同身受。
——Simin Mazaheri德国汉学博士,自由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