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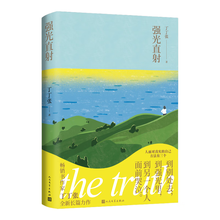

1. 孺子而兼侠女,柳如是,秦淮八艳之首、江南第一钗
2. 《柳如是》是与榕树下网站合作的长篇小说之一,曾在网站连载,点击量及回帖量很多。很多网友评价很好。
柳如是(1618-1664),本姓杨,名爱;后改姓柳,改名是,字如是。
柳如是幼年不幸。14岁时,被故相周道登买于勾栏,强索为妾,未及一年,卖于娼家。后流落松江,自号“影怜”,与东林等党人交往。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东林领袖、常熟人钱谦益(字牧斋,明朝官至礼部右侍郎)与柳如是结婚,居绛云楼,读书论诗,相对甚欢。明亡,柳如是劝钱谦益殉节,钱推托不允,如是勇身投入荷花池身殉未遂。钱降清后,遭忌被逐回乡,郁郁而死。钱氏家族乘机逼索柳如是,如是四十六岁时自尽。
《柳如是》以半实录的手法再现了柳如是作为“秦淮八艳之首”的一生。
柳 如 是前言前言
中秋的前一个晚上,我又一次修改了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柳如是》。柳如是是生活在中国古代男性极权社会里的女子,她美丽、高洁,而且才情非凡,她对虞山的地域文化与钱谦益的家族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曾被誉为六朝金粉之地的南京,在明末清初的那场政治大动荡中,涌现一批著名的爱国歌女,其中最杰出的人物便是柳如是。
三百年已经过去了,昔日的云烟已经消散。除了虞山顶上埋葬的艳骨之外,历史已经把柳如是的一生,默然传奇为坚硬的化石。千百年来无人能够打碎红颜薄命的枷锁,一落红尘便打上妓女的烙印。她走红时千人呼、万人唤,富比封君、势夺王侯,可谓“红颜素封”。达官贵人相交接,文人名士相趋承。但是,她抗争、她呐喊。尤其是在举国艰难的时候,她对国家兴亡的关心、对气节的坚守,丝毫不减须眉男子。清兵攻破南京,柳如是欲殉国难,羞煞食君之禄的丈夫钱谦益。柳氏临终嘱咐子女“悬棺而葬”,表示死后灵魂不践清朝之地,何等的刚烈!
柳如是虽然沦落风尘,历尽坎坷,然而却做到了出污泥而不染,丹心耿耿、胸怀天下兴亡,因而为人们所称道。历来有许多作家、学者,专为她写的著述尤多,其中以近代经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所著的《柳如是别传》,尤为经典名作。近年来,南京的名作家宋词先生所写的近30万字的巨著《南国烟柳》,和业已播出的电视剧《乱世名姬》、邱维俊的《柳如是的传说》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之所以引起如此众多的名家,为之撰写传记传之于世,是因为她的坎坷和多色的人生富有传奇色彩,耐人传诵,她的人生的确值得一传。
柳如是是明末名妓、秦淮八艳之一,她的爱、她的恨、她的离愁、她的思念都是古典优雅,也是更忧伤的故事。
圣人的典训,已经给妇人定了性,孔子是这样说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提起“妓女”,人们大都深恶痛绝,在今天更是典型的打击对象,有什么好写的,还能为她们树碑立传吗!
“妓女”不仅伤风败俗,而且传播性病,污染社会。尽管妓女的产生与存在,有其罪恶的社会根源;但反过来,妓女存在的本身,却又是加剧社会罪恶的一个因素。因此,从根本上讲,妓女不可书,不可传。但是妓女又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社会存在,妓女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构成了社会生活史的一个侧面。而且,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官妓私娼的合法存在,由于那个时代嫖娼宿妓之风的盛行,妓女对文学、艺术、音乐、舞蹈以及政治、军事、经济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从而在许多领域打上妓女的烙印。例如,在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词曲大家,如白居易、元稹、苏轼、柳永、关汉卿等人,就从妓女身上获取了艺术营养。因此,可以说不研究妓女的历史,就不能完整地认识社会生活,尤其是不能完整地认识中国妇女的历史。而且妓女是伴随私有制中罪恶的沃土盛开的一束罂粟花,私有制不灭,妓女不绝。不让它开在地上,它就要伏在地下。妓女问题,是不能回避的,所以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单纯的文化角度来评述妓女,认识产生妓女的社会根源,也是很有意义的。
如果说“红颜多薄命”,那么沦为妓女的红颜,就是薄命中的薄命者,她们的悲苦不可胜言。柳如是百折不挠的追求,可以折射出妓女们的不幸与辛酸,而柳如是最后的结局也是一个悲剧。
本书我也是以半实录笔法论述名妓之花柳如是的兴旺与凋谢,留给读者去评价,去思考,这一精神,不失为谨慎。当然各位读者,力图希望我写活名妓的风姿,写好名妓的生活,写出名妓的成就,写透名妓的心态,反映名妓所处时代的风俗,鞭笞产生名妓的社会土壤,还历史本来面目,这又是严肃的。为了能写好这本《柳如是》,我拜访过不少研究历史的老师,如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的许多历史专家。本书写的是历史,而非风月小说。通过柳如是这位名妓人物的坎坷一生来反映封建社会底层妇女的生活,并从一个侧面展示封建社会的一角或一个层面。所以写人写事迹皆持之有故,评说道理皆言之有据,行文所书重事实不作虚构。
本书经历了九个多月的时间完成,在那些乍暖还寒的夜,我细数着柳如是的过往,然后在纸上写下沧桑。而在那时,我的心里其实是不忍与不舍的,当我一夜或几夜听雨临风,以一种轻盈的姿势,轻易便跨越柳如是绮丽的一生时,我不知道,我的笔能否写尽她的欢喜与忧伤。看着她的笑脸越百年而于纸上,我常常会觉得惭愧,怕我太过草率的文字,不能为她成就一段传奇。
我想,柳如是是厌恶一切平凡的,即便心中向往,那平凡也是绚烂后的平淡,而非一生寂寂。她超然的品格与绝世的才情,注定了她只能以同样一种决然的姿势,走完她的一生,如夜空里的烟花,虽然短暂,却也要为这尘世做一次最艳丽的绽放。
岁月轮转,刹那芳华,当深秋的风迢迢万里,吹过她们如丝的发鬓时,我希望,我对她的这一份珍重与怜惜,能稍稍弥补这尘世带给她的苍凉,能让她那美丽而高尚的灵魂,体会到一点末世的温情。
2008年9月14日
柳 如 是
还记得,潮湿的码头和旧时的飞絮还记得,潮湿的码头和旧时的飞絮
如是在梦中又见到了那个忧郁不堪的美艳少妇,她穿着洁白的衣裳,用纤纤素手握着一把粉红的油纸伞,顶着雾气一样的细雨,袅袅婷婷穿过江南的粉墙黛瓦,在密密匝匝的细雨中轻踱芳步,渐行渐远。
她走上石桥又小心地走下石阶,驻足在河边。她拿开雨伞,仰起脸看着灰麻麻的乌云,细雨打湿了她的脸……眨眼间少妇不见了,河水荡漾着的圆晕渐渐平息了,只有那把撑开了的粉红色的油纸伞红得那么鲜亮。雨更大了,油纸伞被风吹进河里,顺水漂向远方,变成一点红晕……
如是大声地叫着:油纸伞……粉红的油纸伞……
她从梦中惊醒了。
昏暗的油灯下,杨洁儒正在用磨石磨铡草药的刀片。他给灰色的磨石溅上水,然后,手里的刀片开始有节奏地滑动,刀刃上的锈蚀与磨石上的水纠缠成黑色的泥浆,跌落到地上。刀片的锋利本色逐渐呈现在油灯之下,寒光夺目。
杨洁儒听到女儿的惊叫,连忙放下刀片。掀开帐子,看着满头大汗的如是问:如是,你是不是又做噩梦了?如是喘着气扑到杨洁儒的怀里说:爹爹,我又梦见那个美艳的女子,还有她的那把粉红的油纸伞。
杨洁儒急忙取来一条汗巾为女儿擦汗。如是看着父亲的脸问:爹爹,为什么我总是梦见那把粉红色的油纸伞,撑伞的女子是谁?她是不是投河自尽了?我好像亲眼看过这一幕。
杨洁儒说:那不过是个梦,不要多想了,明天还得走三十里水路到盛泽镇的刘地保家去为他老母看病,草药我都配好了,现在二更了,你睡吧,爹爹看着你,你就不会做噩梦了。
父亲的回答含糊混沌,但是如是还是疑心重重。童年的足音开始清晰地叩起心扉,悠然的思绪浸润在一派澄澈如水、明朗如画的温馨记忆里。那个撑伞的女子一步一回头地看着自己,好像她和自己有着揪扯不清的血脉关系。每次梦到的都是同一张面孔同一把粉红色的雨伞,那个场景是那样清晰,一闪而过又记忆牢固,就像被闪电击了一下。她到底是谁,为什么总出现在自己的梦里?
五年前母亲去世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让自己终身难忘的话——那个时候,家里还很富有,婆子丫鬟成群地进进出出。母亲躺在缎被中,伸出鸡爪一般干枯的手握着父亲的手说:我死后,你马上变卖了家产,带着如是逃命去吧!无论如何也得保住如是。这些话分明暗示有人在追杀自己,可为什么自己能惹来杀身之祸?如是很是迷茫。后来,母亲出殡以后,父亲真的变卖了家业,带着如是背井离乡,成为一个流浪民间的寒医。
父亲杨洁儒只重医德,不重钱财,尤其对贫困人家更是分文不取,经常送药上门。但同行很多,生意又冷清,父女俩只够温饱,兼之义不长财,杨洁儒走到哪里都是明月一肩、药包袱一个,依然故我。父女俩整整流浪了五年多,饱尝人间冷暖沧桑。
杨洁儒坐在女儿的床边,只打了一个盹,就听到鸡叫声。他把如是叫醒,背着药袋离开了客栈。天还没有大亮,月亮很好,圆圆的,起伏游移在云层里。父女二人穿过狭窄的碎石街道,来到码头。如水月色轻笼着眼前的一切,早有等待在河边的渡工们点着灯笼,等待渡客。杨洁儒抱着女儿上了竹筏,筏工用竹篙一点河水,竹筏缓缓游动着。河堤一线仍旧泊着几只竹筏等待着渡客。如是依偎到父亲怀中,看着河堤上广阔的田野,浓淡不一,迷迷离离分不清是庄稼还是灌木。河水如绸缎一样平铺着,筏工的竹篙哗哗地拍打着水面。天色逐渐泛白,水声汩汩。山、田野以及河边的竹林霎时间生动起来。如是回首刚才登筏的码头,灯火阑珊。几只等待渡客的竹筏上高挑的灯笼依然亮着。远处,不时地传来狗叫。
如是问杨洁儒:爹爹,你昨夜睡了吗?
杨洁儒温和地看着爱女回答:睡了,睡得很好。
大概行了半日,才到了盛泽镇的码头。刘府的下人早就等待在码头的石栏后。杨洁儒上了刘府派来的马车,走了一个时辰,到了刘府。刘地保夫妇很热情地招待着杨洁儒父女。喝过茶吃完饭以后,杨洁儒问刘地保:病人在哪里,我不妨先看看病人去?
刘地保深深地长叹了一口气说:我和你如实说了吧,家母患的是肺痨,跟着她的丫鬟婆子传染上这种病都死去了,远乡近里没有郎中敢来我家为家母医治,我虽然不是一个孝子但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故去,前日听一个外乡人说杨郎中很重医德,方将您请来,假如杨郎中能够久住下来为家母治病,我万分感激,如果杨郎中害怕传染,现在离去我也无怨。
杨洁儒听了刘地保的话哈哈一笑说:我杨洁儒走遍天下以德行医,既然来了,哪有不见病人就被吓跑的道理,只是我有一个条件,你们不要让我的女儿沾染病人,让她好好在府中生活。
刘地保夫妇双双下跪,冲着杨洁儒拜了三拜。杨洁儒赶紧把他们夫妇扶起来说:干我们这一行的,治病救人是我们的本分,地保大人千万不可太客气。
刘地保命家人打扫了上房的一个院落,安顿如是住下。自己带着杨洁儒来到后院老夫人的厅堂中。穿过厅堂,就是老夫人的卧房,屋里显然好久没有人进来打扫了,雕梁画屏上挂满了灰尘。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垂死的酸气。卧榻上,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夫人蜷曲在明纱的帐子中,像蜘蛛守在网里一样。
刘地保对杨洁儒说:您上去看看病人。
杨洁儒走近卧榻,刚要掀开纱帐,老夫人突然支撑着两只胳膊坐了起来,喘作一团,半天才说了一句:你们都给我滚,小心我传染了你们,作孽呀!
刘地保远远地躲在一边说:娘,不孝儿终于给您请来一个好郎中,您就别折腾了,好好让人家治疗吧。
老夫人用手指指着杨洁儒问:你不怕我传染给你病?
杨洁儒笑着坐到卧榻边上说:老夫人,如果怕死,我就不行医了,我先为您把脉。
老夫人慢腾腾地挽起衣袖,伸出一条肮脏的胳膊。杨洁儒让刘家的仆人端来一盆温水,亲手给老夫人洗了手臂,然后把脉下针。
从老夫人柔弱的脉象和吐出的血痰来看,杨洁儒知道老夫人八成难愈。他从老夫人的内室走出来和刘地保说:老夫人确实病得很重,但是还是有三分希望,这些日子,我留在后堂为老夫人针灸煎药,劳烦你们照顾好我的小女如是,让她自己学琴念书,万不可荒废时日。
刘地保特别感激地说:杨郎中不但医德一流,而且教女有方,您只管在后堂熬药治病,如是姑娘我一定会让贱内照顾好的。
杨洁儒说:我只是先看看病情,不一定能治愈。
刘地保说:家母就是医治不好,我也不埋怨杨郎中,如果家母能够康复,我宁愿把我刘家的家产分给杨郎中一半。
杨洁儒说:呵呵,我不要你的一半家产,我只想带着小女流浪江湖。
从进刘府的那天起,如是就与父亲分开了。她住在上房的一个跨院,父亲在后堂。白日里偶尔能闻到煎草药时弥漫的香味,她知道父亲一定很忙。刘地保的夫人送来几件衣裳,穿上还挺合身,饭食也很好,一日三餐汤、菜、面食,样样齐全。如是苦心练琴读书,但也深感寂寞。她不知道父亲为刘老夫人治疗得怎么样了,从刘地保夫人的脸面上看出,她有几分喜色,所以如是断定父亲最起码为老夫人稳定了病情。
上房的院子里有几棵成年的栀子树。如是喜欢在夜色阑珊时秉烛夜读。栀子花开了,她只觉得栀子花香破窗而入,然后萦怀心间。顶着清亮的月光,如是来到栀子花前。她抚摸着一片片娇嫩的花瓣,思绪浸染着花香悠悠而来,指尖便细细生香。她借着月光,亲眼看着一朵紧锁的花骨朵儿,一点一点地在夜里完全展开。如是的心颤动不已,觉得美妙已经如诗如画沐浴着自己的心田,她仿佛听到了栀子花开的声音。如是双膝跪在花前,祈祷着老夫人的病快些好起来。
如是喜欢栀子花并不是贪恋它那满怀的芬芳和一身的高洁,而是眷恋自己家中以前栀子花开时的烂漫与温情,一家三口在花丛中轻歌曼舞。而现在,花落人亡,母亲永远地走了。
半个月过去了,如是没有见到父亲的面。
又半个月过去了,如是还没有见到父亲的面。
栀子花开了,栀子花落了,花叶泛黄了,但父女同在刘府却难以相见。如是很为父亲担心,如果他传染了老夫人的肺痨那该怎么办?常言说病人患病郎中医,郎中患病无药医。一日早上,她再也忍不住了,洗漱完毕吃过早饭,来到刘夫人的房间。
刘夫人刚好吃完饭,召集了几个女戚打牌取乐。如是进门后向刘夫人款款下拜。刘夫人很吃惊地看着如是问:如是姑娘不在上房学琴读书,来我房里,难道有事?
如是说:近日我越发寂寞,我想到后堂,一来向老夫人问安,二来看看我的父亲。
刘夫人和女戚们说:这是杨郎中的千金,这长相可是万里挑一的。女戚们连声称赞。
如是见刘夫人有意打岔,又说了一句:夫人,让家人带我去见我父亲。
刘夫人说:老夫人的病快好了,昨天竟然能吃一碗米饭,等老夫人的病好利索了,你们父女自然就能相见了。再说,你父亲再三和我家老爷说了,万不可让你进病房,我们老夫人的病可是传染的。
如是问:老太太的病既然能传染给别人,难道就不会传染给我父亲吗?
刘夫人的脸一下白了,好像死人一样,半天才缓和过来,目光迟钝了一下问:你是不是听到我家下人说什么了?
如是说:没有,夫人多疑了,您家的下人从来不和我说一句话。
刘夫人说:杨姑娘真是个孝女,一心想着你父亲,你父亲是郎中,怎么能传染上老夫人的病呢?你只管回房写诗作画,等你的父亲见你的学问有了长进,那他会更高兴的。
如是看着刘夫人没有带她去见父亲的意思,心里有些慌了,再看刘家的女戚们已经摆好了牌局,只等刘夫人上场了。
如是便很难堪地回到上房,守着空空的院落又等了7天。这7天中如是坐卧不宁,她决定到刘家的后堂寻找父亲。当她刚要走出上房的院子,刘家的一个男仆守在门口对她说:杨姑娘,你不能出这个院子,我家主子交代过了,府里有病人,来探望老夫人的亲戚很多,姑娘一个女孩家的,不方便在府里来回走动。如是和刘家的下人说:我和父亲进府快三个月了,一直没有相见,请问哥哥,我父亲的身体如何?
那个下人也是一个守口如瓶的人,尽管如是哥哥长哥哥短地叫了半日,他仍然面不改色,也不说一句话。如是无奈,又回到上房,趴在床榻上大哭起来。
晚上,刘家的下人照样把饭菜端进屋里,放在桌上,一声不吭地转身走了。如是一口饭也吃不下去,她端坐在黑暗中,双眼直直地望着窗外——树的顶端是星星和月亮,它们在夜空的旷达中传递着某种暗语,黑夜使世界有了庄严的深度。如是想着这五年和父亲一起流浪的生活,不管走到哪里,父亲都亲眼看着她入睡。现在这种断裂的生活规则让她提心吊胆。
如是回忆着父亲对她说过的每一句话,回忆着父亲对她的千般慈爱。回忆是多么疏离感叹的痛,在夜里变得清晰、浓郁、经久不息。
如是一直坐到第二天早上,刘家的下人又来送早饭的时候,看到昨夜送来的饭菜丝毫没动,再看坐在床榻上的如是一脸惆怅,双眼恍惚,眼睛上蒙着一层水雾。下人觉得这样下去要出人命了,便匆匆禀报了刘夫人。刘夫人也无法,着急地跑到前厅找到了刘地保,和刘地保说明了如是的异常反应。
刘地保说:老夫人日渐好转,杨洁儒却染上了老夫人的暗疾,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要让杨洁儒死在咱家,那样太晦气了。
刘夫人说:那该怎么办?总不能把人扫地出门吧?
刘地保说:今天,你上账房柜上拿二十两银子,让他们父女赶快离开我们家。
刘夫人说:这也未必太说不过去了,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刘地保说:你一个妇道人家懂得什么?像杨洁儒这样的流浪郎中,一年不知道要饿死几百人,何况咱家对待他的女儿也是很好。
刘夫人从前厅出来,按着刘地保的意思去办了。并且吩咐下人说:杨郎中父女离开得越快越好。
如是正在惆怅不堪的时候,刘家的一个老妈子来到上房,对如是说:杨姑娘快收拾一下东西,随杨郎中走吧。
如是问:老夫人的病好了没有?我的父亲在哪里?
那个老妈子说:姑娘不必多问了,随我来就是了。
如是略微收拾了一下,背着两个包袱,跟着老妈子出来,在刘府的大门口等待了片刻,只见刘家的下人搀扶着杨洁儒从弄堂匆匆而来。如是看到面如枯草的杨洁儒大吃一惊。三个月不见,父亲整个人都变了样。
如是迎接上去问杨洁儒:爹爹,您老人家到底是怎么了?是不是传染上刘老夫人的肺痨了?
杨洁儒看着如是摆摆手说:我不光是传染上刘老夫人的肺痨,我又添了新的疾病,如是,你扶我走吧。
刘家的下人递给如是一个包袱说:我们老爷和夫人说了,我们老夫人能医治到这个份上实在是不容易的了,这是二十两银子,给你父女做个盘缠,杨郎中该找个地方养养病了。
如是接过包袱对刘家的下人说:我父亲进你们刘府的时候,可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现在成了这个样子,只拿了二十两银子来打发我们父女,就这二十两银子连一个好客栈也住不起,我要见你家夫人,评评这个道理。
刘家的下人说:我们老爷说了,让你们父女赶快离开我们刘府,不然杨郎中死在我们府中,就不好说了。
杨洁儒说:如是,这也许是父亲我命中所遭,我们走吧,先找一家客栈落脚。如是虽然生气,但是也没办法,只好扶着杨洁儒出了刘府。父女二人刚刚出府,刘家的下人哐啷一声把门关上。如是和杨洁儒同时打了一个寒噤,一阵冷冷的秋风拂面而来,吹起了如是的发帘,杨洁儒看着如是说:你长得越来越像你母亲了。
刘地保夫妇没有出面相送,他们觉得杨洁儒已经完成了在刘府的任务,该走了,最好是走得干净利索。如是回头看了看刘府紧闭的大门,狠狠地说:真是狼心狗肺的人家,可惜还做了地保,真是这一方人民的不幸呀!
杨洁儒对如是说:我们不要和这样的人计较了,公道自在人心。刘老夫人的病能够渐痊愈,我就心满意足了。普天下的恶人都是一样的,只要我们无愧于他人就是了。
如是搀扶着杨洁儒,投宿到盛泽镇的一家客店里。如是每日煎药做汤服侍着杨洁儒,可惜杨洁儒已经病入膏肓,难以复愈。杨洁儒自己也明白自己的病已成就,根本没有好转的希望。不过是挨一日是一日罢了。杨洁儒把如是熬的药喝得一滴不剩,可心里没有一丝好起来的打算。
江南的深秋,已经有了凉意。如是怕父亲受冷,让店家点了火盆放在父亲病榻之下。杨洁儒看着勤劳的女儿,心中更加不忍。尤其是黎明之时,杨洁儒胸口憋闷简直喘不过气来,如是坐在他的身边,给他捋着嗓子。杨洁儒喘了一阵问如是:你现在还做红纸伞的梦吗?如是说:有时也梦,不过比以前少了,爹爹为何突然问起这个问题?
杨洁儒说:事到如今,我不过是一日半日的光景,我把你的身世告诉你,死也无憾了,只可惜你的年纪尚小,还没成人,这便是我唯一的牵挂。
如是哭泣着说:我好好伺候爹爹,或许能有好转,哪怕女儿我粉身碎骨。
杨洁儒说:孩子,你梦中的那个投河女子不是别人,她是你的母亲,我不是你的爹爹,是你舅舅。
如是突然睁大眼睛,惊奇地问:爹爹,您说的是真的吗?杨洁儒点点头说:你原姓柳,自从跟了舅舅我之后你便姓了杨。
如是说:事到如今,舅舅,就把我的身世告诉我吧。
杨洁儒说:你的父亲在朝中曾任过御前太医博士的医官,名柳养吾,饱读诗书,尤精医典,对《黄帝内经》、《难经》以及《伤寒论》等经典医著熟之不览,尤精于脉决和《本草纲目》,堪称一代名医,所以被召入宫廷侍奉。
当时,他是太医院的学术权威人物,为人性格耿直,医术高明,因而招致院中同行的嫉妒。当时的皇帝明光宗朱常洛,长期沉湎酒色,生活失去正常的节制,以致酒色伤身,一病不起,于是召太医院为之诊治,柳养吾出差外地未归,这病首先是院中一位所谓权威御医叫王殉的诊治的,王殉的医道其实平庸,不过嘴巴却能说会道,夸夸其谈,当谈起医道的五行和阴阳之道时往往能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使人深信不疑,其实看病常常牛头不对马嘴,时有误人性命的嫌疑。不过若出了医疗事故,他却又能巧妙地推脱责任,移故于人。这姓王的在柳养吾没来之前,是院中主事,唯一的权威,但自柳养吾来院以后,由于柳养吾的真才实学,他就只好屈居其次了。他为此是不甘心的,对柳养吾怀恨在心,久欲寻隙陷之而不便。
光宗皇帝患病,由他医治,他以权威自居,切脉之后,他拍胸担保,说这病只需服他几剂汤药,即可妙手回春。皇上和娘娘等问他皇上是何症候,全说是阴阳失调和感染时令风邪,另外是亏了气血,于是在调和营养的基础上大加滋补。谁知汤剂投后,病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加剧,引来潮热恶寒,大量吐血。正在危急之时,柳养吾外地出巡回来。娘娘命太监总管急召柳太医进宫医治,柳养吾问了病情并切脉之后,眉头紧皱,只是摇头,禀奏娘娘说皇上已病入膏肓,他纵然开出处方也难于奏效。
娘娘一听慌了神色,并严肃地对他说:你作为太医院的主事,难道不为皇上尽忠,见死不救!现在正是圣上用你的时候,无论如何也要挽救圣上的性命。
柳养吾再拜启奏:娘娘,依臣的脉象推断,皇上的病,只在早晚之间的事了,微臣纵有仙方,恐也无济于事了。
碍于皇家的权势,柳养吾还是开了处方,果不其然两服药还没服完,皇上就驾崩西游了。
皇上驾崩,岂同儿戏,这太医院可就大祸临头了,这位姓王的太医见皇上驾崩,就趁机嫁祸于你父亲,说是因服他的补药而死,说皇上不该误死庸医之手,所指的庸医是谁,就无需道明了。于是你父柳养吾被御林军乱棍打死,你的母亲投河自尽,临死前把年仅三岁的你,托义仆王德带回江苏吴江娘家,由我来抚养。因畏当时权宦魏忠贤,怕他另生事端,因为那姓王的太医是魏党的爪牙,我就把你当做自己的女儿,改姓杨名如是。每日行医以后,到得晚来,教你读诗、写字,和讲解历代的忠臣义士的故事,希望你替你冤死的父母报仇。
杨洁儒说完以后一再叮咛:现在仍是奸臣当道,千万不能声张,此事仍要守口如瓶!
如是此时已初谙人事,听了舅父讲述父母的冤情,伤心痛哭了一场,并将此事牢牢记在心中,同时也渐渐明白了忠与奸的界限。后来,她恢复了原姓,嫁给了钱谦益以后,才把这件血泪隐史告诉了自己的丈夫。
当夜,窗外乌云翻滚,闪电交加。残破的客栈里,雨水从门缝中流到地上,如是趴在杨洁儒的身旁,听着杨洁儒艰难地痛诉。黎明的时候,杨洁儒断了气,撒手而去。如是抚尸大哭不已,她的哭声惊动了店小二,店小二又转告了店主。店主匆匆赶来,看见他们父女没有什么家当,只有一堆破衣烂衫,便亲自到刘地保家,来禀报杨洁儒的死况。
……
前言
还记得,潮湿的码头和旧时的飞絮
尘漠漠,浑河水落草离离
泪眸中,独立寒秋路
人何在?人在烟雨湖
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阑
春雨时,泽被苍生我亦豪
心事愁,情断画梁上
清代曹雪芹糅合王实甫“多愁多病身”及“倾国倾城貌”,形容张崔两方之辞,成为一理想中之林黛玉。殊不知雍乾百年之前,吴越一隅之地,实有将此理想而具体化之河东君。真如汤玉茗所写柳春卿梦中之美人,杜丽娘梦中之书生。后来果成为南安道院之小姐,广州学宫之秀才。居然中国老聃所谓“虚者实之”者,可与希腊柏拉图意识形态之学说,相互证发,岂不异哉!
——陈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