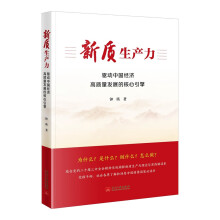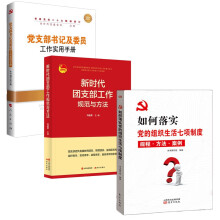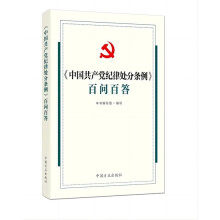《“书香政协”百日漫游:叶小文读书笔记》:
“李约瑟之问”和“颠覆性风险”
在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中,要防止出现颠覆性风险。
现在看来,在病毒来袭,在逼近的瘟疫等现实挑战面前,我们可能有必要把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风险作为民族复兴进程中颠覆性的风险之一来认真对待。我们民族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像我们保卫国土安全一样,要把它作为一个可能出现的颠覆性风险来考虑,这样很多问题就容易解决。如果我们已经判断未来公共卫生事件是我们民族复兴进程中颠覆性的考验,甚至概率比打仗还要高一些,那么就值得研究,值得花功夫去认真对待。这样来提出问题,是否可称作当代中国的“世纪之问”?这使人想起近代著名的“李约瑟之问”。李约瑟的问题是:“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这个问题振聋发聩,促使一代一代中国人警醒、震惊、深思、探索、奋斗。现在对“李约瑟之问”,我们已有答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否定之否定,转变再转变,历史又“转变”回来了!但对新的“世纪之问”,我们这代中国人,是不是也应该警醒、震惊、深思、探索、奋斗呢?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作为以“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为初心为使命的我们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好、解决好这个“世纪之问”。就像一个接力赛,如果跑到我们该发起冲刺的这一棒,却因为没有应对好“颠覆性风险”而栽了跟头甚至被“颠覆”,我们何颜告慰先烈先贤,我们何以面对后世后人?回答好、解决好这个“世纪之问”,当然远不是谈一点读书体会就可以完成,这是“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但能提出问题并且开始讨论,就是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因为话题过于沉重,我们围绕这个话题的读书,就要读出道道;我们围绕这个话题的议政,就要议出道理。如王阳明所说:“此道之在人心,皎如白日,虽阴晴晦明千态万状,而白日之光未尝增减变动。”1982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过一篇题为“社会学否定之否定的进程及其内在矛盾”的论文(1984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青年作者优秀论文奖),考察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诞生和发展,是伴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发展,对社会的认识也从原始综合阶段向经验实证阶段发展再走向辩证综合阶段的产物。诚如马克思所说,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从搜集材料的科学进入“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④。中国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道法自然”,确是博大精深的哲学思维和战略思维,放之四海而皆准,时至今日亦精灵,但充其量恐怕还只是“认识的原始综合阶段”。而近代科学,无论是物理学、生态学,还是人类学、社会学,都注重以实证、实验、实践为基础。这恰是我们中国人今天讲科学启蒙、扬科学精神特别要注意的方法,也是今天我们读书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书,就是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