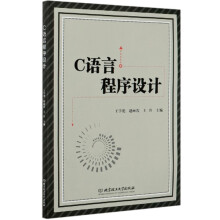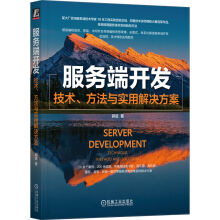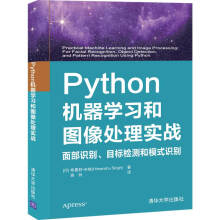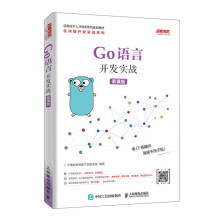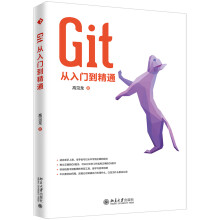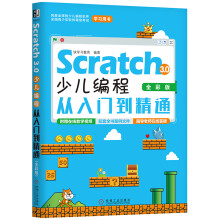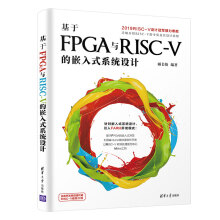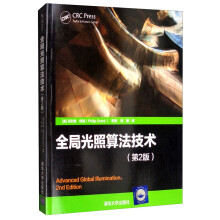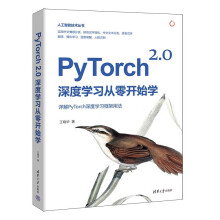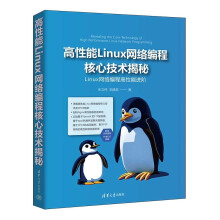1921年7月,夏季,上海。
现在已经认定在这个月的23日这一天,在法租界的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李氏公馆”内,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胞兄李书城家,13位分别从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和上海本地来的青年共产党员先后跨进这座位于石库门弄堂的李氏家中。他们是: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广东的陈公博、包惠僧和旅日留学生周佛海。除此之外,还有两名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嘎吱——”随着“女主人”王会悟轻轻地掩上石库门建筑的双叶木门,一楼客厅内便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声音:“好,现在我们开会……”
这个在夏天开启的会,虽然是在悄无声息中召开的,也只有十几个人参加,但是它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从此揭开了中华民族史上最耀眼的历史性一页。
说起中共一大和中国共产党建党史,许多人的目光总会聚焦到出席会议的13个人身上。其实,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史和中共一大,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简单地说,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关键性人物,并没有参加党的一大,这里说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然而他们由于当时各自的公务缠身而没有能够出席一大。此外,还有一位建党的重要参与者、原本的一大代表,却也没能参加一大,他就是邓中夏。
南京雨花台牺牲的烈士中,邓中夏是最接近中共一大的人物之一。参与建党和筹备一大的邓中夏,这位革命英烈、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和青年领袖,已经有无数书籍介绍过他,然而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概括的人:革命激情四射、赤胆忠心干事、从不计较得失,是一位为理想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本色共产党人。
南京雨花台的每一位烈士,都有可歌可泣的事迹。毫无疑问,邓中夏与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历史渊源最深、也最近,而他在每一次历史关头所呈现的革命者形象,也总让人难忘——
理想者与理想者在一起,碰撞出的一定是理想火花。1916年,两位湖南学子一起在同一位老师那里,产生了理想的碰撞,所产生的革命火花结成了他们青春时代的红色友谊。这两个青年就是毛泽东和邓中夏。他们的老师叫杨昌济。
毛泽东与邓中夏虽不在长沙的同一所学校,但因为杨昌济是他们共同的老师,常聚会于老师的家中,所以两位英俊青年总在岳麓书院后门的爱晚亭内谈古论今,常“英雄所见略同”。
也同是因为老师的推荐,两人先后到了北京大学。他们都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了革命领袖李大钊等人,从此皆成为与中国共产党命运相连的历史性人物。
20来岁的邓中夏,常常穿着蓝色长衫,脖子上系着一条紫色围巾,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朝气。1918年,北大主体建筑红楼在沙滩落成之后,邓中夏有时便穿着笔挺的西装和飘逸的风衣,皮鞋总是擦得锃亮,往日的小平头也开始变成了长发。他善于演讲,口才出众又热情洋溢,充满鼓动性,因此我们印象中的“五四”运动时期的青年形象,其实就是按邓中夏的形象塑造出来的,或者说之后的许多文艺作品中的“五四青年”形象,几乎就是依照邓中夏的形象而来:英俊、潇洒、活泼、坚强,充满激情……
北大红楼诞生之后的校园内,一座并不大的两层建筑,就是图书馆。这座现在看起来很平常的房子,我原来工作的单位——《中国作家》杂志社与它距离仅有30多米,当时它已成为《红旗》杂志社图书资料室,我每天也会进去翻翻资料。然而就是在这座位于沙滩北街2号院内的小房子里,100多年前,它汇聚了后来影响中国命运的诸多伟大人物。邓中夏和后来当了每月拿8块大洋薪水的临时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经常在此探讨他们共同的导师李大钊给引领的“如何走俄国人的路”等问题。
1919年1月1日,北大校园内的学生们高举着一本名为《国民》的杂志,争相传阅着,那封面上一位对未来饱含希望的青年凝神沉思、眺望远方的形象,是青年徐悲鸿照着3个多月前在由邓中夏、许德珩发起的一个近似全国性的学生救国会上邓中夏激情演讲时的样子所绘的画。那封面上的青年的精神状态,正是“五四”运动前夜的中国青年的形象,也是邓中夏作为那个时候的中国青年领袖的形象。《国民》杂志便是他和学生救国会的同学们一起创办的第一份爱国杂志。
风暴的前夜,是呐喊的疾书。邓中夏在1919年2月至4月的3个月时间里,为出版的3期《国民》杂志撰写了8篇文章。他以大量事实、犀利笔锋,向全国人民系统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收买北洋军阀、控制我国军事和财政大权、侵占我国领土的罪行,为北大进步学生和广大爱国人士认清形势、觉悟革命,做了舆论准备。而在这个时间里,邓中夏作为主要发起者,他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这是邓中夏从毛泽东那里学到的经验,即“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用他们当时的话说,这是面对民族危亡之势而采取的第一个“直接行动”。P3-5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