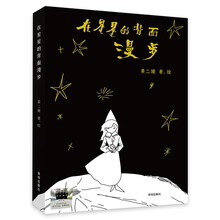村上笔下的人生最后24小时
假如人生只剩24小时,假如你我将在24小时后从这个桃红柳绿莺歌燕舞的世界上消失,那么你想做什么呢?这里说的当然不是卧病在床昏迷不醒的24小时,而是活蹦乱跳能做一切好事也能干所有坏事状态下的24小时——你打算如何度过这宝贝得不得了的24小时?
忽然冒出如此荒诞而又痛切的念头,是因为最近为在上海出精装本而重校村上春树《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当中遇到了相关情境。那是具有某种暗示性和启示性的情境,同时含有不无英雄末路意味的悲凉和孤独感。容我概述如下以供参考。
主人公“我”是一位精通电脑技术的35岁男士。由于无比复杂的原因,他的人生只剩下24小时。跨度大约是10月2日3p。m。—10月3日3p。m。。季节自然是秋天。不知何故,一个即将走到生命尽头之人却对天气十分关注,几个比喻极见特色。例如,晴:“天空晴得如被尖刀深深剜开一般深邃而透彻”,晴得“竟如今晨刚刚生成一般”,晴得“仿佛是不容任何人怀疑的绝对观念”。并且感叹“作为结束人生的最后一天,场景似乎不错”。
实际他最后24小时的人生场景也似乎不错,至少尽情饱餐了一顿,做爱也做得相当尽兴。同一个胖女孩从地下“冷酷仙境”逃到地面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打过交道的图书馆女孩打电话,约定当天傍晚6∶00一起吃意大利风味餐。女孩是“胃扩张”,他饿得“螺丝钉好像都能吃进去”,两人旗鼓相当,顿时吃得天昏地暗。生牡蛎、意式牛肝酱、炖墨鱼、奶油茄瓜、醋渍公鱼、巴旦豆焖鲈鱼、菠菜色拉,主食有意面、通心粉、蘑菇饭和意式番茄炒饭。加之男侍应生“以御用接骨医为皇太子校正脱臼的姿势毕恭毕敬地拔下葡萄酒瓶软木塞斟酒入杯”,结果所有吃喝一扫而光。之后又去女孩家受用冷冻比萨饼和帝王牌威士忌。吃罢淋浴上床,三次大动干戈。干罢一起裹着毛毯听平·克劳斯贝的唱片,“心情畅快至极”。
翌日晴空万里,他同女孩开车去公园——“星期一早上的公园犹如飞机全部起飞后的航空母舰甲板一般空旷而静谧”——歪在草坪上喝冰凉冰凉的易拉罐啤酒,谈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女孩走后,他继续喝啤酒。当生存时间仅剩一小时多一点点的时候,他从钱夹里抽出两张信用卡烧了——两张现金支票昨天已经折成四折扔进烟灰缸——“我首先烧的是美国运通卡,继而把维萨卡也烧了。信用卡怡然自得地在烟灰缸中化为灰烬。我很想把保罗·斯图尔特牌领带也付之一炬,但想了想作罢,一来过于惹人注目,二来实在多此一举。”最后,他把车开到港口空无人影的仓库旁,在鲍勃·迪伦唱的《骤雨》声中进入沉沉的梦乡……24小时至此结束。
放下书,我不由得返回本文开头那个假定:假如自己的人生只剩24小时,自己会做什么呢?能效法上面的主人公吗?基本不大可能。作为人生压轴戏诚然声情并茂可圈可点,但问题首先是年龄不同。他35岁,我则至少要把这两个数字颠倒过来。有哪个图书馆女孩——尽管我平生最爱图书馆——肯同一个半大老头儿吃哪家子意大利风味餐呢?至于餐后去女孩住处共度良宵,更是痴心妄想。其次,身份不同。小说主人公是自由职业者,IC个体户。我则有单位有组织有领导,而且是据说多少名声在外的大学教授。倘在人生最后关头弄出桃色新闻,来个晚节不保,一世英名从此休矣。这可使不得,万万使不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现实不可能由心情说了算。那么此外呢?扔存款折烧信用卡?这也绝无可能。人家是金牌王老五,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身外之物留下也无用。我则是有老婆孩子之人。再说那东西也不在我身上,想烧也找不到。领带?领带倒是偶尔系在脖子上,可是把领带付之一炬又有什么可“酷”的呢?“一来过于惹人注目,二来实在多此一举”,信哉斯言。
思来想去,能效法主人公的只有两条:一是欣赏万里无云的晴空,二是躺在公园草坪上喝啤酒。非我自吹,我对万里晴空的鉴赏和描写绝对不在小说主人公或村上君之下。啤酒虽然喝不过他(他喝了六罐!),但喝啤酒这一行为本身并无差别。
不过,当务之急是必须把《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最后几页校完,两个半小时差不多。再往下,作为补偿我想领老婆孩子外出旅游。问题是21。5个小时能去哪里呢?去意大利吃意式番茄炒饭倒是不赖……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