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克服身体羞耻感:我的来访者以及我本身
朱迪思·拉斯琦·莱彬纳,哲学博士
…………
身为女人的治疗师
在持续很长时间而且充满着欢乐的感恩节晚餐之后,几位住在郊外的亲戚要求看看我正在编辑的一盘关于女性身体意象问题和进食障碍的发展和治疗的录像带。我感到得意,并且多多少少有点满足于奉承,我同意了。这盘录像带包含了从新闻节目、谈话节目和我过去几年主持的研讨会中摘录的选段。当大伙散去以后,我意识到我感到心神不宁,情绪有些低落。我让他们觉得乏味了?我纳闷着。他们真的想看这盘录像带吗?我将这些念头对一个朋友说了。最后,经过详细谈论,我们不再讨论这件事了。但是我仍然感到不自在。
后来,他又对我说道:“你没注意吗?在录像带上,你在讨论女人如何因为她们的外表而被评头论足——女人形成厌食症和贪食症是为了感到强大有力;女人之所以痴迷于节食、减肥、保持完美体型,是因为从内心里,她们感到缺失和空虚。你在谈论帮助条理不清的来访者们建立一种内在的同一性,立足于她们真正的需求和意愿,而不是着重于她们的外表……但是没有人过多关注你在谈论什么……相反,每一个人都在谈论你在录像上看起来怎么样。”
突然,整个场景在我眼前浮现:我的三个姑妈、我母亲和几个各种各样的亲戚,围在我的书房里,都在看着录像。
评论首先集中于我的头发:
长度:长还是短?
而后:烫过还是没烫过?
然后,颜色:深红还是浅红?
棕色,再加上突出部分红色是不是更好?
朱迪染成金发看起来怎么样?乔安娜姑妈问道。
关于我的衣服:
那是一件衬衫还是披巾?
你在哪里弄到那件粉色夹克的?
现在谁还穿粉色的?
你为什么不穿一套黑色套装?我母亲问我。黑色要流行得多!
最后,关于我的体态:
亲爱的朱迪,我觉得你现在看上去比在电视上胖一些。
不,不是的——她现在看上去瘦一些!
那是因为电视让任何人都看上去胖一些。谢天谢地,你看上去没有录像上那么胖!你现在瘦多了!
带着厌倦之感,我意识到我的朋友是对的。我原以为这盘录像带会让她们对我的工作产生兴趣,但是最引人注意的是我看上去怎么样。关注的焦点从我思想的展现转移到了我外表的展现,从我的内在转移到了外在,从我的心灵转移到了我的身体。而且这种转移发生得如此迅速,以至于我都没有意识到。
我的浑然不觉使我大为惊讶。我对我的工作的自豪感被放到了一边,相反,我感到好像有人在我的内衣秀中将我当场捉住一样。而且当我想到这一点时,我意识到,那一刻所发生的事在我的生活中如此频繁地发生,以至于我又一次与之擦肩而过。慢慢地,我意识到,我在办公室里日复一日所看到和鉴别出的那个过程,那个对真实可信的自我意识的发展造成了破坏的过程,在我自己的生活中竟也发生在我身上。而且它的出现是如此自然而然,以至于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这个事件使我注意到,我的力量感是多么容易被侵蚀,不安全感和羞耻感是多么容易被激起,以及我是多么容易失去我的发言权。在即将获取赞誉和权威的边缘,围在那个房间里的女人们之间联系的纽带,却仍然是女性历来赖以维系相互之间联系的东西——外表。它使我注意到了我和我的厌食症与贪食症来访者之间的联系,因为我也被影响她们的那种同样的文化价值观所影响——那就是,外表是很重要的。
我终于意识到,真正让我心烦意乱的是,我认识到我的身体使我分心了,使我遭到了挫折,出卖了我。我感到被贬低了,被轻视了,感到自己不够格:先是关于我的头发,最后是关于我的身体;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萎靡不振、压抑不安的感受席卷而来。我失去了重心,我受到了压制。
在我琢磨这件事的时候,慢慢地,我的来访者们的面容浮现在我面前:
首先,奥德丽,今年22岁,“忘记”告诉我们的贪食症小组她拿到了法学院成绩评定,她荣列全班最顶尖的10%。其次,吉妮,她不想让丈夫知道她新近升职加薪后,薪水是他的两倍。最后,兰蒂说,她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在班里做个最瘦的女孩比做个最聪明的女孩让人感觉更好。即使她知道答案,她也常常不举手。这最终使她开始感到恼火。“聪明伶俐使我感到害怕,”她说,“但是当我知道答案时却不说出来,这很荒谬!”我能理解吗?她很担心。我绝对相信她有足够的理由保持缄默。那天晚上,她梦见自己以优异成绩毕业,却没人参加她的毕业典礼。
…………
第十四章 镜子中的裂纹:当精神科医生为医生及其家人提供治疗
迈克尔?F.迈尔斯,医学博士
…………
在我的私人医务所中,我既是个人治疗师又是专攻婚姻和离婚治疗的专家,有机会治疗大量遭受精神疾病折磨的医学学生、医生以及他们的家人。这成了一种特殊条件——因为当今的医生们所面临的那些生理上的和社会心理上的很多弱点,我也身在其中。能够帮助医学领域的人们重新感觉良好并再次发挥最大作用,这令我感到欣慰。但是这种工作也会深深地触到我的痛处,并激起大量烦扰不安的情绪反应。
在这种背景下,继之而来的是我作为医生们的精神科医生的工作所特有的那些感受、反思和洞见。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已经为大约500名前来找我咨询的医学学生和医生们提供了服务。他们的问题形形色色,既有重大精神疾患(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复发性情感障碍、失智症),也有比较轻微的顾虑,比如适应障碍、性功能失调和生活各阶段的问题,包括很多人对人际关系、婚姻和离婚的担忧。然而,潜藏在这些诊断类别之下的,或者说从中产生的,是医生们很多痛苦的情感冲突(例如,因病休假而产生的负疚感,依赖镇静剂而产生的羞耻感,对感染AIDS的焦虑感,婚姻走到尽头的失败感)。所有的治疗师都知道那些精神病学标签,而冷冰冰的诊断类别并不能够触及患者内心所遭受的困扰。下面是一些触动治疗师心灵的“素材”。
震惊
震惊是很多精神科医生不常感受到的一种情绪反应,尤其是随着他们年龄渐长并且经验日渐丰富。他们往往会感觉到“我早就见识过了”。但是我作为一名医生的精神科医生,确实不止一次地感受到了这种情绪,尽管我渐渐变得经验老到、身经百战。这里有一个例子:
当A医生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问我愿不愿接收他作为患者的时候,我起初很犹豫。为什么?有三个原因。首先,我们在同一所教学医院担任临床教学任务(尽管在不同的科室),并且都在一个AIDS政策委员会任职。其次,我们的妻子是朋友,尽管我们两对夫妻从来没有一起参加过社交活动。再次,我们的孩子们通过各种体育运动队而相互认识。我本想对A医生敷衍了事,但是他打消了我的想法,他在电话里说道:“我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打这个电话——承认我需要帮助很令人尴尬——我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打给你的,因为我曾经见过你,对你了解一点点,而且很尊重你——胜过了这里的绝大多数精神科医生和我个人所了解的其他人。”奉承归奉承,我还是决定那个星期稍后一些和A医生会面。
因为我通过妻子了解到A医生的父亲最近刚刚去世,而且这对他来说非常难以承受,所以我以为他打电话给我就是为了这个。错!他初次造访开场就说道:“谢谢你答应为我诊治。让我直说了吧。我不爱萨拉。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爱过她。大约两年前我开始与我的秘书相爱并开始约会。现在她已经离开了她丈夫,而我也计划鼓起勇气告诉萨拉以后尽快与她离婚。莫尼卡和我打算一起生活。我知道你做了很多婚姻和离婚方面的工作。你能帮忙吗?”
出于我先前对他的婚姻的了解和错误假设,当A医生告诉我他来看我的原因时,我被惊呆了。假如他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人,我倒不会感到震惊。同情会有的,但是震惊不可能。A医生在第一次造访的时候是如此的紧张和专注自我,我认为我的震惊他没有看出来。就算他看出来了,他也什么都没说。假如他说起来的话,我会承认我的惊讶,给他做出简短的解释,然后继续进行评估。我发现,在初次会面以后,我作为他的治疗师不再那么窘迫了。我能够恢复往常的专业风范,并为他提供关怀、支持、建议和指导。当他向他妻子表露离婚的计划时,他告诉她自己咨询了一位精神科医生,但是没有告诉她自己去看的是谁。我继续单独约见他,并推荐了一位治疗师,是他们两人都不认识的一位社会工作者,以便让他们两人接受离婚治疗。
…………
对家人的忧虑
作为心理健康专业人士,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去遵守行为规范,并且注重医患关系的界限。但是,当精神科医生诊治他们的生活圈子或者工作圈子里的医生(或他们心爱的人)的时候,其他因素往往会产生干扰。其中之一就是某些医学领域的封闭性和狭小性。有时候,职业和家庭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松散的。
当我应邀为科琳治疗进食障碍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对她的治疗工作我会感到如此不安。她当时21岁,她的父母都是医生。我没有违反传统的规则(也就是说,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她,而且与她父母也只是在一次晚会上被人简短地引荐了一下)。我和他们没有先前存在的或者正在发生的关系。我所不知道的是科琳和我时年21岁的女儿有一个共同点——同一个男朋友加思。他是我女儿的第一个“真正的男朋友”,是在我女儿从17岁到18岁那段时间。一年以后,他成了科琳的男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维持了大约一年半。大约在科琳成为我的患者之前的六个月,他们之间的关系破裂了。
在将科琳送入医院治疗并且帮助她度过了严重的体重下降和抑郁危机以后,我开始对她进行心理治疗,探讨一些导致她患病的动因。在一次会谈的时候,她谈起了她和加思的关系以及她对他的愤怒。她不停地描述他是多么地暴虐——言词方面、情绪方面、肢体方面以及性的方面。他常常羞辱她,当他生气的时候就叫她“笨蛋”,咒骂她,并且指责她对他“不忠”。他常常与她约会却不露面。他会答应打电话给她却又“忘记”。有两次,他打了她——一次是他不喜欢她的穿着而她拒绝更换——还有一次是他觉得她在一次晚会上与他最好的朋友聊得时间太长了。他还强奸了她一次,当时她来月经了,不想做爱。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一切——包括下周要为她治疗盆腔炎的家庭医生。
对于一名治疗师,听患者讲述虐待经历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但是这一次与众不同,对我来说艰难得多。科琳所描述的,是那个我原以为我很了解并且真心喜欢的年轻人吗?那个彬彬有礼,尊重我的女儿(我以为)、我妻子和我的人?这就是那个我原本以为,假如我女儿和他晚几年相遇的话,会成为非常棒的女婿的人?我女儿与男性相处的时候,真的像表面看上去那么自信那么安全吗?突然之间我感到疑虑重重,心中充满了身为父亲的担忧。
这个小插曲表明了从事心理治疗的一种令人痛苦的现实——医患承诺的伦理约束力。我不能够探寻我女儿和加思之间的关系。我不能向她透露我在心理治疗过程中听到的一切。我不能够告诉她科琳是我的患者。我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这些信息,并且希望我女儿和加思之间发生的事不像可怜的科琳所经历的那样。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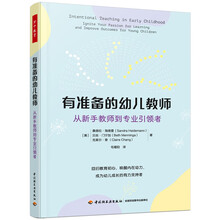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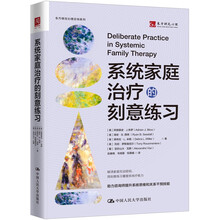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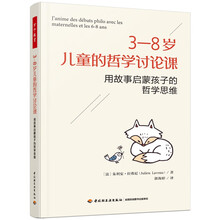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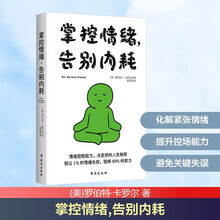



——迈克尔?B.萨斯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