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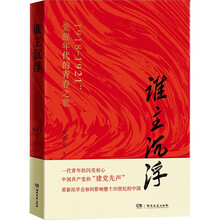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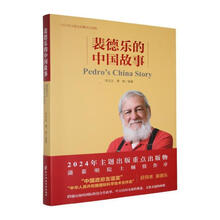






关于北朝经学的研究专著,迄今不多,本书之问世,可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进一大步。
经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成见以为,隋唐的一统在政治军事上是北方人征服了南方,在学术文化上却是南学征服北方。然而,本书作者却独具慧眼,修正了以往学界的共识,认为这一时期是以北方经学为主,而不是以南方经学为主。
《北朝经学史》详论北朝经学的起源、流派、学官制度、争论历程及其影响,对于中原少数部族政权的汉化、平城拓跋氏与中原士族的关联,以及孔颖达学派的崛起,无不一一考辨和论述。对于北魏时期的河北经学、宗教制度和学官系统,都有新见。对于北魏的政治改革,作者纳入经学的视野,做了饶有兴味的评议。对于北周的河西学者、关中学者与流亡名族学者的聚集,也各有专论。故而,本书观点较为新颖,水准较高,内容也较为完善,是一本难得的佳作。
乱世时期,经学之延续如丝缕,但始终未曾彻底灭绝,它体现的是传经之人的坚韧不拔和绍述微学的精神。有斯人,斯有经学。
《北朝经学史》融合经学史研究与政治局势、社会变迁等宏观视野,深入考察北朝经学史上学者群体的命运际遇、地缘背景和社会阶层的流动途径,从而在一种“图景”式的叙述中,揭示乱世中不为后人所知的“沉默”学术活动,梳理经学风貌的变迁特征及主导因素,凸显传经之人的个人命运,展示动荡时期政治事件和个人命运相互激荡的诸多学术光影。
北魏晚期官学与“河阴之变”
元宏是北魏诸帝中对儒学教育最为热心的君主,特别是其迁都洛阳后,不仅新建国学和太学,而且还增设四门小学。不过,仔细考察这一时期中央官学的具体情形,我们不难看出北魏洛阳时代中央官学的衰微颓败甚至名存实亡已是无法掩盖的事实。在元宏时期,曾担任国子祭酒的郑道昭在奏议中提到:“今国子学堂房粗置,弦诵阙尔。”意即迁都洛阳之后,虽然新建了国学房舍,但并没有履行教化之责,所以听不到诵读弦歌之声。在元恪即位之初,郑道昭再次上表,请求颁布学令,但未获允准。从这一奏议中,我们可侧见元宏迁都洛阳之后的整个官学体系,实际上已徒有虚名。其文如下:
澄等依旨,置四门博士四十人,其国子博士、太学博士及国子助教,宿已简置。伏寻先旨,意在速就,但军国多事,未遑营立。自尔迄今,垂将一纪,学官凋落,四术寝废。遂使硕儒耆德,卷经而不谈;俗学后生,遗本而逐末。
郑道昭所描述的情形,主要是针对元宏迁都洛阳将近十二年后的官学现状,从中不难看出其时北魏中央官学处于“学官凋落”、“四术寝废”的名存实亡状态。更为严重的是,平城时期尚能维持形式的国子学机构,也没有任何生源。根据《魏书?儒林传》的记载,自此之后,北魏在正光二年(公元521年)、永熙(公元532—534年)时期曾两次分别置立国子生三十六人和七十二人,但这些都只是昙花一现的点缀而已。
当然,北魏晚期官学的颓败,对于以诗礼传家的世族名门而言,并不是致命性的,它只是表明北魏官方并不掌握学术传承的主导权而已。而真正导致北朝经学传承主体发生巨变的,是魏末“河阴之变”这一巨祸,这从根本上使得名族经学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变得脆弱不堪,因此,我们有必要简单说明一下“河阴之变”的基本情形。
迁都洛阳后,拓跋氏统治的重心便逐渐由黄河以北的草原地域向黄河以南的农业区域转移。特别是拓跋氏本身在迁都洛阳之后的迅速汉化,更使得左右北方政局的主导力量无形中又转移至还保留有部族强大武装的北方少数民族之手。北魏末年,原本为了防范北方少数部族入侵而设置的六个兵镇,便首先以镇兵暴乱的形式昭示了这种主导权转移序幕的拉开。动荡时代来临之后,部落酋帅出身的军事贵族尔朱荣便俨然成为问鼎中原的新霸主,或许是为了全面控制北魏洛阳朝政,他在河阴屠杀了当时在朝的王公卿士一千三百余人,这就是发生于武泰元年(公元528年)的“河阴之变”。我们可以想象,这对于北方那些诗礼传家的名门世族的打击,当是极为沉重的。
在“河阴之变”后不久,北魏官方仍举行了最后一次隆重的儒学讲经盛会,即永熙(公元532—534年)时期在显阳殿诏令祭酒刘讲《孝经》,黄门李郁说《礼记》,中书舍人卢景宣讲《大戴礼记?夏小正》篇。上述诸人,刘出自彭城刘氏之后,是名儒刘芳之子;李郁出于赵郡李氏,是北魏名臣李孝伯之孙;卢景宣则是出自北朝一流名族范阳卢氏的杰出学者。这些名族学者在“河阴之变”后的讲经活动,与其说表明名族儒学并未受到河阴巨祸和兵灾的灭绝性摧毁,倒不如说是名族儒学在退出历史主流舞台之前的最后一次集体出场,因为北魏中晚期“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的情形,表明文化传统深厚之地的士庶学者已经成了经学传承的主体。此种转折,往往历时漫长而不为人留意,但其深远的影响,不能不特别加以指出。
……
关于北朝经学的研究专著,迄今不多,此书之问世,或可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进一大步,使关心经学历史的学人增加了一部新颖的、高水准的、较完善的参考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葆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