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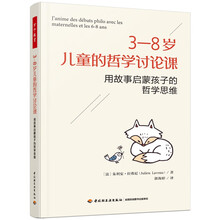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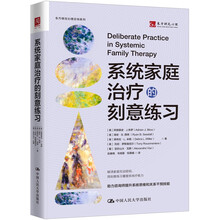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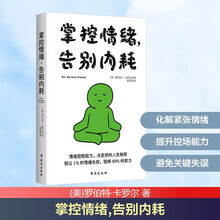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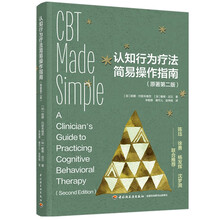

这是一本不寻常的书,它所描述的却是一个寻常的过程:谈话―倾听―理解。这里有金玉良言,也有动人的故事,能教给我们一种新的观照。作者巧妙地绘制了心理分析师的自画像,也向读者展示了咨询室里所发生的一切。相信无论是需要咨询,还是提供咨询的人,都能从中获得启示。
我们怎么会被一个无法讲述的故事所掌控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一个让我震惊的病人的故事。
我刚开始当精神分析师的时候,在汉普斯特德(Hampstead)租了一个很小的咨询室,位于名为“菲茨约翰斯大街”(FitzJohns Avenue)的宽阔林荫道上。那里毗邻好几家知名的精神分析诊所,距离弗洛伊德博物馆步行就几分钟。在这条街的南端,耸立着一座大型的弗洛伊德青铜像。
我的咨询室很安静,也空荡荡的。那里有一张书桌,仅够在上面写写字条或者整理一下每个月的账单,没有书架和文件。这个房间不是用来读书或者搞研究的。和大多数咨询室里面一样,摆放的沙发不是那种躺椅,而是一个配了深色罩子的坚固单人床。床头有一个天鹅绒垫子,上面有一块白色的亚麻手绢,不同病人之间我会更换一下。把咨询室租给我的精神分析师多年以前在墙壁上挂了一个非洲民间艺术品。她仍在上午使用这个房间,而我则在下午使用它。因为这个原因,咨询室
没有个人风格,甚至有些禁欲的味道。
我还在波特曼诊所(Portman Clinic)兼职,那是一家法医门诊部。一般说来,转介到波特曼诊所的病人都触犯过法律;其中有些人是暴力犯罪或性犯罪。我见过各个年龄段的病人,写过相当多的法庭报告。与此同时,我正在筹建自己的私人诊所。我计划保留上午的时间用于门诊的工作;下午我希望去见自己的病人,他们的问题可能不太极端或者紧迫。
结果,我自己最初的那些病人也十分“难伺候”。现在回头看看,我发现最初这些个案很棘手有许多原因。一定程度上是我自己缺乏经验。我觉得,认识到人们彼此是多么的不同,需要花些时间;我当然也得花时间。有些资深的精神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师试图帮助我开业,我接收了许多他们的转介,但是这样可能并没有什么帮助。医生们常常将他们自己不想见或者别无他处可去的病人转介给新任咨询师。所以,那时候我很挣扎。
A小姐,一位20岁的大学生。尽管曾经评估过她的精神分析师描述A小姐“正在经受一阵阵无法控制的哭泣、抑郁和一无是处感”,她还是表现得像一个开朗的年轻女性,坚持认为她不需要治疗。然而,经过一段时间,我了解到她过去暴食并且经常冲动地自残。由于她只是偶尔参加治疗,前两位咨询师已经放弃了见她。
B教授,一位40岁的研究型科学家,已婚并且育有两个孩子。他那时候被指控剽窃了竞争对手的工作。大学校长将这件事交给纪律委员会。如果他被认定有罪,会给他机会让他悄然离职。B教授告诉我,这种可能性很大。他的医生让他服用抗抑郁药物,并让我见他进行精神分析。B教授在狂热的胜利(例如,在纪律委员会嘲讽同事)和极度的沮丧之间摇摆不定。
C夫人,拥有一家小餐馆并且和丈夫一起经营;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需要帮助是因为她感到焦虑并且会躁狂发作。在我们最初的会面中,她说她“发现很难诚实地建立关系”,但是仅在治疗的几个月之后她告诉我,她和孩子的保姆有一腿。那个女人在过去的七年里一直为他们家工作,从C夫人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开始。当时,C夫人正在偷偷努力怀孕,完全不顾与丈夫的约定,因为她不能忍受“失去保姆”的这个想法。
我最初的几个病人中还有一个名叫彼得的年轻男子。他当时正在附近的一家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我们见面的3个月前,彼得躲在当地一家教堂的储物间里试图自杀。他先吞服了大量不同的药物,然后割了腕。他还用一把小刀扎入自己的脖子、胸膛和手臂。一位清洁工发现了他。虽然清洁工吓坏了,但是在等待救护车的时候一直抱着他。“这是谁干的?”,她问他。“告诉我,是谁这样对你的?”
医院里会诊的精神科医生问我,是否愿意每周五次会见彼得进行精神分析。她感觉,日常心理治疗加上每周去她那里复诊,是彼得康复、回到未婚妻身边以及重返工作的最佳方案。
彼得时年27岁,职业是一名建筑工程师。住院以前,他和未婚妻在伦敦郊外买了一套一居室的公寓。他的工作很艰难并且缺钱,但是这两点似乎都不能解释他为什么会伤害自己。我的这部分工作就是和彼得一起找出他企图自杀的原因。如果我们不能分析出怂恿他伤害自己的原因,那么有理由认为这种状况将会再次发生。
彼得又高又瘦,但是他把自己弄得和那些抑郁的人一样,弯腰驼背,耷拉着脑袋。他的神情也很沮丧,说话欲言又止,与人少有眼神接触。一旦躺在沙发床上,他几乎一动不动。
彼得出席了所有的治疗,并且几乎从没迟到过。几个月以后,他出院了并且能够回归到他原来的生活。但是渐渐地,在我们的治疗中,我感觉他消失到一个我找不到的地方去了,更别提理解他了。“你已经沉默了很长时间。你能告诉我你一直都在想什么吗?”在一次治疗中我这样问道。
“在德文郡的一个假期,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子”,他回答。
停了很长一会儿。能再跟我说说吗?我问他。他说,他并没有在想什么特别的事情,他只是想自己待一会儿。
我有种想法——他想要远离我、在分析中开小差,于是我把这种想法告诉了他。“可能是吧”,他回答道。
好像彼得在努力保护自己远离我的侵扰,好像他在遵守分析的规则,比如说,准时赴约、回答我的问题,但是采用的这种方式像是为了阻止我们之间任何有意义联结的建立。他似乎对我们的谈话心不在焉。
不过,我了解到彼得有交朋友的经历,后来中断了与他们之间的联系。他的职业生活也是如此。他原来一直默默地做着他的工作,后来突然与老板吵了一架就辞职了。这种事情发生过好几次。我试图用这些信息向彼得表明,他似乎有两种心理定位——默许或爆发。他似乎同意这种说法,但是我一点都没感觉到这种说法让他感觉有什么意义。而且不久,这种模式在分析中又遇到了。彼得起初与我和睦相处,后来变成不断地嘲讽我。经历了特别闹腾的一周之后,彼得停止了他的治疗。我写信给他,建议他跟我谈谈他要结束治疗的决定,但是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我联系了他的精神科医生,她告诉我彼得也没有去见她。
两个月过后,一封来自彼得未婚妻的信告诉我,他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解释说,在彼得去世之前的那个月里,他已经渐渐变得不安和退缩。一个星期以前,家人在西伦敦火葬场(West London Crematorium)举行了一个葬礼。她写道,她很感激我努力帮助过他。我写了一封哀悼信给她,然后通知了彼得的精神科医生。
我早就料到彼得是一位高危患者。在我接待他的时候,我寻求了督导师的帮助。他是一位有经验的精神分析师,曾经写过一本关于自杀的书。他反复多次向我指出,彼得似乎在许多方面都将死亡理想化了。那时,我又去见他,担心自己漏掉了什么。我的督导师试图安慰我。“谁知道呢?”他说,“和你一起分析可能已经让他在过去的一年里远离了自杀。”然而,彼得的死仍然极大地困扰了我。当然,我知道我们都有自我毁灭的能力,但是无论如何我始终有一种信仰,生存欲望更有力量。那时,正好相反,我感觉到了这种信仰的脆弱。彼得的自杀让我感到,生与死的较量不相上下、势均力敌。
六个月之后,我的答录机收到一条留言。我听到清晰的公用电话声——嘟嘟嘟,硬币落下;然后是彼得的声音:“是我。我没有死。我想知道我能否过去和你谈谈。我用的还是原来的号码。”
听到彼得声音的瞬间,我感觉眩晕、迷糊。好一会儿,我试图说服自己可能是答录机出了故障,我正在听一条没被洗掉的彼得的旧留言。接着,我笑了,出于愤怒,源于解脱。因为我被震惊了。
那天晚上,我写信给会诊的精神科医生告诉她彼得没有死的时候,我做了许多人生气时都会做的事——我开了个玩笑。“除非地狱里有付费电话”,我写道,“彼得还活着。今天早上他在我的答录机上留言,要求预约。”
随后的那个星期彼得来见了我。他用事实陈述的方式告诉我,是他写信告诉我他死了,而不是他的未婚妻。他还拦截了我的哀悼信。“那封信很感人”,他说。
“天哪,太有趣了”,我的督导师说。“真是奇怪,这并不经常发生。想想那些说过‘我自杀以后你会很难过’的青少年,你会发现他们当中更多的人都不会那样做。”我们决定,如果我感觉彼得真是准备郑重承诺遵守治疗规则的话,我只要再次接待他就好了。
几次会面之后,彼得和我一致同意重新开始他的疗程。最终,他的消失和回归证明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呈现了我们从未理解的东西——他需要震撼其他人。
在随后的治疗中,这种需要慢慢变得清晰起来。彼得喜欢去想在他突然辞职或终结友谊的时候由他引发的那种痛苦。他已经把分析搞砸了两次,第一次是他退出了治疗,第二次是他捏造了自杀。在分析的第一阶段,我没能发现是什么将彼得与粗暴伤害他人联结在一起。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彼得的父母在他两岁的时候就离了婚,之后不久他母亲就再婚了。在分析的第二阶段,彼得找到了他的生父,并且和他母亲坦诚地谈了谈。他发现他母亲过去一直与后来成为他继父的男人有染,而且他的父母都严重酗酒。他还发现,他出生后头两年的经历与别人告诉他的情况完全不同。他的母亲和父亲都承认,他刚出生的时候,他们根本无法应付,还曾经对他拳脚相加。
彼得告诉我,他的父亲根本不记得多少,只说那是一段糟糕的、不愉快的时光,一段不幸福的婚姻。“我的母亲哭了,她不停地说对不起”,彼得说。“我出生的时候她只有20岁,没有人帮她。她说,有时候她感觉自己就要疯了。”
母亲的忏悔给了彼得一些宽慰。凡是那些他能够记得的,他过去一直都感觉恐惧。他告诉我,知道自己受到了什么惊吓是有帮助的。对于一个小孩儿来说,暴力是一种压倒性的、无法控制的可怕经历,它的情感作用可能会持续一生。创伤被内化了,它就是在无人同情时掌控我们的东西。那么,为什么彼得会切断那些与他亲近的人际关系呢?
彼得的行为清晰表明,他不允许自己感觉很弱小。对于他来说,依赖是危险的。彼得的故事可以被总结成一句话,“我是创伤的制造者,不再是受伤的小婴儿。”但是,彼得也会对“打开自己”有所反弹。他在教堂自残,正是由于相同的原因。就像他告诉我的那样,“我心想,你这个可怜的爱哭的小屁孩,我可以这样对你而你却不能阻止我。”
我相信,所有人都试图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来赋予生命意义,但是彼得却被一个他无法能讲述的故事掌控着。他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而不是用话语。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彼得的行为就是他用来与我对话的语言。彼得讲他的故事是通过让我感受他过去的样子——愤怒、困惑以及震惊,那一定是他小时候感受到的。
作家卡伦·布利克森(Karen Blixen)说过,“如果你把悲伤放入一个故事,或者讲述一个关于悲伤的故事,那么悲伤就会产生。”但是,如果一个人无法讲述他的悲伤经历,会怎样呢?如果把他的故事告诉他,又会怎样呢?
经验告诉我,童年会留给我们诸如此类的经历,留给我们永远无法讲述的故事,因为没人告诉我们该怎么讲。尽管我们无法找到一种讲述自己经历的方式,但是我们的经历会告诉我们——我们会梦见这些经过、出现症状或者发现自己的行为方式无法理解。
在彼得给我的答录机留言两年以后,我们一致同意结束他的精神分析。我认为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而他感觉是时候该结束了。
所有的这一切发生在许多年以前。从那以后彼得没有再要求过见面,但是我最近确实遇到了他,在电影院里。我们在大厅认出了彼此。彼得与站在他身边的女人说了些什么,然后一起走了过来。他伸出手来握手,然后把我介绍给他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