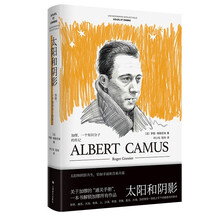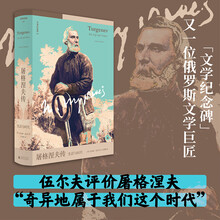江边依旧立着的古老吊脚楼,每日听着江水咿呀独唱,寂静地,沉默地迎来送往,它身上斑驳着旧日痕迹,每个角落,都写满了故事,如日光悠长。在这里,我追寻着那位勇敢女子的足迹,跋山涉水,风尘千里。只是我不曾预料,她曾生长的地方,几乎跟这座繁华的小城毫无干系。
黑胡子冲——丁玲最原始的故乡。这是个需要骑马、坐轿才能一窥真容的小村,在纷扰喧哗的红尘里,已经很难找到这样一处清幽动人的所在。草木幽深,繁花似锦,这里干净得当真如同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我想,我们是需要出来走走了。
在这个坐地日行八万里的时代,我们只要守着一台小小的电脑,仿佛就能够遨游整个世界。然而,那样的世界,是不是我们能够用手触碰,能够俯首轻闻、侧耳倾听的世界?那些快捷方便的现代化设施,是不是足以值得我们用触手可及的真实去交换呢?浸透红尘日久,我们着实需要开门推窗,亲自寻访一处能够洗净疲敝心灵、净化风尘外衣的地方。
而这个地方,有山有水有竹林,遍布绿意,美好得像是许久许久之前,哪位吟游诗人低吟浅唱的一首诗。大约也只有这样的地方,才能养育出这样一位才华出众的女子了。好比沈从文笔下的翠翠,换了湘西幽幽风水,替了湘江悠悠唱晚,哪里能孕育出那样清透伶俐的姑娘。
可惜的是,时光流逝,并不是什么都没有改变。时光的美妙也在这里,它能够改变一些事,也能够令一些事,在人心里镌刻永久。1904年,孙中山先生为他的梦想满世界奔走,而这个国家,满目疮痍,遍地硝烟。就是这一年,这个宁静小村里,一户蒋姓人家里,诞生了一个女婴。这户人家,有着几进几出的深宅大院,一切都很符合人们对富贵人家的定义。
后来这里的人们,提到那座蒋家大宅时,总不无艳羡地描述,大宅门口曾置着一方长石,这块石头被称为“下马石”,即便是知府来了也得停轿下马,步行而人。与下马石一样声名远播的还有蒋家那富丽堂皇的戏楼,据说这座戏楼,用的通通都是上好木材,更叫人瞠目结舌的是,它还用象牙和宝石以装饰辉煌。除此之外,蒋家的花园是专门请了上海的工程师精心设计的,用料是从无锡千里迢迢地水运过来的,就连他家的佃户,也专门住在蒋家另起的一条长街上。
豪门大户里的威严,自古以来是男儿支撑起来的,家族的血脉和荣光只有在男孩的身上才能够传承。丁玲的父亲,这位蒋家少爷,同样是如许期待,然而,女儿的到来,却让父亲的期望全部落空。蒋父叹息之余,将这个原本留给男儿的名字转给了自己的长女——蒋伟。
虽没有一个男儿传承血脉,父亲却给了这个孩子男儿郎的使命。他给她一个男儿郎的名字,就是将重如山的责任紧紧地附着在她的生命中。就算是后来她为自己取了“丁玲”这个名字,也始终无法摆脱宿命中沉重的责任。
蒋家是当地出了名的富户,奢华谈不上,却门楣高挺。富贵的里子往往容易滋生骄腐,除却几位远房的贫寒书生,蒋家子弟,极少不是纨绔子弟。
正如那华美的袍子上,暗生结群的虱子。
丁玲的祖母,孀居时依然年轻,她的丈夫在三十五岁时便死去。红颜福薄,她几乎是做了一辈子的寡妇,还好有儿女陪伴,可以寄望余生。
苦楚就如同花粉,散播在下一辈的宿命里。她的儿媳,大多也循着她的路子,年纪轻轻便孤身一人,领着膝下几个孩子,乏味而平静地走过人生。
好好的一次生命,却死寂如同尘埃,未及绚烂飞扬过,却早早地归于沉寂。
一代代人,在富贵里演绎着相同的人生悲欢,平静里带着些许悲哀。然而,芸芸众生里,总会有些异数。在丁玲之前,这户人家与众不同,没有走上那条老路的,只有丁玲的二伯父和一位叔叔。他们看透了荣华里的钩心斗角,奢靡里的空洞凄凉,一位将红尘早早看破,念着佛经皈依佛祖门下;另一位更加出格,干脆上山当了土匪。痛快倒是痛快了,只是偌大蒋家,在丁玲伯父和父亲相继去世后,便剩下了满门寡妇,冷清得令人忍不住要做噩梦。噩梦如蛇,在每一个昏暗的午夜里缠绕着那一道富贵的门楣,冷冷地窥视这一大家人的悲欢。
其实如果丁玲的父亲未曾死去,那她还是这个大家族中备受宠爱的小姐。闺门里的纤纤女流,闲来看花喂鸟,忙起来,也至多做些女红,绣几方罗帕或是锦囊。等到待嫁的年龄,自有父母为她寻一户门当户对的人家,尔后成婚,相夫,教子,一世安宁,操心的,也不过是些富贵里的琐事。当时的深门闺秀,莫不是如此。
她终究没能这样安稳地成长,平静地度过她的一生。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