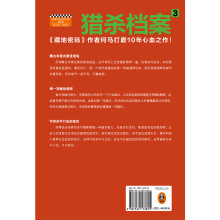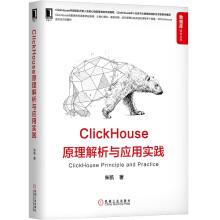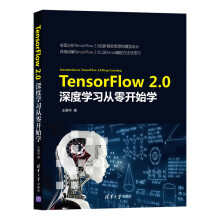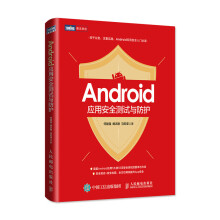《创造性破坏:好莱坞大片影响下中国式大片的发生与发展研究》:
电影《芙蓉镇》与张艺谋的《活着》都把视角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次运动给普通人和其家庭带来的悲惨命运以及他们的隐忍与抗争。与《活着》中福贵一家游离于运动的外围不同,《芙蓉镇》大胆直面了运动暴风眼中的人物,右派、走资派、革委会领导、红卫兵小将,无论是秦书田、胡玉音,或是李国香、王秋赦,他们都历经“反右”、“四清”到“文化大革命”,完整地展现了他们在这些运动中的浮生百态与起落沉浮。影片正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运动的名称有异,但所有的运动核心是一以贯之的就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最高指示引领下,以虚妄的“革命”和“进步”来切割和摧毁人性的温情与美好,将人际关系革命化、斗争化。简单说,即“整人”和“挨整”。并且,“整”的施动主体与“被整”的受动客体并非一成不变,今天的施动者在下次运动来的时候,可能会变成受动者。比如,李国香从“四清”时的革命旗手,在“文革”时被打倒在地,串联的红卫兵小将她揪出,挂上写着“破鞋”的黑牌与“黑五类”们一起游行示众,并被逼迫手脚并用,如狗爬行。
《芙蓉镇》中胡玉音、谷燕山等人的悲剧,发生在那个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时代的悲剧。但影片引起我们更多深思的是,为什么“人性”会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被扭曲、被异化,人性之恶的“潘多拉魔盒”为什么,又是怎么样被释放了出来,这到底是时代的悲剧,抑或更多是人性的悲剧?影片中对人性的洞悉和反思,将这种反思和批判升华了。李国香批斗整垮胡玉音,表层的理由是以革命正统自居的她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但深层的原因来自女人的嫉妒和其自身的性紧张。她嫉妒胡玉音的美貌、风情,特别是嫉妒胡玉音有着美满的家庭,还拥有满庚、谷燕山等人对她的情爱。革命的、性别特征一度被遮蔽的、高龄独身的李国香利用了“运动”,剥夺了胡玉音的婚姻、爱情,甚至间接威胁到胡玉音肚子里的孩子,将一个风情万种、人见人爱的“豆腐西施”打成众人避之不及的“黑五类”沦落街头扫地。在此过程中,她释放了内心的性焦虑。当然,真正的性满足还来自她与王秋赦的苟且。而黎满庚的悲剧是典型的性格悲剧。他想爱,但不敢也不能爱,想保护胡玉音,但在关键时刻为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出卖了胡。他始终处于内心各种矛盾、各种顾忌的张力与纠结之中,他是在那个时代软弱的“这一个”的典型形象。
影片中秦书田与胡玉音艰难之中孕育的爱情,是这个充斥着以人与人的斗争为主题,“人人防我,我防人人”的小镇上出现的难得的希冀与亮色,展露出虽微弱但亮眼的人性光辉。秦书田在胡玉音最痛苦的时候走近了她,相濡以沫,两人在扫街的时候还跳起了狐步,苦中作乐,将枯燥的体罚变成了享受;两人在滂沱大雨中挨批,在胡玉音就要绝望的时候,秦书田鼓励她“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最让人唏嘘的是,在李国香对他们的结婚申请嗤之以鼻,批他们是黑夫妻的时候,秦书田干脆在自家门上贴上了“两个狗男女,一对黑夫妻”这样一副对联,这是一种自谑式的乐观,因为黑夫妻毕竟也是夫妻,这是对其关系的一种变相承认。
现在来看,《芙蓉镇》的反思和批判依然有时代的局限性,体现出主创一定程度上的软弱和妥协,这主要表现在对李国香命运的最后处理。一手造成了胡玉音、秦书田、谷燕山悲剧的李国香,几经浮沉,最后依然可以与省里的中年干部结了婚,恢复了政治待遇和相应职务,而其朋党王秋赦却疯了。如此的处理当然有主创对李国香的同情,因为她在整人的同时也在挨整。但却让影片的反思性有余而批判性不够彻底,难道就是因为李国香是根正苗红的党的干部,而王只是投机的流氓无产者?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