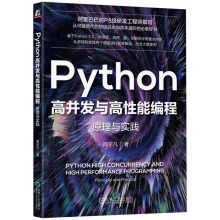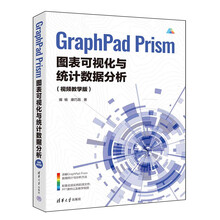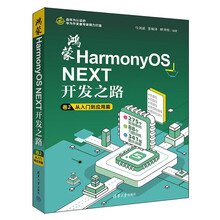住在苏州是有福气的,因为人的耳朵。苏州人的耳朵可以听到世界上最软糯的语言、最风雅的曲调。
昆曲里有一个又一个有着好听名字的曲牌,就像苏州有着一条又一条各有韵味的弄堂和巷子。而那些弄堂和巷子深处,在那些紫薇花下和垂柳之侧,有着看似平常却浸润着爱与真的艺术人家。
在那些人家里,时而一阵花香飘过,时而一阵风儿吹过,自自然然。苏州人坐在庭院里,看着从枝头坠下桂子或者花瓣飘落在池塘里,和着心底的节奏打一打板眼,再有把扇子闲闲地摇一摇,昆曲的味道自然就浮现在眼前耳畔了。
说起来,坐在群花之间听曲,是苏州人白相出来的。
苏州昆山人顾阿瑛,一个元末明初的资深文艺青年。顾阿瑛的园子里除了他爱玩的昆石之外,还有三个荷花池,其中一个引来了原本生长于天竺的并蒂莲,池底安放有孔石板,好似莲房,荷梗从石板下穿孔而出,文气斐然。
隔着种满了荷花的池塘,后来成为昆山腔宗师的顾坚,指导着顾阿瑛的声乐家班在水中戏台上,缠绵婉转地吟唱。这样的唱腔,就像雨后荷叶上滚动的水珠,骨碌骨碌,在丹田里打转。昆曲后来叫水磨调,说不定也是从这里得到的暗示。
这一说,有六百年光阴了。从元末开始,苏州园林里就有昆曲的影子了,而园林里的荷花,从小就是听着昆曲长大的。曲折亭台婉转桥,苏州的昆曲与园林,同工异曲。曲名与园名相通,曲境与园境依存,曲情和园情交融,昆曲中唱园林,园林里听昆曲,苏州人在园林里赏花、听曲、读书,曲和园,有点像这座城市的天光和水土,荷花,就是天地之间生长的清白人心。
好像从战国到明末清初,很多人都表述过同一个意思:人,天地之心。心是用来做什么的?它不是手,不是脚,人不能对天地动手动脚;人心只有一个作用,那就是悟。西方的海德格尔老兄也说过类似的话:人,需要辛劳地栖居在大地之上。这种辛劳,就是一种需要感悟的诗意。
这种诗意,大多西方人是很难体味的。莫奈画睡莲,初得了美的印象,而天才毕加索,晚年才终于明白齐白石永远站在他的前方。应该说,在思想领域,西方靠智,东方靠慧,智是一种理性,慧是一种悟性。而中国人理解,慧之根源在于心静,静了才能感悟到那种难以言表的宇宙暗物质,还有那些终极的原则。
但是,中国的慧也不是高天厚土,难以把握。吟诗、度曲、游学、打拳、做工、修炼,其实都是异曲同工的事情,都是解决悟性的方法。而在这方法之上还有世界观,你的世界观是怎么样的,才能决定你的心能不能静而生慧。
由此,我不得不感谢脚下的这块土地。这块土地深处,依然充盈着阴阳的互动;这块土地之上,依然还能奇遇千代而来的诗性符号;这块土地隐隐地还在昭示我,诗性和人生的核心价值。而昆曲就是其中最宝贝的一份指点。
我有一枚印章,是苏州一位篆刻高手为我刻的,四个字“松风度曲”。在松风下听昆曲,必定要好大王碑刻一样慷慨悲凉的北曲,像【脱布衫】、【大红袍】;而在苏州的花柳下听曲,是唐、祝、文、仇一般的风采,非【山桃红】、【步步娇】、【懒画眉】这样的曲子是不能合住这股劲的。而在苏州拙政园的荷花池畔听曲,上台的杜丽娘和陈妙常们一定要加倍着仔细,必须要有着几分原汁原味的俞派唱口才有胆气,因为这园子里走过的“拍先”太多,就连卅六鸳鸯馆下的鸳鸯们,听到不合音韵的腔调,它们也要在水中不屑地振振翅膀,一个猛子潜泳去了。
好,拉拉杂杂聊了这么多,我主要是想表露一个意思:昆曲不是一种柔美小技,也不单单是中国古典戏剧中的最高范式、戏中极品、曲中之神——这些都没错,而在我心中,昆曲格律之中正,运气吐字之松沉,曲牌结构、舞台魅力和音乐节奏之中庸圆融,都可以让人心生敬畏,不敢造次。心术不正之人,对此可以正衣冠;正直友善之人,对此可以结良伴。东方的昆曲和其他艺术不一样,它像朋友,更像是我珍惜的那些百年老宅的主人。好吧,各位读者,请随我一起,在水磨调里慢慢沉醉吧。在阵阵吴地的荷香里,我们可以像红鱼一条,隐入宫商深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