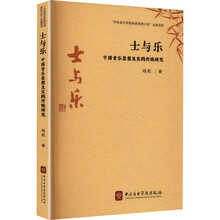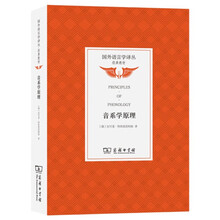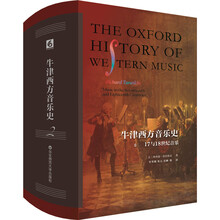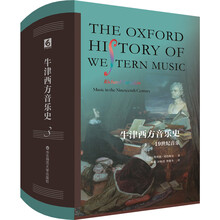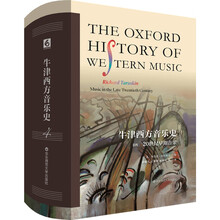他拥有统率力,无比的尊严,极佳的记忆力,丰富的经验,强烈的风格和宁静的智慧。他已经受过烈火的考验,但仍未熔化,反而闪耀出一种刺目的内在光芒。他有多重身份:音乐家,管理者,执行官,使节,心理学家,匠人,哲学家,以及可以随时发怒的人。像许多伟人一样,他出身低微;在公众眼中,他是天生的演员。就事论事,他是个自大狂,他必须是。如果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没有绝对的信任,他就什么也不是。
首先,他是个领袖。他的部下向他寻求指引。他即刻拥有了父亲的形象,伟大的赐予者,灵感的源泉,无所不知的导师。称他为伟大的道德力量也许不算过分。也许他半是神圣,他肯定在神圣的笼罩下工作(至少某种有着浪漫主义理想的学派让我们这样想)。他必须是强势人物,他越强悍,就越容易被下属称为专制。他只有伸出手,才能让人听话。他不能容忍任何异见。他的意愿,他的话语,他的每一次扫视,就是法则。
有时候他的名字是威廉·富特文格勒,有时候是阿图罗·托斯卡尼尼,有时候是弗里茨·莱纳,莱昂纳德·伯恩斯坦,亚瑟·尼基什,或者奥托·克伦佩勒。这里面没有区别。不管他叫什么,他都必须站在一群音乐家面前,指挥他们。他站在那里,因为必须有人控制一切。他要设定速度,保持节奏,保证和谐与平衡,尽力实现作曲家写在乐谱上的方方面面。从他的指挥棒,指尖,灵魂中流淌出一种高压电,击中了一百名乐手角儿,让他们收敛个人意愿,服从于集体努力。他的耳朵有一百多根隐形触须,每一根都插了电,像是控制板,将每位乐手的潜意识纳入他的掌控之下。假如某一位奏出了错误的乐句或是音符,那根触须就会抽搐。接下来就是盛怒。
他让那一百来号人乖乖听话,并用不同的方式得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弗里茨·莱纳和阿图罗·托斯卡尼尼那样的指挥擅于利用恐惧,莱纳只消眯着眼睛瞪上一眼,乐手们就会呜咽着变成一团原生质。布鲁诺·瓦尔特则有另外一套办法。他总是表达理想已经幻灭,自己有多么凄凉孤寂,乐手们几乎要号啕大哭,马上发誓不再捣乱。“先生们,先生们,”瓦尔特会用基督一般的口吻说,“用空弦拉D,莫扎特会怎么说?”莱昂纳德·伯恩斯坦则有一种发自内心、异常亲切的友爱之情,好像一个足球教练分成两半,“现在,伙计们,让我们一起奏那个乐句,让我们的弦乐部正好在拍子上进来。准备好了?一,二,……”列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在排练时声音单调,完全是公事公办,“D之前三个小节,降A应该是A,用中强演奏,在后两个小节慢慢加速。全体准备,开始。”
指挥通过乐队将音乐符号转化成有意义的声响。每位指挥对符号的解读都不同,因为他们个性不同。小孩会问“天上有多远”,而对一位指挥来说,“多快才算快?”可不是什么幼稚的问题。多快才算快?当莫扎特写下“小快板”,到底是快步还是小跑?每位指挥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他要做的就是跟随直觉,这些直觉的基础是多年的思考和学习。
指挥和他的乐团应该融为一体。如果他有知识和内在力量,就可以让乐团完全听从于自己。然而这不是一朝一夕便能成就的(除非是尼基什或莱纳那样的人物),彼此熟悉、磨合的过程往往需要好几年。但前提条件是,指挥必须优秀。一支乐队通常只要花上15分钟就知道面前的新指挥是真诚还是虚伪,是不是在例行公事。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