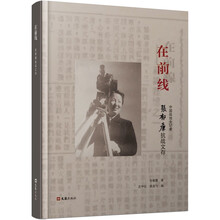舒姓在溆浦县算第一大族,有一舒二向三张四李之谣(即谓全县人口最多,文风最盛的第一推姓舒的,第二推姓向的……),通常都是聚族而居。独有我家单独世居刘家渡。五服以内的亲房都在离刘家渡上十余里的龙王江及黄茅寨住居。而我的故居又是孤立在溆水之滨,半里以内并无邻居;半里外虽有两个小村落可以守望相助,但因既非同宗,又均有一丈余深的水沟隔着,除非年节请乡酒互相访问外,平常是不大往来的;所以我自幼即少和亲族邻舍接触。虽然遇着年节的社戏也跟家里的长辈去参加,但因我曾祖及祖父均系单传,父亲虽有两兄弟,而我在幼年时仍是我家唯一的孩子,家长们自然特别重视;就是参加地方的群众集会,也是守护维谨而不使我与一般邻孩往来,所以我在幼年时代所过的生活,可以说完全是孤独生活。
我家世业农,且为佃农。在曾祖父及祖父时代都是以佃田力耕为生,故生活也很困苦。到祖父中年因我父亲及叔父长大,能代为耕种,且善于经营副业——我家之周围隙地及园场有柑、橘、桐、李、桃等各种果树,稻田除稻外兼种荞麦,沙田则种甘蔗、棉花及桑树等——家道稍可过去;但除屋场外,仍无半亩田地。只因曾祖在某时曾受人欺侮,立志要送子孙读书,所以父亲在生活万难之中也曾读过几年书,而能记得出账目,写得出书信,在我家历史上要算读书人了。我母生于我家对河徐家湾的徐姓家,无兄弟姊妹,而且当她五岁时,外祖父即逝世,外祖母因生活关系,又中道改嫁,所以我母八岁即过我家为童养媳。她处那样的时代和那样的社会,当然说不上受什么教育。但是我的外祖父天资特高,虽然只在乡间读过数年书,可是他能动笔写东西,并且教过书;只因为人爽直高傲,终于被人排挤以至于死。母亲受了他的遗传,天资很高,而豪爽有打算,对于读书人,特别重视;但因自幼即过孤女生活,故性情极孤僻而执拗。到我家后,常与祖父祖母发生争执,我父亦畏之。所以我家自我母亲成人以后,家事多由其操持,且由之而有薄田数亩。我为长孙,在习惯上应得全家的钟爱,而因我母亲的性情与对于家族的劳绩等种种关系,我在全家中更占了特殊的位置。所以我虽然是贫苦的佃农之子,但幼时在物质生活上所享受的并不弱于中产之家。
我在五岁以前,既少与他家儿童相往还,又无兄弟姊妹作伴,所以在精神生活上是很孤寂的。当时家庭中的长者虽然都很重视我,但他们都有农事上的职务,不能常常和我在一起。与我形影不离的只有母亲,所以母亲是我幼年时代的唯一教育者。
因为母亲自幼便过孤独生活,加以性情上教育上的种种关系,故对于我的期望特切:她希望我将来绝不再步祖先的后尘作胼手胝足的农夫,只馨香顶祝地向各处求神拜佛,祷祝我长大成人时作一个读书种子,得一官半职以显扬我舒家与徐家的祖先。所以小农子弟的种种生活如放牛砍柴等事,均绝对不准我参加;就是衣服行动也绝不准效邻家儿童的,而得保持斯文气派。这在她以为读书人应有读书人的态度,幼时即当养成,绝不可有牧竖村童的粗野举动。可是我生性好天然风景,对于牧童的风趣尤为醉心。每遇母亲监督稍弛的时候,便跟着叔父和长工(长年的工人)跑到田野间去替他们帮忙。对于牛尤有好感:四岁以后,总是背着母亲和牧童商议要他把我放在牛背上骑着,躲到树荫下去唱歌。每到秋季遇着摘棉、摘橘和收甘蔗、采茶子(采山茶树之子以为制油之用)——这些都是我家的农产副业——的时候,无论如何都得设法加入。而对于水与鱼的嗜好尤为特别:我家的后面与左面都为灌溉农田的水沟所围绕,而此水沟的水,又是从上流的溆水引曳而来,所以每遇到河水泛滥时,水沟也跟着高涨而有从河流中冲来的许多小鱼。祖父常在沟口张网取鱼;到秋汛时,父亲们也常携网至河中取鱼。我每遇他们取鱼的时候,总得设法跟去,为之背负鱼篓。如果鱼篓盛满,至于背负不起,用拉纤式的方法把它拖回家中,并且不许他人帮忙。回家之后,又得帮着母亲、祖母,把鱼破好洗好然后才心满意足。为着疲劳过度而睡在鱼盆的旁边,也是常有的事。所以遇着不如意的事而哭泣时,只要有人拿着网喊声捕鱼去,我就自然而然地止着哭。可是因为母亲的限制终于不会泅水,也终于不能捕鱼。不过现在回想当时与祖父父亲们捕鱼的往事,犹使我的童年的天真宛然在目。
我的幼年,因为时代和环境的限制,当然不能受现代式幼稚教育。所有的生活习惯,除了母亲的指示外,都是从“直接参加”得来的。故我幼时所受的教育影响,在人的方面自然以母亲为最大,在物的方面则以我所处的自然环境为最大。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