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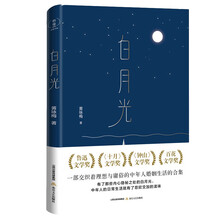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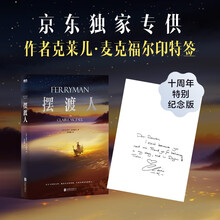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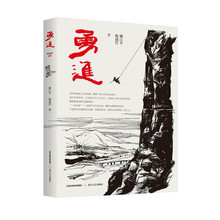




再宏大的家国史都由千百个跌宕的个人史构成
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纤细入微的情感体验
百岁老人雷高汉,一直活在鸿祯塞的影子之中。那盘踞山丘的庞大建筑的影子,既浓缩了他的饥饱冷暖,又覆盖了他的恩怨情仇,直至生命*后一刻,他才完成了和它的漫长对话。
这是一方乡土同生共死的秘史,也是百年中国恩山义海的传奇。
《塞影记》
第一章
我在网上刚查到那三个字,高速列车就到站了。
我来这个县看油菜花海,快要到了才上网查找这一带的民宿,然后给“喜鹊小栈”打了一个电话。一个女人在电话里说,出了火车站,再坐车半小时到鸿祯塞,大老远就能看见一个喜鹊窝。她说:“我的喜鹊就在那儿。”
“什么塞?”我问,“哪三个字?”
“鸿雁的鸿。”
“贞节的贞?”
“需要添衣。”
“没有这个字,”我说,“什么塞?”
她把电话挂了。
我从火车站出来,上了一辆出租车,油菜花很快就一浪一浪涌上来。不上半小时,我看见了那个喜鹊窝,被大树高高举起来。我下了车,朝喜鹊窝下面那栋小楼走过去。
这是一栋三层小楼,用石材、钢材和玻璃建成。屋基大概是垒起来的,四周砌了几尺高的石墙。邻近的小砖楼又都是两层,老远就看见它冒出半截,所以连一个招牌都没有。三楼大概是一个玻璃花房,在夕阳下亮晃晃一团。
我爬上几级石阶,不见一个人影。一排玻璃门打开了一扇,我却碰撞上了没有打开的一扇。我等着里面的人回应那一声响,一直等到火气上来。
“有人吗?喂,有人吗?”
楼上好像有一点动静,细听却又没有。
我后退几步,看见一树海棠花正开得热闹。户外的石桌石凳都很干净,我让拉杆箱立在石材地面上,就在一架秋千上坐下来。秋千吊在高大的钢架上,看不出那钢架是为什么藤蔓预备的。我刚让秋千荡起来,一个年轻女人就从石阶上冒出来。她看我一眼,从那扇打开的玻璃门进去了。我跳下地,提上拉杆箱跟进去。她只管往楼上爬,钢架撑起的玻璃楼梯无声无息。她把我领到二楼转角处,在一间屋子门口停下来。
“身份证。”她说。
我好像不是来住店,而是来向什么管理员报到的。
她看过身份证,还给我说:“我们吃什么,你吃什么。你不能上三楼,见他需要我的同意。”
“寒露!”一个女人在楼下喊,“温寒露!”
她没有答应,下楼去了。
我进了屋子,把厚厚的窗帘拉开,玻璃窗占了两面墙各一半。油菜花海就在窗外,风平浪静。我向远处望过去,长山丘后面冒出了短山丘。天色暗下来,我却已经看清,短山丘是一片庞大的建筑,只冒出来一个顶。那一片影子,就像昏昏沉沉的晚云,很快就把白天涂染成了黑夜。
两个女人在楼下高一声低一句说话,不一会儿就安静下来。
窗外有一只鸟儿一直在叫,不一会儿也歇了。我从屋里出去,看见温寒露提着饭盒上三楼去,而我还饿着肚子。看样子,三楼并不是花房,住着人。她在上面待了很久,吃两顿饭都足够了。我原想在民宿改善一下伙食,晚餐却是一碗酸菜豆腐挂面。豆腐切成颗粒,让油煎出了几面黄,那酸菜却差点让我掉了牙。我回到二楼那间屋子,刚拿起一本书,她却来敲门了。
我一手拿书,一手接过她递上的电茶壶,说:“正愁怎么泡茶呢。”
她并没有在意我的口气,问:“什么书?”
“小说。”我把电茶壶放下,双手端起书让她看封面。“《午夜之子》。”
她把目光从书上移开,说:“你是作家。”
我知道,她已经上网搜查过了。我的姓名、年龄、相貌和著作都已经在她手上捏着,她大概不用再提防我什么了。
她问:“你是来写鸿祯塞的吧?”
我已经把那三个字忘得一干二净,问:“什么塞?”
她好像受了欺负,转身就往回走。脚步声在楼梯口那儿停了,然后,响起了开门声和关门声。
我轻轻关上门。她是我在乡下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我发现,我在电脑上输出来的是“温寒露”,愣了一阵,才换上了“鸿祯塞”。图片和文字跳了出来,那是从前当地豪门建造的全封闭建筑,大概就是天黑前我看到的那一片影子。我一动念头就拖上拉杆箱出门,可不是奔什么建筑来的。我提醒自己,我计划在这个名声在外的油菜花海住上十天半月,我是来这儿写作的。
突然,我听见了喊声。
那喊声就在楼上,在一面窗上面。我走到那儿去听,喊声却又去了另一面。我赶紧换到门边,喊声果然转过来了。我听清楚了,那大概是在喊一个人。
“翠香!”
我把门打开了一道缝。喊声并不大,好像来自更高一些的空中。
“翠香!”
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苍老而清晰。
“翠香!”
夜还不深,我并不害怕,接下来那一声咳嗽却让我浑身一颤。
我慌忙把门关上了。
早上,我从二楼下来,一见温寒露就问:“楼上是谁?”
“我叫他老祖宗。”
“他今年高寿?”
“和鸿祯塞同岁。”
初见之时,温寒露把我当成了来“长寿之乡”搜集什么材料的人,不过她很快就接到电话,那个人在半路上得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她已经知道我认错了门,但没有赶我走的意思。我迷路的本事让我钻了一个空子,我却也不打算住到旁边的“喜鹊小栈”去。
我吃过早餐往外走的时候,才看见石阶分两道,弯曲的一道通向侧门,端正的一道通向正门。我在头天弯曲地爬上来,而我正在端正地走下去。到底了,我才想起鸿祯塞,却只望得见山丘了。
楼底藏着一个车库,停着一辆香槟色宝马。
这儿叫板桥湾。它其实是一个小平原,让那山丘拦成了一个山湾。这一片小砖楼有一点密,外观大体相当。我是一个路痴,就先绕着三层小楼转了一圈,只见顶部墙外围着玻璃。我往远处走,还好,什么时候回头都能看得见它。但是,我无论走到什么位置,鸿祯塞一点影子都望不见。我为了避开游人不断转向,上了一条石板小路。我在油菜花间的石板路上走了一段,掉头朝来的方向走回去,“玻璃屋”和喜鹊窝就都在跟前了。
一个女人从“喜鹊小栈”出来了。我没话找话,问起了“玻璃屋”里那个老人。
“大家都叫他汉子大爷。”她想了想,“他叫雷高汉。”
我听出来,她就是电话里那个女人。我问:“昨天黄昏,你去他们家了吧?”
“送豆腐。”她说,“汉子大爷喜欢我们家的豆腐。”
她却不知道,是谁给汉子大爷修了个高级别墅,三年前又给他配了个美女秘书。温寒露来了以后,汉子大爷在夜里都要到门外大声咳嗽,最近又在夜里出来喊什么人了。
我问:“他没有亲人吗?”
“我也不知道。”她说,“听说,他从前是包家的管家还是什么。”
“哪个包家?”
“这儿除了鸿祯塞,还有哪个包家?”
我转了一圈回去,才看见正门下来那地上栽着一块标识石,上面刻着“鸿祯田庐”。我上了台阶,在正门前面回过头去,看见那一片建筑的顶已经冒出来,平顶上面还有钟楼一样的尖顶。
那棵海棠把上午的阳光挡了一半,我在秋千上坐下来,又在手机上搜起了“鸿祯塞”。我浏览了一下说明文字,细读了几篇文章,知道了这座保存完好的建筑不同凡响。一篇文章里说,“据百岁老人雷高汉大爷回忆”,他八岁时从外地逃难来到板桥湾,那个山丘上已经有了建筑,就是南塞。他说,他在十几年后参加了北塞的修建。那些文章里见不到包氏家族多少影子,却都有一个和说明文字保持一致的雷同部分,“鸿祯塞始建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那篇文章说到此处又多了一句,“雷高汉大爷也生于那一年”。那么,他逃荒到当地时已经八岁,距今已经九十九年。
就是说,这三楼上住的老人,已经一百零七岁了。
午餐有三个菜,一笼蒸肉,一碗鸡汤,加上一盘清炒豌豆尖。
我和温寒露默不作声吃了一阵,还是她先开了口:“蒸肉和鸡汤,还有酸菜豆腐挂面,都是老祖宗喜欢的。”
“那么,这一盘豌豆尖,是特意为我加的了?”
她不理会我的幽默:“他牙还好,就是听力没了。”
“助听器呢?”
“买过两个,都不管用。”
“你们怎么交流?”
“他动嘴,我动笔。”
“你是他的秘书?”
“崔蔓莉告诉你的吧?”
“谁是崔蔓莉?”
“我看见她和你说话了。”她说,“我是保姆。”
“他没有亲人?”
“或许有。”
“伙食费,还有你的工资,谁管?”
她埋头吃饭,不再搭腔。
我却不依不饶:“这房子,是他自己的积蓄修的吗?”
过了一阵,她才告诉我,成都一个房地产集团做慈善,在全省农村挑了一百个孤寡老人,为他们建“安乐居”。汉子大爷得知自己被挑中,反倒提了一个条件,如果在新房里依旧看不见鸿祯塞,就请把指标让给别人。
我知道屋基为什么要升高了。我问:“对方为什么就答应了?”
“那年他正好一百岁。”她说,“大概为了新闻效应吧。”
我在手机上却没有搜到那个新闻。我说:“下午,我想去看看鸿祯塞。”
我去鸿祯塞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那石板小路,一条是那水泥大路。温寒露建议我走石板小路,从那片黑松林爬上去。她说:“无论多么优秀的路痴,也不会把那么大一个目标走丢了。”
我上了石板小路,从一条横空跨过的水渠下面穿过,没多久就进了黑松林。石板与另一路爬上来的石板在黑松林里会合,那路就变宽了。出了黑松林,劈面一道石梯,到了。
鸿祯塞,覆盖了整个山丘。
山丘三面都是坡壁,被城墙擦着边儿揽过来,只在南面开了一道门。门外那道石梯依了地势,弯弯扭扭到了门口。门口也有些局促,一个从地面冒出半截的大石头在那儿支撑场面。城墙的基石顺了山丘的原样,微微泛红的条石从上面砌起来,高一脚低一步,头上却一水儿端平了。黑松林蔓延过来,松树在外面薄薄地围了一圈。空中冒出来的那个尖顶,就是在图片上见过的望哨楼了。
我买票进去,游人远不如看油菜花的多。我穿过两个天井,从一道石梯爬上城墙。城墙顶部是一道宽大的回廊,其实是一个全封闭的炮楼,哪一段都像一张弓。回廊坚固的石头外墙,一圈儿布满了瞭望口和射击孔。石梯有好几道,兵丁可以从不同方位同时奔上炮楼,从射击孔向外开枪。回廊上面有木构屋架顶着青瓦,既遮风避雨,又与内部的木构建筑连成一体。石头主外做军事防御,木头主内过太平日子,它们互相依存,因为只有军事防御成功,才会有太平日子好过。
军事防御的外壳是关键的,所以叫了“塞”。
太平日子的内瓤是丰厚的,挑了“鸿祯”二字。“鸿祯”,就是“极大的祥瑞”。
我从不同方位挑了射击孔往下看。我在大门顶上看到,下方的小山窝里藏着一片屋瓦和一座碉楼。不用问,那就是网上说的包家大院了。包氏家族就是从那个小山窝发迹的,当年最为显贵的包企鹤,在晚清做到了五品大员。
鸿祯塞和包家大院之间有一道长长的石梯相连,虽然不直,却避开了黑松林。
直到油菜花晃花了眼睛,我才看见了“鸿祯田庐”。远远望过去,它混在那一片小砖楼丛中,“玻璃屋”在夕阳下闪耀着零碎的光点。
我从城墙上下去,上坡下坎,已经说不清是向里还是向外,也估算不出山丘的原样。我已经从网上知道,鸿祯塞众多的房间起先大都分给了翻身农民,后来又被公家买回去做了粮站。这会儿,我却只能依靠标识牌去辨认了。
溥仪在长春那个“伪满皇宫”,好像都不如这儿气派。
我不大懂建筑,草草一看便返回了。我走的是水泥大路,一见有农用车或是摩托过来,就早早让到一边。
吃过晚饭,我又坐上了秋千。天上的星星好像都到齐了,装进了钢架上面那些方格。我头顶那一格里的星星有点稀疏,秋千一晃,有一些就出去了,更多的立即挤进来。
地上突然亮起几颗小灯,就像大个儿的萤火虫。
温寒露给汉子大爷送饭上楼,差不多一小时才下来。我坐上藤椅,把秋千让给了她。
她说:“他那电脑出了一点问题。”
我问:“他会上网?”
她看不出用了什么力气,秋千却渐渐飘高了。她的声音也飘起来:“刚才,他在网上看了一会儿你的小说。”
“哪一部?”
“《宫影记》。”秋千上的声音降下来,“昨天晚上,我差不多看了一半。”
仅凭地灯的光亮,我看不见她的表情。
“他看得很慢。他说,他想向你请教一下。”
“就是说,我可以上三楼了?”
她就是在秋千上点了头,我也看不见。头顶的方格已经换了,里面的星星密起来。她让秋千安静下来,说:“你或许不应该错过他。”
我不知是不是点了头,反正她也看不见。
“他一直在记笔记。”她说,“他把笔记本都锁在一只皮箱里。”
我问:“他什么文化程度?”
“他七十岁才开始自学识字。”
我正不知道怎样表达惊讶,却见三楼上的门打开了,走出来一个高大的身影。灯光映照出来,那身影在星光和灯影里缓慢地移动着。我以为那喊声又要起来了,可是,夜晚静悄悄的。接下 来,我连一声咳嗽也没有听到。
第三天上午,温寒露领着我上了三楼。汉子大爷站在屋子中央,向我行拱手礼:“景三秋老师,请!”我也赶紧向他还拱手礼。我知道他听不见,却还是说:“大爷,叫我小景。”温寒露在一张纸上写下“叫我小景”,给他看。“你是作家,可以给寒露当老师呢。你是她的老师,而她是我的老师,你说,我该叫你什么呢?”
他说完,已经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来,然后请我在另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来。他身材高大,站着时的那点驼背坐下去就直了。他穿一件藏青色毛衣和一条黑色休闲裤,趿一双紫色布拖鞋。他说话很慢,就像怕说错一个字,声音并不高,吐字很清晰。他的眼睛也很清亮,不用眼镜,温寒露写的那四个小字他就只看了一眼。他的头发和眉毛全白了,稀疏的头发留得很浅,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他的脸上堆满了小山丘,因此,那笑意一直散不开来。
我从没有见过一百岁以上的老人,想说他看上去最多八十岁,却又想起温寒露的提醒,尽量少去麻烦纸和笔,所以,我只保持着一副毕恭毕敬的笑模样。
屋子很大,中间有一扇镂刻着梅花的玻璃屏风。前半间里有一张宽大的写字台,上面摆放着电脑,一部《新华字典》和一部《现代汉语词典》,一个砚台和几支毛笔,还有一叠纸片和几支硬笔。写字台前摆放着一张硬木椅。墙上有电视、电子钟和挂式空调。一个很小的木制书柜里只有少量的书,除了《论语》《孟子》《老子》《唐诗三百首》,还有几本很薄的旧书和武侠小说,以及毛笔和硬笔书法字帖。皮革单人沙发背靠玻璃屏风摆放,小茶几上除了茶杯,还有一个红色呼叫按钮。地板是实木的,非常干净。一张木制小几也靠着玻璃屏风摆放,上面那只上了锁的皮箱很显眼。皮箱是红色的,已经转暗,但是,看它的时候也会看到屏风上的梅花,那一团红朗朗的光芒就会照耀过来,暗红皮箱就会鲜亮起来。
那好像并不是一个老人的屋子,我没有嗅到一丝苍老的气息。
温寒露坐在硬木椅上,我转向她小声问:“后半间除了床,还有什么?”
“衣柜、盥洗室和卫生间。”
汉子大爷对我说:“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寒露为我盘回来的。”
温寒露夸张地指了指那只暗红皮箱。
“对,它不是。”
汉子大爷看了《宫影记》开头部分,他问我为什么不让末代皇后婉容当主角,而是让祥贵人谭玉龄来当?我拿过纸和笔,想写下“谭死得早”,一想不妥,就写下了“避免撞车”。我正担心他会误会“撞车”,却听见他说:“撞车最多的,还是写戏班那些戏,你抄我,我抄你。”
我写道:“我相信,您有不同寻常的人生。”
他说:“我这本书,虽然不大可能和人撞车,却有可能一再让人失望。”
我写道:“您愿意讲给我听?”
他说:“你只要不嫌我说话慢。”
我写道:“要是每天对谈两三个小时,您行吗?”
“别担心。”他说,“我这条命,是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不会一下子就散了。”
屋外阳光正好,我和温寒露陪着汉子大爷从屋里出来,在四面贯通的廊道上走了一圈。四周镶上了遮风挡雨的玻璃,每个方向都有高低不一的方孔。汉子大爷不用拐杖,在洒满阳光的仿石材地砖上踩踏实了,才迈出下一步。他已经有两年没有下过楼了。他说:
“我也知道那玻璃楼梯不会有事,但越来越不敢走它了。”
一声不吭的喜鹊窝差不多和三楼一样高,我们透过玻璃从它顶上望过去,鸿祯塞拉近了,也变大了。
汉子大爷没有望鸿祯塞,而是低头在看油菜花间那条石板小路。我已经知道,那是他九十岁那年修成的,他拒绝任何人帮忙,一个人前前后后修了两年。
我对温寒露说,我愿意中断正在进行的写作,来听一听汉子大爷的故事。我说,我可以在旁边的“喜鹊小栈”住下来。
“为什么要去民宿?”温寒露说,“你在这儿愿住多久就住多久。”
“那好。”我说,“费用,你按照民宿标准折扣收取吧。”
我在“鸿祯田庐”一住就是一年。
温寒露在县城为我买回一支录音笔,就把我们撇在一边,每天换着花样做三顿饭。她是能够做出拿手好菜的,只不过汉子大爷的老三样很少有变。
汉子大爷为我打开暗红皮箱那一刻,他的一生就算正式对我敞开。
他让我看他那些笔记本,只是不能带出屋,并且不能透露给温寒露。他管控着它们的出场顺序,也管控着让自己的岁月重来一遍的路线。那些一天一天好起来的字迹,浓缩了他的记忆。他那先于我七十年的人生里面,确实藏着一个一个让我惊异的段落。一百零七岁的人生,收拢在一个玻璃护卫的逼仄空间里,以顺时针或逆时针的方向,以分针或秒针的脚步,向近在眼前的终点走着,让我听到了生命的嘀嗒声。他年轻的身影刚在我眼前浮现出来,我却害怕他转眼间就老了,甚至走了。
我对自己说,慢慢看,慢慢听,慢慢记,慢慢整理,一切还得从头开始。
我从二楼再上一层楼,坐在那张暂时为我专用的单人沙发上,恭敬地倾听另一张单人沙发。
我从三楼下来,站在二楼宽大的玻璃窗前。鸿祯塞在远处,在上面。路在眼前,在下面。那么,汉子大爷,雷高汉,他是从哪一条路来到板桥湾的呢?
第一章 玻璃屋 001
第二章 暗道 016
第三章 喜鹊窝 055
第四章 戏台 066
第五章 天井 125
第六章 望哨楼 136
第七章 田庐 187
第八章 黑松林 198
第九章 井 235
第十章 水库 245
第十一章 秋千 293
第十二章 瓦房 298
第十三章 暗红皮箱 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