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正当吴波金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时,木材商 “弗落疾”先生,维拉斯瓦米医生的朋友,刚刚从家里出来,准备去俱乐部。
弗洛里差不多三十五岁,不高不矮,长得也不错。他头发乌黑,又短又硬,贴着脑袋,还留着短短的黑色小胡子。他的皮肤天生就是土黄色的,让太阳晒得变了色。他并没有发福,也没有秃顶,所以并不显老,但除了被晒变色,他的脸一副憔悴样,脸颊瘦长,干瘪的眼窝深陷下去。很明显,他今早没有刮胡子。他穿着平常总穿的那件白色衬衣,一条卡其色的斜纹短裤,一双长袜,但是他没戴遮阳帽,而是戴了顶破旧的印度特赖帽,帽檐遮住了一只眼睛。他手里拿着一根带腕带的竹拐杖,身后跟着一只名叫弗劳的黑色可卡犬。
但这些都不是他最明显的特征。人们见到弗洛里,首先会注意到他左脸上那块丑陋的胎记——不规则的月牙形,从眼部一直延伸到嘴角。从他左脸望去,他一副历经沧桑,愁眉苦脸的样子,那块胎记就好像是块青得发黑的淤伤。他也知道这胎记是多么丑陋。在人前,他总是侧着身子,不想让别人看见他那块胎记。
弗洛里的房子在山顶的练兵场上,就在丛林边缘的不远处。从他家大门开始,整个地势急转为下坡,卡其色土地被烤得焦黄,房子周围分布着六间亮白色的平房,透着热浪望去,都在微微颤动。在半山坡的一面白墙里面,有一片英国墓地,附近有一座锡顶的小教堂。教堂后面,便是欧洲俱乐部了。这是座破旧的单层木头建筑,当你看见这个俱乐部时,在你眼前的就是这个镇子真正的中心了。在印度[2]的任何一个城镇,欧洲俱乐部都是精神圣地,是英国权力的集中地,是当地官员和百万富翁可望而不可及的极乐世界。而在皎塔达,更是如此,因为令皎塔达骄傲的是,这里的欧洲俱乐部从来不接纳东方人做会员,也许这在全缅甸也仅此一家。俱乐部外面,赭色的伊洛瓦底江水浩浩荡荡,在阳光下波光粼粼,闪着钻石一样的光芒。大江后面是大片大片荒弃的水稻田,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最远处,与连绵的青山相接。
当地的城镇、法院及监狱都在右边,大多藏在绿色的菩提树丛中。佛塔的塔尖冲出树丛,就好像是镀了金的细长矛。皎塔达是个非常典型的缅甸北部城镇,从马可·波罗年代到1910年就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要不是由于这里建了火车终点站地理便利,皎塔达怕是要在中世纪再沉睡个一百年了。1910年,政府将其封为分区的首府、重点发展的对象——也就是建立了一系列法庭,里面充斥着大腹便便、贪婪无厌的辩护律师,还建了一所医院、一所学校还有一座坚固的大型牢房,从直布罗陀到香港,英国人建造的这样的监狱随处可见。这里人口大概有四千,包括两百个印度人、几十个中国人和七个欧洲人,还有两个欧亚混血,弗朗西斯先生和塞缪尔先生,分别是一个美国浸信会传教士和一个天主教传教士的儿子。镇子里没有什么奇闻异事,除了有个印度苦行僧在市集边上的一颗树上住了二十年,每天早上都用篮子把食物吊上来。
弗洛里出了大门,打了个哈欠。前一天晚上,他喝得半醉,耀眼的阳光让他烦躁起来。望着山坡下,他心想:“该死,该死的破地方!”周围除了他的狗,没有别人,于是他开始用“神圣,神圣,神圣,啊,您是如此的神圣”的曲调大声唱“该死,该死,该死,啊,你是如此的该死”,他沿着烫脚的红色山路往下走,边走边唱,还一边朝着路边干枯的草丛挥舞着手里的拐杖。快九点了,太阳越来越毒,热浪劈头盖脸地袭来,持续不断地猛压过来,就好像在被一个巨大的垫子不断地当头猛击。弗洛里在俱乐部门口站了一会,琢磨到底是进去还是继续往下走,去拜访维拉斯瓦米医生。然后,他突然想起,今天是“英国邮政日”,报纸应该送到了。于是他走了进去,绕过那张巨大的网球网,上面爬满了滕蔓,还长着淡紫色的星型小花。
路边的绿化带里面种着一排排英国品种的花——福禄考花、飞燕草、蜀葵花和矮牵牛——目前还没被太阳晒死,开得花枝招展、妖娆饱满。矮牵牛长得很大,几乎和树一样大。这儿没有草坪,但有一丛丛当地树木和矮灌木——繁茂的凤凰树就像是血红色的伞,鸡蛋花树上面则开着奶油色的没有花茎的花朵,紫色的九重葛、鲜红的木槿、粉红的月季花、绿得扎眼的巴豆、长着如同羽毛般蕨叶的罗望子,开得姹紫嫣红,让人看着目眩。一个几乎赤身裸体的园丁,手里拿着一个水壶,在花丛中穿梭,就像一只巨大的采蜜鸟。
在俱乐部台阶上,站着一个浅棕色头发的英国人,须髭如戟,一双灰白的眼睛眼距很宽,两个小肚腿简直瘦得出奇,双手插在短裤的口袋里。这是韦斯特菲尔德先生,这个地区的警长。他无聊地哼着的小曲儿,垫着后脚跟,前后不停地晃动着,他翻着上嘴唇,用小胡子刮着自己的鼻子。看见弗洛里,他脑袋稍微歪了一下,和他打了个招呼。他交流的方式总是简短干练,绝不多说一个字。从他口中讲出的话几乎都是在开玩笑,但他说话的语气却空洞而忧郁。
“嗨哟,弗洛里老兄。今儿早上真他妈够难受的,是不?”
“我想这个时节就是这样。”弗洛里说道。他把身子斜了斜,试图不让韦斯特菲尔德看见他的有胎记的左脸。
“是啊,真该死。还要忍受两个多月呢。去年一直到六月都没下一滴雨。看看这该死的天,连片儿云都没有,他妈的就和个搪瓷的蓝色平底锅差不多。上帝呀!真希望现在在皮卡迪利大街啊,是不?”
“英国报纸送来了吗?”
“来了。《笨拙周报》,《粉安报》,《巴黎人生活报》都到了。读起来会想家,是不?趁冰还没化,进来喝一杯吧。拉克斯廷那老家伙几乎在酒里泡着呢,已经半醉啦。”
他们走了进去,韦斯特菲尔德用他那悲伤的声音说道:“来,麦克德夫。”俱乐部里面,墙是柚木的,房间里一股石油的味。俱乐部一共只有四个房间,其中一间是一个无人光顾的“阅览室”,里面放着五百多本发了霉的小说,另一间房里有一张脏兮兮的旧台球桌——但是几乎没人在这儿打球,因为每年都有大半年的时间,成群结队的飞虫会在电灯下嗡嗡打转,桌布上也爬满了飞虫。还有一间棋牌室和一间“休息室”,“休息室”外面有个宽敞的阳台,朝向江面。但每天这个时候,所有的阳台都拉上了绿色的竹帘。休息室丝毫没有家里的感觉,地上铺着椰棕地毡,桌子椅子都是柳条编的,上面丢满了鲜亮的插图报纸。房间装饰有几幅“邦左”画,还有几个落满灰尘的黑鹿头骨。挂在天花板的布屏风扇懒洋洋地转动着,将灰尘卷入温热的空气中。
房间里有三个男人。在风扇下,有个满脸通红、长相不错、稍稍发胖的四十岁男人,他两脚摊开躺在桌上,双手捂着脸,痛苦地呻吟着,这个人就是拉克斯廷先生,木材公司的地区经理。前一天晚上他喝得烂醉如泥,现在正受罪呢。埃利斯是另一家公司的地区经理,他站在公告牌前,痛苦地集中全部精力阅读着一条告示。他个头小小的,头发又硬又直,长着一张苍白而又棱角分明的脸,很是好动。马克斯韦尔是代理地区林业管理员,他正躺在长椅上读着《旷野报》,人们只能看见两条大骨架的腿和两条汗毛浓密的粗壮小臂。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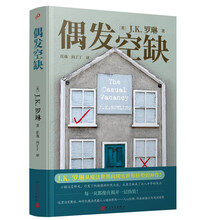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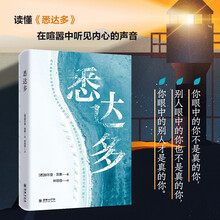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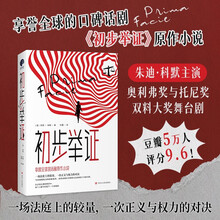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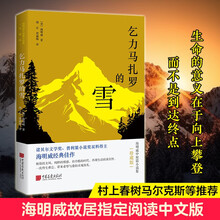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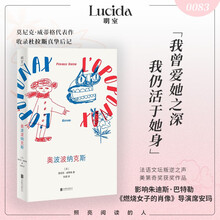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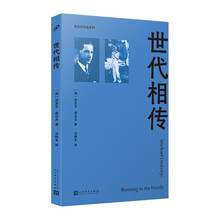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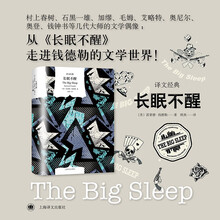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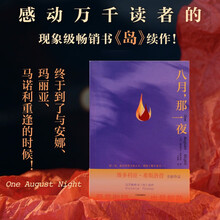
在不让他们获得自由的前提下,他觉得他们是这世上可爱的人了。
奥威尔首先是先知,其次才是圣徒。
——止庵
奥威尔是我们这一代人中仅有的几位重要的作家之一。
——Desmond MacCarthy
他能够在目睹糟境况的同时为美好的东西而战。
——Granville Hicks
我想写的,是一种有着悲伤结局的长篇自然主义小说,不仅充满细致入微的描写与恰到好处的比喻,而且不乏精彩华丽的辞藻,选词注重其音韵之美。事实上,我构思了许久,但直到三十岁才完成的一部小说《缅甸岁月》,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奥威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