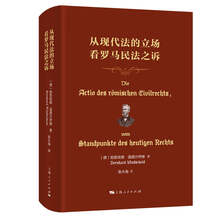一、现行著作财产权体系存在的问题
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以作品使用行为为依据,规定了12项著作财产权,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和汇编权,最后以“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作为兜底条款,防止挂一漏万。这种清单式列举的初衷是对著作权人提供全面保护、对司法实践提供明确指导,但是,如此纷繁复杂的规定在实施中却存在诸多问题,无法很好地因应现实需要。
1.权利细化导致“封闭式”的误解
权利细化便于在司法实践中找到立法依据,但会导致人们将著作财产权理解为“封闭式”体系,以为只有法律条款规定的权利才受保护。虽然有“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这一兜底条款可以覆盖相关行为,但是由于著作权法并未对“著作权”作出定义,因此“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在理论上难以界定究竟是著作权法上的权利还是该法之外的权利。而我国是成文法国家,通常会考虑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因此实践中真正适用这一条款的案例并不多见。这便造成,立法修订前产生的新的著作权使用方式很难得到确定承认,不利于及时保护;同时也会提出比较频繁的立法修订要求,不利于维持法律的稳定性。
2.权利规定过于偏重技术特征根据使用行为划分权利项时,越细致区分使用行为,就会越具体、越严格地界定权利项。换言之,权利项的外延趋于狭窄。而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作品使用方式不断增加,现有的权利列举势必无法很好地涵盖新的内容。对此有两种解决思路:一是修改现有的权利内容,扩张其外延,涵盖新的使用行为;二是在现有权利之外增加新的权利项。从著作权法的历次修改可以看出,我国采取了第二种思路。其优点在于能够直接回应技术进步提出的特定问题,便于司法适用。缺点是,法律的滞后性易于导致立法频繁修订,同时造成《著作权法》第10条的内容越来越庞杂,增加了各权利项的界定难度。
3.权利界定不甚合理
立法应当准确划定每个权利项的保护范围,不扩大也不缩小相关权利的外延。但现行立法在此方面显然不尽如人意。以翻译权为例,仅对作品进行翻译而不利用和传播翻译作品,不会损害著作权人的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因此立法目的和权利人的诉求并非限制翻译行为本身,而在于规制翻译作品的利用及产生的利益。事实上,作者无法控制这种演绎行为,实践中也从来没有人对此追究侵权责任。但是,从文义上看,现行立法却将翻译行为本身纳入著作权的规制范围,这既缺乏合理性也远离人们的生活经验。再如广播权,现行立法界定来源于《伯尔尼公约》第11条之二的文字表述,从权利可控制的范围看包括三种行为:一是以无线方式传播作品,二是对广播作品的有线传播和转播,三是对广播作品以扩音器或其他类似工具再现。结合“有线传播”和“转播”的含义,可以发现,以有线方式直接传播作品、对有线传播作品的无线转播、有线转播、扩音器转播等均不在广播权的范围内。①这将导致一部分传播行为无法受到立法规制。
4.权利之间存在交叠或空白
以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为例。根据现行规定,广播权仅涉及非交互式传播,并且限于无线、有线和扩音器方式,信息网络传播权则针对在线交互式传播。据此,通过信息网络进行的在线非交互式传播,既不受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也不受广播权控制,可能游离于立法之外。再如,表演权、放映权和广播权应当如何划分,数字环境下的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如何界分?此等问题即使是从事知识产权研究的专业人士也很难清晰判断。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