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童年早期的人格发展是成年人格的基础,另一方面童年之后出现了重要的发展变化,这两种看法看似矛盾,实则不然。精神分析立场并非认为童年人格和成年人格完全一致,而是说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基础或结构框架。试想一下,一个在童年早期具有强烈口腔破坏性幻想的人,经常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强大恶势力的破坏者和牺牲品。精神分析理论似乎由此断定:这些想象将在其成年人格中发挥重要的构成作用。但是,它们的表达形式、与自我分离的程度,或者融入具有个人和文化意味的自我认同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童年中期、青少年期和之后的经历。关于这一点,埃里克森在讨论达塔他人时有过令人难忘的解释。
除了一以贯之的内容,精神分析观点原则上允许人格发展有变化,允许考虑整个发展过程和顺序。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即完全关注童年早期,忽视后面的发展阶段。究其原因,部分在于关于后面阶段的发展理论相对停滞。比如,卡迪纳在多项研究中试图描述个体从出生到成年的生命周期。但是,最后他还是把成年人格首先和童年早期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
罗海姆认为,只有在超我形成的主要过程出现之后,即五六岁之后,个体才可能形成特定的文化价值和模式。与之相似,德弗罗提出童年中期,从生殖崇拜阶段到青春期,在许多方面是个体“文化”性格发展的关键时期。不过,对于这种发展,两位研究者都没有提供更多概念解释或经验描述。
过去几十年来,童年中期、青春期和青少年时期的人格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理论关注,尽管这个趋势还不曾对国民性研究产生很大影响。苏理文在这方面提出过一些有趣的观点,但他的理论较为概括,没有被社会研究明确利用。墨菲的情况与之类似;从他1953年的印度研究中就可以看出这种理解路径的价值。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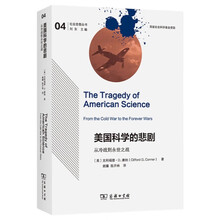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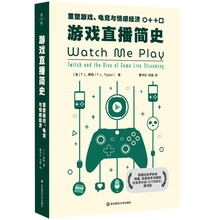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驻院学者
艾历克斯·英格尔斯是研究民族与人格关系的权威。他一生的研究和思考凝聚为这本书。当代政治事件显示,国民心态上的差异现在如以往一样重要。对研究现代社会的跨文化心理学家、比较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英格尔斯的著作在未来若干年中,都是重要的资源。
——吉尔特·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荷兰文化合作研究所,《文化之重》作者
借用马克·吐温关于天气的说法,人人相信并依赖国民性,但没人觉得能够科学地研究它。作为这种思维的讽刺性产物,任何国民性研究都有可能同时引发对其实质内容的赞同和对其方法论的质疑。在这部穷其一生写就的著作中,英格尔斯打破了这个困局,使国民性概念和它的研究方法同时变得可靠可信。他的众数人格概念是在两个极端之间作出精彩而有价值的妥协:一方是在“集体心理”研究中的成见,另一方基本上否认不同文化类型的存在。他的国民性观念从来不曾脱离其社会文化决定因素。他的比较视野也相当广阔。而且,他的著作运用了最适宜、最好的社会科学方法去研究时常难以捉摸的集体性格现象。英格尔斯的国民性研究跨越50个年头,著述散见各处。无论是社会学者还是普通读者都应该感谢作者和出版商把这些精彩的论述汇集为一本书。
——内尔·J.斯麦尔瑟(NeilJ.Smelser),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