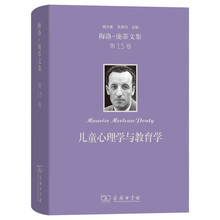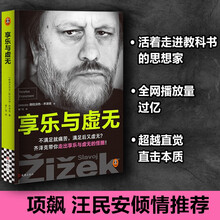帕里是1950年问世的,21年后,英国的数学家兼计算机工程师艾 伦·图灵写了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他在文中提出了一 项测试,以决定一台机器是否可以思考。该测试以被称做模仿游戏的派 对游戏为基础,需要一位对话者与一个人和一台机器交流,两者并无身 体上的联系,而是以电流的形式联系。为把人与机器区分开,对话者什 么问题都可以问,如果一段时间内对话者还不 能区分,就可以说机器通过了考试。帕里通过考试了吗?其实没有。按照适当 的图灵测试,精神病学家小组(充当审问之人 的角色)应该事先告知其中有一个病人实为计 算机,大家的任务就是认出哪个是计算机。不 管怎么说,问的问题再宽泛,帕里都可以迅速 作答。图灵本人相信,到20世纪末的时候,计算机编程的进步将会达到这样一种地步:无论谁来充当对话者,五分 钟的交谈之后,正确识别的概率不会超过70%,可实际进步比图灵预测 的要慢很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台计算机通过图灵测试。图灵以该测试回避了“机器能否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该问题太 不准确,因而不值得解决。但该测试现在被广泛当做判定一台机器是否 能思考(根据个人偏好,可以说“有心灵”或“展示了智力”)的标准。这样一来,图灵测试就被视为“强人工智能”的支持者(科学的或哲学 的)基准点。这些人认为,适当编程的计算机有与人类一模一样的心灵 (不仅仅是心灵的模拟)。中国屋 1980年,由美国哲学家约翰·瑟尔设计的思想实 验,成为对图灵测试的最大挑战。他本人是一位说英语而对汉语一无所 知的人,想象自己限于一间屋子里,然后有人寄来了中国汉字。他有很 多讲汉字和语法的英文书,用来解释如何从屋里寄出一定的文字结合,以回应给他寄来的一串儿符号。他最后可以轻松胜任,而且在屋外的人 看来,他的回答与中国人没有差别。换句话说,从屋子的输入和输出来看,还真像那么回事,好像他对汉字了如指掌一般。可实际上,他在 做的只是处理未经解释的形式符号,而对汉字 什么都不理解。为了回应给他传来的东西,他根据一套程 序(与瑟尔的那些英语写的语法书一样)提供 的规则做些恰当的回答,这就跟数字计算机一 样。瑟尔表明,像中国屋这样的一套计算机程序,不管多复杂,都只是 操纵符号的无心之士,而且绝不会越此一步。它本质上是按照句法规则 办事,遵循规则来操纵符号,但它不理解意义,不理解语义。就像中国 屋中没有理解一样,计算机程序中也没有理解:没有理解,没有智商,没有心灵,总是对以上这些东西的模拟而已。通过图灵测试,基本上就是给一定的输入提供适当的输出,以此来 测试一台机器能否思考。所以,如果你能接受,中国屋其实削弱了这一 点。如果图灵测试奏效,那么人工智能的核心论题也应该奏效。但并不 只有这一种因果关系。如果承认中国屋的观点,那么,研究心灵哲学的 这两条特别重要的途径就会随之被削弱。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的一些问题 行为主义背后的中心问题是,精神现象可以转化为各种行为或某种 行为习性,而没有任何损失。所以,说某人疼痛,就是他在流血,疼得 面部扭曲的简要说法。换句话说,精神事情完全根据外在可观察的输入 输出来确定,其充分性已经被中国屋明确否定了。在瑟 尔之前,由吉尔伯特·赖尔所做的经典解释基本上已遭到众多致命的反 对。在今天看来,其重要之处在于产生了功能主义这一学说,功能主义 可能是被接受最广的心灵理论。功能主义为修改行为主义中的很多缺陷,主张精神状态即功能状态:一定的精神状态可以根据在与各种输入(特别引起精神状态的原因)关 联时所扮演的角色、对于其他精神状态的影响、各种输出(精神状态对 于行为的独特影响)而定。用计算机来类比一下,功能主义(类似于行为 主义)是对于心灵理论的一种“软件解决之法”:根据输入和输出来确定 精神现象,而不考虑软件借以运行的硬件平台(二元论者、物理主义者之 类)。当然,问题在于,聚焦于输入输出将胁迫我们径直地返回中国屋。天啊,西奥从乔那里买来的车有问题吗?问题是 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小事儿,和往常差不多,有个门锁要换。后 避震轴中的一些小零件掉落了。接下来,大一点儿的零件也开始出问题,先是离合器,后是变速箱,最后整个变速器都出了问题。修理过程中,这辆车又出现了大量问题。所以,差点儿就没能开出车身修理厂。就一 直这样,日复一日……真不可思议。西奥很悲伤,自己在那里琢磨:“如 果这辆车才买两年,就把每个零件换过了,那可才叫难以置信呢!嘿,往好处想吧!也许我有了一辆新车!”西奥这样想对吗?还是说其实仍是同一辆车?人、事的身份会随时 间的流逝而变化,在检验对这一变化的直觉时,西奥的汽车的故事通常 被称为忒修斯之船,是哲学家使用的众多难题之一。似乎我们在这方面 的直觉往往强烈但却相互矛盾。忒修斯之船的故事是英国哲学家托马 斯·霍布斯提出的,后来他做了进一步的详细阐述。下面来看看西奥的版本吧。诚实的乔其实名不副实。他从西奥车中换下的那些零件,大部分都 是好的,而后他又修理了一下那些出毛病的地方。乔把那些换下的旧零 件都攒了起来,重新组装在一起。两年后,他便组装出了一辆车,可以 说是对西奥那辆车的准确复制。他自己认为这是复制品。或许这就是西 奥的那辆车?身份危机 哪个是最初的?西奥现在这辆完全由崭新零件组成的车,还是乔那 辆完全由原厂零件组成的车?答案也许取决于你问谁。不管答案是什 么,这辆随时间而变的车的身份问题远没有我们期望的那样简明微小。这不只是车或船的问题。人一生会发生巨大变化。一个姗姗学步的 2岁小孩儿与88年后一位步履蹒跚的90岁老者之间,在生理和心理上,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他们是同一个人吗?如果是,又是什么让他们成为 一个人呢?这可不是无稽之谈,因为他70年前做的某件事而惩罚这位 90岁老者公正吗?如果他不记得了呢?如果这位90岁老人40年前说 自己到90岁时就让医生把自己杀掉,现在他90岁了,医生应该那样 做吗?这就是人的身份问题,几百年来一直令哲学家感到困惑。那么,究 竟在何种充要条件下,某时的一个人和之后某一时刻的他是同一个 人呢?动物和大脑移植 常识看法可能是这样的,个人身份是生物学问题:我是过去的我,因为我仍然是同一个活着的有机体,同一人类物种;我还是附着在一个 特殊躯体中,该躯体是独一无二且连续的有机体。抽空想象一下大脑移 植吧,在伸手可及的未来科技中我们有望实现这样的手术——把你的大 脑移植到我体内。我们的直觉显然认为,你有了新的身体,而不是我的 身体有了新大脑。如果是这样,那有个特殊的身体就不是个人生存的必 要条件了。P37-41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