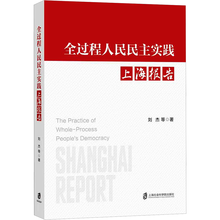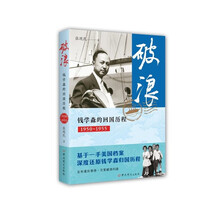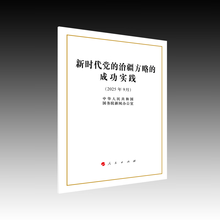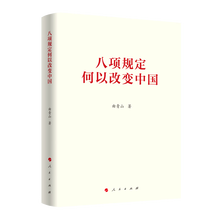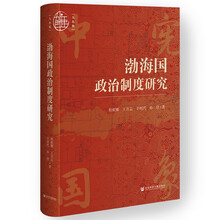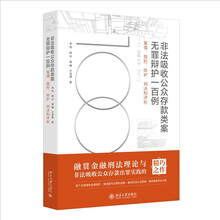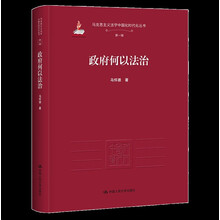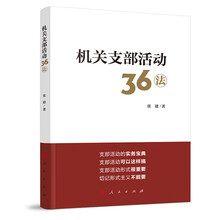如上所述,编者是有意让读者知道作者的资讯,即使是零碎的资讯,那么第一和第二个可能性就可以大部分排除了,即使发生(见下),数量不会太多,至少不会多至每4.2个书判就有一个是无名的那样大。所以,只剩下第三个可能性,即121个无名书判里,“大部分”都不是无名,而是作者被省略了,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宋本户婚门争业类的第一案《吴盟诉吴锡卖田》下面写着“西堂后同”(今从中华点校本4:100作“范西堂,后同”,它不见于现存的明刻本,应属上文所说,是编者的不小心,仅此一次,见附件1),而接下来十九个案件都没有作者,①这跟今天的学术著作有相同之处,尤其在参考或引用书目里,同一作者有多种著作时,往往只在第一种著作挂上作者,接下来的都节省了。
既有如此直接的证据,似乎可以结案了。但是,读者仍可提出种种质疑,就附件一来看:第一,“后同”假如是指后面的书判都属于同一作者,这些书判都不应有名,但宋本《吴盟诉吴锡卖田》署名“西堂后同”,之后是十九个无名书判,而接着的《漕司送下互争田产》又署名“西堂”,②明本《探阄立嗣》(7:205)署名吴恕斋,之后是两个无名书判,但接着的《不可以一人而为两家之后别行选立》又署名吴恕斋,这不是有点奇怪,理论上《漕司送下》和《不可以》两案都不必再挂上范西堂和吴恕斋才是。同样,宋明两本均有的《亲邻之法》(9:308)署名胡石壁,之后是两个无名案,接着的《典买田业合照当来交易或见钱或钱会中半收赎》又署胡石壁。同类情况可见附件一,不一一列举。第二,“后同”只出现一次,而无名书判共出现55次,在“后同”之前共出现18次,为何“后同”没有在无名书判第一和二次出现时便用上?第一次是在卷一页1至9,三书之最后两书无名(现有者是中华书局所加),第二次是在卷一页16至18,三判之最后两判亦无名。更难明的,是“后同”在无名书判第三次出现且数目颇多之时也没有用上,即卷一页18至24,共十四判,最后十三判无名。第三,有些地方可用“后同”而不用,例如宋明两本均有的卷五,页135至141的五判一一挂上翁浩堂,页152至155的三判一一挂上人境,又卷六页164至168的四判亦一一挂上吴恕斋,相同的情况不少,可见附件一。一言以蔽之,依今天的学术规范,无论是宋本或明本,都犯了“体例不一”的罪名。究竟“后同”能否适用于其他无名书判出现的场合?我们该用什么研究方法?
……
展开